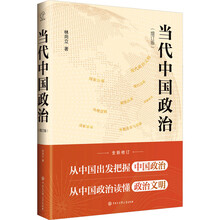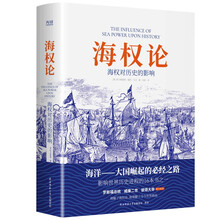然而,我们不仅仅要怀疑,还要判断,还要有所作为。世俗意义上的伟大价值从来都是可以而且必须被分解的,并且可以被量化和用以交换的。否则,就不会产生可以不失去博弈机会而产生的节制以及可以被接受的妥协。认真反思东方民族的困境与教训之后,我发现了“中庸性审慎与决断”这个复合型新概念,据此整理出了“小共同体精神”的问题方法:顾全大局、深思熟虑、力所能及、循序渐进。与某些激情澎湃的口号相比,由于继续贯穿了一种怀疑的精神与承担责任的决心,我当然喜欢这种内省性叙述。
细心的朋友会发现,这些文字,越到后面越回到历史与实证中去。我想说,我仍然警惕某些个体结论,我不相信对几千年历史的简单的归纳与演绎能够告诉我们完全的真相与真理。我还想指出,与另外一些已被我否定的叙述相比,我只敢相信这些结论。一方面我深知“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另一方面我折服于托克维尔、伯尔曼、斯金纳在历史叙述中所得出来的结论。这种专业的治学精神,在中国文明史上是至今难见的。
阅读《联邦党人文集》和《论美国的民主》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西方立宪时期的那些思想家,如果称呼他们为“知识分子”,他们的文章却不是以知识分子为核心而展开的叙述。就个体行为的演绎逻辑而言,以知识分子为核心的叙述,倾向制造道德群体的幻想,更是常常不符合实证要求。真正的学术不应该沉浸在政治正确和启蒙偏见之中。当然,他们还会远离另外各种各样的民族性群体迷信。我们要尊重他们这种独立思考与坚忍不拔的精神。
那么,他们一以贯之的实践、调查、阅读与思考的核心关切,究竟是什么?作为苦苦思索如何“师夷长技以制夷”并完成转型的中国人,我们究竟如何去继承(或者去批判)他们的这种核心关切、思维方式与立宪技艺?在回答此问题之前,我们必先确认一个根本事实:个体的生活经验和公共交往,较之整个社会的实际情况,总是相距甚远。
即便如此。对托克维尔这个法国人来说,他就必须开创政治社会学。发展比较政治学,在大洋彼岸通过田野调查,对比出法国的现状、问题与可珍惜之处。这种实证精神,是绝大多数传统中国知识人所欠缺的。由此导致,中国公共话语中,不仅根本缺乏超越性的关怀,而且基本缺乏在场性的技艺。中华民族的幸福感和荣誉感,从总体上来说是不可确认且难以操练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如果我们希望中国有相对美好的生活,整全的实证研究应该成为这个国家知识人的立身之方法。并成为政府的公共决策之基础。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