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即便学校的确可以戒绝道德教育,这也并非欲求的做法。民主社会中的公立学校应当照顾到我们作为公民对未来公民的道德教育之利益。①我们作为父母所具有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我们作为民主社会的公民所扮演的角色,因此,家庭中道德教育的重点可能非常不同于学校中的道德教育。多数家长希望能够创造一种能满足其情感和精神需求的家庭生活,希望这种家庭生活能允许和自己的孩子分享自己特定的价值。无论这一要求分享特定价值的关切是如何的深厚,它却不必意味着同样关心如何在孩子之中更为普遍地传播这些价值。如果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在该社会中,人们深深地持守诸多不同的价值,而且人们因此可以自由地教授自己的价值于自己的孩子,那么.家长会认识到居于这种社会的优点。
而这一自由依赖于教授孩子对不同生活方式的广泛的和持久的宽容。就孩子的道德教育来说,单独行动的家长和集体行动的公民都发挥着有价值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作用:前者可以教导孩子认识到忠诚于特定的人们以及诸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究竟意味着什么,后者则可以教导孩子认识到自己在一个更大的以及更多元的共同体中的责任和权利。我们最好把民主社会中的道德教育看做是家庭和国家之间的彼此信托,对于那些既理解家庭生活之价值,又理解民主社会中公民身份之价值的每个人来说,这两者是相互受益的。
自由主义中立性
那么,初等学校如何能够最佳地满足这一信托呢?在这个国家中,最常见的答案中有三种答案的理论起点分别源自于我们之前讨论过的个体构成的国家,家庭构成的国家,以及家庭国家。与个体构成的国家最为吻合的答案是:学校应当教授孩子道德推理和选择的能力,而不能引导孩子朝向任何55给定的优良生活观念,或朝向任何特定的道德品格(由教导的能力所衍生的品格除外)。正如一个自由的国家必须让其成年公民自由地去选择自己的“优良”生活,自由国家的学校也必须让孩子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价值。如果公立学校在公民年幼时诱导他们偏向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那么,自由国家所自称的中立性就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而已,是一个遮蔽其教育体系之偏颇性的幌子。
自由主义的中立性支持“价值澄清”这一教育方法,而且,这一教育方法在美国的学校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价值澄清方法的支持者界定了学校中道德教育的两大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帮助学生理解并发展自己的价值。第二个目标是教导学生尊重他人的价值。价值澄清方法的倡导者将其看做是可替代灌输法的一种教育方式:作为对灌输法的替代,我和我的同事为学校中与价值处理相关的所有领域引入了这一种过程方法。这一方法关注的是评价的过程,而非对“正确的”价值的传输,而且这一方法立基的前提是任何人都没有“正确的”价值可以传输给他人的孩子。
尽管它明确声称价值中立,但价值澄清法经常被批评为负载着价值。这一批评并不如通常认为的那样有说服力。价值澄清法的倡导者无须否认,而且很多人也没有否认他们所捍卫的价值澄清法负载着价值:如果我们鼓励批判性思考,这就意味着我们珍视理性;如果支持道德推理,就意味着珍视正义;如果提倡发散性思维,就意味着珍视创造性;如果支持自由选择,就意味着珍视自律或自由;如果鼓励“无损式的”冲突解决,就意味着我们珍视平等……如果被召唤到委员会跟前的话,我们只能说价值澄清法不是而且也从来不是“价值无涉的”。价值澄清法的支持者可以承认这一点,而无须担心自己因道德上承诺教师不应当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学生这一教育立场而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价值澄清法的问题不在于它负载着价值,而在于它负载着错误的价值。把每一种道德观点都看做同样地具有价值,鼓励孩子接受一种错误的主观主义观念,即“我有我的观点,你有你的观点,那么,谁有资格决定我们谁对谁错呢?”这一道德理解没有严肃地对待民主社会中正义的要求。价值澄清法所教导的宽容和相互尊重过于缺乏鉴别性,以至即便是最为热忱的民主主义者也无法接受。如果孩子来到学校后,信守这样一种观念,即“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以及/或同性恋者是低劣的人,因此不应当与他们之外的其他人具有相同的权利”,那么,我们需要的是对孩子的观念做出批评,而非只是澄清。
所需要的批评类似于个体构成的国家所遭遇的那些批评。公民所重视的不仅是孩子的理性选择能力,而且也重视那种使孩子选择优良生活而非低劣生活的道德品格。为了培育优良的品格,可以授权老师只尊重为孩子所认同(或践行)的一些有限范围内的价值。对孩子的价值不加区分的尊重既不能被辩护为教育的终极目标,也无法被看做是培育优良品格的一个可行途径。
道德主义
“道德主义”立场源于我们之前讨论过的家庭国家,它承接我们之上对自由主义中立性的批评,起始于这样一个观念,即基础教育的明确目标就是培育品格,以及限制孩子只能选择那些值得追求的东西。道德主义者,不管是自由主义的还是保守主义的,都拒绝把自由选择看做是基础教育的主要目标。他们着力于塑造一种特定类型的道德品格,然后再辅之以习惯或/和理性的限制,以此使孩子能追求一种优良的生活。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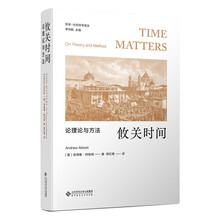



——赫伯特·M.克立巴德,《学术》
这本书不寻常,它提供了一种明确的政治教育理论……其理论布局严谨,实际的含意得到了完整、严密的论证,材料充实,是对美国教育政策中争议性问题的极富启发的讨论。
——琼·弗拉德,《泰晤士报文学增刊》
古特曼博士试图用清晰的概念和良好的常识,建立起民主教育的理论。这本书属于自由主义传统,这个传统可上溯至合众国的诞生……这是一个随着立国者开始的传统,今天这个传统的代表人物是托马斯·内格尔和约翰·罗尔斯。这是托克维尔颂扬的美国。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