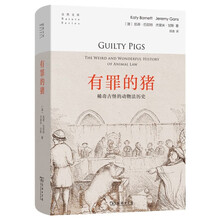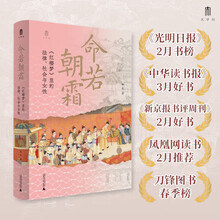有关“情理法”的看法,以及“情理法”的运用,在明清司法审判中可以找出许多鲜活的例证。当时有人认为:“古人立法,止在于生人而不在于杀人。”所以要求司法官“问拟重案,当思此案何处有可轻之情,所犯何人有可生之路,有可宽之罪,于律例有何条可引,恰与之相合,求全案之可轻而不可得,则于所犯之人而求之,于所犯之人求其可生可宽,而又不得则于律例中求其可相援引者,而委屈以合之。总之,念念以生人宽人为要,不厌烦琐周详”。这是因为“古人制律之心原存恺恻,盖因所犯之罪虽一,而所犯之情不一,故又原其情”。所以“今人用律之心,与古人制律之心,本无殊异,是贵原其情而分别之矣”。不过,原情是有一定原则的,“事有关于纲常名教,或强盗叛逆,为法之所不容贷者”,是不能原情的,“彼虽遭显殛,于我无可憾也”。如果是“贫难小民,为饥寒所迫;无知乡愚,为匪类所引;计所得之赃,衣不过数件,银不过数两,而遽令耕颈就戮,不亦惨乎?”所以要求司法官必须认理,“我认理既真,比拟确当”,就应该没有什么冤狱了,人心也就顺服了。(黄六鸿:《福惠全书·刑名部·问拟余论》)当然,这仅仅是个人的见解,在现实中如何应用,则会是因人而异。这正是:
事方掣肘科条缚,人尚吹毛翻复寻。佛法依来都饿死,有
司读律莫教深。(清·袁守定:《有司》)
什么是有司呢?这是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本诗内的有司则泛指道府州县等“亲民之官”,他们既是行政官,又是司法官。作为司法官,他们要认理、原情,还不能违反国法。任何一级司法官都是处在上下左右包围的复杂政治环境之中,不但要求司法官具有应付上下左右的能力,而且需要他们使出浑身解数以对付各种难以预料的问题,容不得有半点疏忽和松懈。因此,对上阿谀奉承、谄媚邀宠,对左右寒暄恭维、各怀各计,对下恩威并施、沽名钓誉等各种权术,就成为各级司法官得以安位的重要条件。而戒备防范、排挤倾轧、阴谋毒计、尔虞我诈等手段也成为各级司法官得以进取的必要措施。以此之故,人性的善良博爱,人心的光明磊落,人际关系的互敬互爱,有时能在各级司法官身上体现出来;然而,人性软弱怕事,人心的谨小慎微,人际关系的冷漠无情,也常常能在各级司法官身上表现出来;至于人性的卑鄙龌龊,人心的阴险毒辣,人际关系的尔虞我诈,更会在各级司法官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但在官场上的“官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李伯元:《官场现形记·自序》),于各级司法官中习为常见,而且大凡官场上的丑陋现象和宦海沉浮,都可以在各级司法官中找到例证。这不仅说明各级司法官的政治权术的多样化,也表明各级司法官政治权术是与当时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相适应的。
各级司法官是如何面对各种各样的案件的?又是如何在各种法规科条掣肘下来认理、原情的?且看后文分解。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