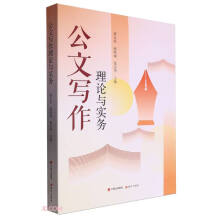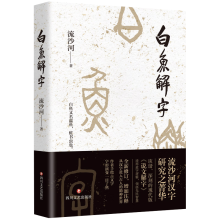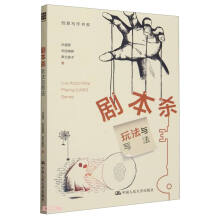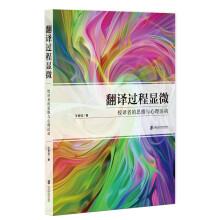则具有心理性,所以是普遍的。”他又说:“人们渐渐趋于相信句法标准(noms)是颠扑不破的,这些标准在预想不到的地方持续不断地反复出现。”(20页)
我想,这里说的关于波利尼西亚人的事恐怕不是通过对他们的语言进行全面的研究之后所得到的结果,而是根据某种先验的推测,认为谁也不能避免所提到的那些语法手段。正如丹麦哲学家克罗曼在以逻辑为基础创立了九种时态的体系之后所说的:“每一个有思想的民族的语言理所当然地具有表达所有这些时态的方式。”通过对实际存在的语言的调查,我们就会看到,在一些语言中时态的表达方式比我们预料的少得多,而在另一些语言中又多得多;在一种语言的每个句子中极其精确表达的概念,在另一种语言中却不予表达,仿佛这些概念无关紧要。“虚拟语气”尤其如此——具有单独表示虚拟语气形式的那些语言并不把它用于同一目的。因此,尽管在英语、德语、丹麦语、法语和拉丁语中,这种语气的名称相同,但严格地说,它们指的并不是同一件事。根本不可能给这些语言的虚拟语气下一个有助于我们决定何时使用虚拟语气,何时使用陈述语气的定义,更不可能同时下一个囊括虚拟语气在所有上述提及的语言中全部用法的定义。因此,难怪不管虚拟语气的含义如何延伸,在许许多多的语言中却没有可以称之为虚拟语气的东西。事实上,英语和丹麦语的历史都表明曾经兴旺一时的虚拟语气是如何日益衰退的,如今只能把它比之于那些用途不大或非常次要的、发育不全的生物器官了。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