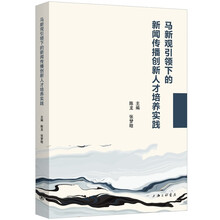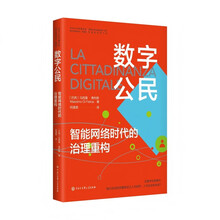这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这种非此即彼的区分或许难以用在这个现象上,用兼/和来思考或许比用非此即彼来思考更有意义。社团逾越r公与私的界限,它们形成于边际之上、在把公共的界域从私人的界域区分开来的“界限”里面。它并不那么以理性选择的个人或者以认可凭借论说来体现的言说行动为基础,而是以情感的联系、仪式的创发与共享的意义为基础,它是基于视野的合作生产而来的承认,韩国前现代儒家知识分子的先例在此特别具有指导意义。我要申论的重点在于:合乎伦理的生活与直接的、地方性的社团形式——而并非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似乎是在后现代性条件下激进的政治文化的一种较好的基础。全球信息文化与流的逻辑正侵蚀着国家的——组织的与合会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基础,所以,要在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里形成一种激进的政治或许是日益遥不可及的幻想。
在社群主义的伦理学和诸如罗尔斯(Rawls)与哈贝马斯等思想家所提出的较为自由主义的、审慎的民主伦理学之间曾有过很大的争论。刚刚讨论过的合乎伦理的生活的观念与一种实践(而非行动)的伦理学和社群主义者的观点有许多共通之处,这已经成了自由主义者、社群主义者与解构主义者三方之间的论争焦点。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伦理——从鲍曼到德里达到勒维纳斯——是一种解构的伦理、一种差异的伦理。许多关于后殖民政治的讨论提倡这样一种后现代的差异政治(Bhabha,1994),我认为,后殖民分析家——从萨义德到斯皮瓦克到巴巴——对于差异与解构的片面强调,显示他们与勒维纳斯、德里达和鲍曼一样站在解构伦理的立场。重点在于:对西方元叙事的批判并不是单单通过这种差异的政治伦理就可以办到的,也需要涉及社群、合乎伦理的生活与实践这些观念。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