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民安全感的保护来说,最重要的是减少犯罪,作为国家的责任就是预防犯罪,包括预防犯罪人再犯与预防没有犯罪的人犯罪,也就是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但无论是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都不能走向极端。如果从预防的角度来说,特殊预防的要求包括依据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与再犯可能性来确定刑罚,再犯可能性大的,刑罚要重,反之则轻。因为依据特殊预防的要求,更关注的应当是行为人的再犯可能,而不是当下之罪行的轻重,基于特殊理由的杀人很可能没有再犯可能性,要求的刑罚很低,而具有犯罪倾向的人即使实施较轻的犯罪,也可以通过这样的行为表现了行为人主观的恶,说明其再犯的可能,其对社会的威胁大,因此特殊预防也在情理之中。但“刑罚不允许出于特殊预防效果的考虑,而降低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在人民群众中间不拿刑罚惩罚当一回事,那样将动摇对法律秩序的信赖,并从而鼓励模仿”。①在此意义上,一般预防将防止他人对犯罪的仿效甚至刺激犯罪的发生作为主要目标。因此一般预防要求的主要是相同情况(这里的相同情况是指表现于外的行为状况相同)相同处理,而与特殊预防要求的相同情况(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除外)不同处理之处理机理具有相当的不同。两者相比较,德国的罗克辛教授提出了一般预防的三个优点:“首先,它可以毫不牵强地说明,在没有再犯危险的情况下,也不允许完全放弃刑罚;惩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犯罪行为没有给行为人留下什么后果,那么就容易激起模仿的兴趣。其次,一般预防的理论并不倾向于使用不明确的和法治国所怀疑的危险估计,来代替对行为的明确描述;相反,它要求尽可能准确的明确性,因为被禁止的对象必须准确地在法律中加以确定,由此才可能鼓励国民在内心产生一种对这些被禁止的特定行为保持距离的动机。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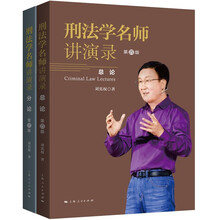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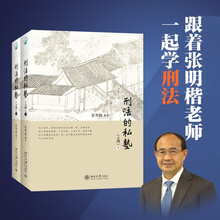


——西原春夫
人们不回家,不是因为没有家,家里的房子虽然足够大,也足够豪华,却无法得到家的感觉,所以,只能生活在别处。外面是物欲狂欢,里面是精神困顿。面对“文革”造成的道德滑坡,道德法庭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开始盛行,道德恐慌使人们陷入道德麻痹之中,于是,电视上过去常见的道德法庭变成了今天不断上演并且收视率极高的人间剧场
——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