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法意
神证时代的正义
霍贝尔在《初民的法律》一书中提到,“在初民的法律中,通过占卜、赌咒、立誓和神判等方式求助于超自然来确定案件真实是非常普遍的”。现代人或许很难想象,古代社会曾经长期流行过水审、火审、毒审、鳄鱼审等现在看来非常荒诞的审判方式。证据裁判主义的出现,只是证据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古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曾经以成文形式规定过当时处理“巫蛊之罪”的“水审法”:将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投入河中,如果他没有被溺死,就意味着河水已为他“洗白”,此人无罪,告发者应处死刑,其房屋归被告发者所有;反之,则说明被告发者有罪,其房屋归告发者所有。同样,如果某人怀疑自己妻子与他人通奸,也可以请求将其妻投入河中接受神的裁判。古代日耳曼人也曾采用这种“水审法”,但其检验标准与古巴比伦人的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河水是世界上最圣洁的东西,不能容纳有罪之人,所以嫌疑人被投人水中后若浮于水面,则证明其有罪;若沉入水中,则证明其无罪。在后一种情况出现时,嫌疑人亲友必须立即捞救,以免被神验明无罪者反被溺死。我曾经开玩笑地跟我的学生讲,如果古巴比伦人想通奸,就要提高游泳水平;如果古日耳曼人想通奸呢,则要苦练潜水技术。
神明裁判的方法有的是轻松的,有的却是异常残酷的。“抽签审”是诸多审判方式中最为轻松的一种,就像猜硬币一样,嫌犯只要在正邪两球中凭手气摸到正球,就可以被宣告无罪。“秤审”,是用秤量嫌犯体重两次,第二次较前次轻者无罪。有一种堪称古代拼吃大赛的“面包奶酪审”,要求嫌犯在祷告后,迅速吃掉一盎司的面包或奶酪,如果能顺利咽下,就会被判无罪。当然,残酷的神明裁判方法占多数:“火审”让嫌犯手持烙铁步行一段路,数天后如伤口不溃烂则无罪;“毒审”让嫌犯服某种毒物,无特殊反应则无罪;“热油审”让嫌犯用手取出热油中的钱币,无伤则无罪。还有一种令人咂舌的“鳄鱼审”,是把嫌犯丢人鳄鱼池中,观察鳄鱼是否吃他,如果安然无恙,则宣告无罪。
或许读者会认为,这些神判方式是愚昧的古人想出来的,是非常可笑的。但是,在生产力发展程度很低、人类认识能力有限的当时,裁判者难以获得可靠的证据,运用神明裁判是一种保障裁判权威性的不得已的方法。中国云南的景颇族,在20世纪时仍在运用闷水、捞油锅、煮米、斗田螺等残存的神判法处理一些民间纠纷。别看神判法看似愚昧,但有时也体现着一定的“科学”道理。例如,面包奶酪审有着心理学现象的基础,即通常一个内心紧张的罪犯,唾液分泌少,口干舌燥,毫无胃口,在吃大量食物时会难以下咽。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采用不同的证明方法,产生有罪或者无罪的几率是有很大差别的。例如,火审的结果往往不利于被考验者,秤审的果往往有利于被考验者,抽签审的有罪无罪概率则各占一半。因此,如果裁判者认为嫌犯有罪的可能性比较大,就可以采用对其不利的神判法;如果裁判者认为嫌犯清白的可能性比较大,就可以采用对其有利的神判法。而且,在选定神判法之后,结果也可能被“有心者”左右,以达到预想的效果。
英国人霍顿在一篇描述神判法的文章中讲述了一个他经历过的“鳄鱼审”故事。1938年,霍顿在太平洋所罗门群岛的英国殖民局工作,负责处理当地积压的一些案件。在一起涉及强奸的案子中,因为证据不足,他释放了被告人,但被害人的家属并不满意。在霍顿离开所罗门期间,他们请头人启用了古老的鳄鱼审判,要求把被告人投入指定的鳄鱼潭。被告人极不情愿地同意了,虽然这样做冒着生命的危险。在审判的那天上午,被告人惴惴不安地下了水,居然顺利地游过了鳄鱼潭,所有的鳄鱼都没有伤害他——这就证明他无罪!被害人家属只好接受这个结果,而且还付给了被告人一笔钱作为赔偿。霍顿对此大惑不解,通过暗中调查,他了解到了事实真相:原来,被告人事先买通了看守鳄鱼潭的老僧侣,在裁判日的清晨,把一群准备好的猪赶入潭中,鳄鱼填饱了肚子,当然就对他没有兴趣了。霍顿不由地感叹道:“原始的审判方法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简单。”
除了水审、火审、鳄鱼审等神明裁判方法外,以起誓为特征的神誓法也是神证制度的一个部分。同样是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在水审之后,规定了一种神誓方法:倘若某自由民的老婆被其丈夫所诬陷,而她并没有在与其他男子共寝时被捕,则她应当在对神宣誓后得以回其家。公元5世纪末至6世纪初,法兰克王国的《撒利法典》把“誓言”规定为“主要的证据形式”,要求当事人对神宣誓以证明自己主张或抗辩的真实性。为了加强誓言的力量,该法典还规定可以由当事人亲属或友人对神宣誓来证明当事人陈述的可靠性,这叫做“辅助宣誓”或“保证宣誓”。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双方当事人为证明己方的主张,会尽量邀请比对方多的誓言帮手,以致证明过程变成简单的“人海战术”。在阿拉伯国家中,以《古兰经》为代表的伊斯兰法律也把宣誓作为一种重要的证据调查手段。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一般先让被告人宣誓。如果被告人拒绝宣誓,那么原告人只要宣誓即可胜诉;如果原告人也拒绝宣誓,或者双方都宣誓,法官则要进一步根据誓言是否流畅等因素判明案情曲直。在现代一些有宗教信仰传统的国家,我们还可以在其法庭上看到证人手按圣经宣誓的场面。撇开宗教不谈,宣誓仪式即使在司法心理学上也有其存在的意义。当然,与动辄水浸火烤的神判法比。神誓法似乎更为文明。如果以中国式的语言来理解,神判法像是“武斗”,神誓法像是“文斗”。
更为充满“武斗”精神的是一种流行于中世纪的被称为“司法决斗”的审判方式。对俄罗斯文学史感兴趣的人或许知道,著名诗人普希金(1799—1837)死于决斗,莱蒙托夫(1814—1841)也死于决斗;而在数学史上本该大放异彩的数学天才伽罗华(1811—1832),也是因为决斗而英年早逝。与古代决斗所不同的是,中世纪司法决斗的动机不是个人恩怨,而是法律诉讼,其目的是发现真相、伸张正义。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提供给当事人的公平机会,是对付诬告的方式,因为凡是诬告者大多没有勇气和信心参与一场决定生命的决斗。但是,从其本质上而言,司法决斗只是一种特殊的神判法,比起其他随机性强的神判法形式,可以给原告和被告更多自我控制命运的机会。当时的人们认为,相对于蛮横无理的赤裸裸暴行,司法决斗还是比较文明的解决纠纷的法律手段。但是,司法决斗的历史,似乎并不总是朝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被告人开始被允许与原告决斗,后来被允许与控方证人决斗,甚至最后荒唐到被允许与法官决斗。大约在19世纪,“司法决斗”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纵观神证时代的证明制度,我们发现在非理性的背后,其实透露着人类对于真相追求的取舍态度。当囿于认识能力的限制、事实难以查清的时候,一种能保证裁判权威性的证明制度取代了对真相的过度发掘。这种证明方法或者有着司法心理学方面的基础,或者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形式公平,更重要的是,它能达到定分止争的目的。因此,即使在人类认识能力提高之后,对于神证制度好处的依赖,也使得一些地区依然延续着这种古老的审判传统。对于他们而言,对事实真相的追求受制于太多不确定的因素,而神证制度却是一种比较确定的权威,而后者在保证社会关系的安定上,有着前者法企及的作用。时代改变了,人类发现真相的能力在不断提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纠纷的解决,除了查清事实之外,尚有很多社会政策需要关注,发现真相不应该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以统帅我们的司法制度。
在事实与证据之间
2004年5月,在荷兰作学术访问时,我有幸邂逅了一次由某民间组织发起的展览,至今记忆犹新。那是在鹿特丹的一座大教堂里,我们意外发现那里正在举办关于“侵华日军暴行”的展览,有详尽的图片、中文繁体和英文双语介绍,还有专门的英语解说人员。当那位慈眉善目的老先生知道我们是从中国来的时候,语气中带着激动和兴奋,他说,很多人不了解当年日军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现在有一部分日本人也不肯正视这段历史,反而篡事实,所以国际社会有义务让更多人知道真相。我深深地为他这种行为所打动,但同时也在心底盘旋着一个问题:在中国人、日本人和国际社会的眼中,日军侵华的“事实”分别呈现什么面目呢?
作为中国人,我们耳熟能详的是“九·一八”、“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即使如我辈并未亲历者,也对这段历史笃信无疑;但是第一次站在域外审视这个问题,却发现有人在为证明该“事实”而不懈努力!环顾邻邦,还真是有人在“日军侵华”上搅局:在某些日本人眼里,那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他们的教科书也在告诉日本的青少年,所谓的“南京大屠杀”根本不存在!日本国内一些右翼分子也声称,经“研究”发现日军在“南京事件”中并没有对当地平民实施有组织的屠杀行为。我想,如果是在日本接受这种教育长大的人,是很容易相信日本右翼分子谎言的!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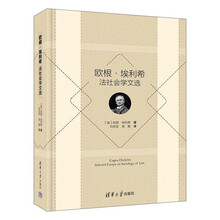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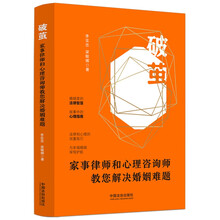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何家弘
我一贯认为学者不应该只生活在“象牙塔”中,而应当透过理论的迷雾,去关注来自现实的事件。而体悟的过程中的一些思想火花,就是如《法律的侧面》这样反思性的法学随笔。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陈瑞华
《法律的侧面》透过对身边社会现象的细微考察,反思“书本上的法”和“行动中的法”的距离,剥去宏大叙事下法治的光芒,还原一个真实的法律世界。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明楷
法律的真谛不在法律条文本身,而体现在运用法律分析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之中。《法律的侧面》娓娓道来,充分体现了这一精神。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 顾永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