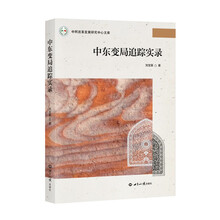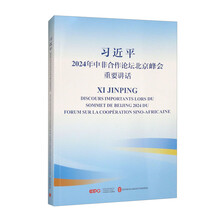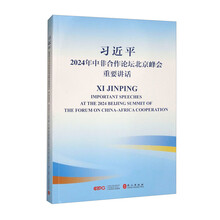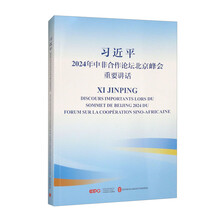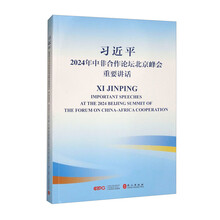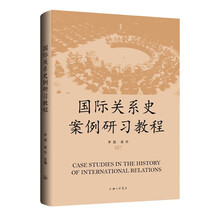第一部分 德国当代外交政策的起源与发展
第三章 德国当代外交政策与大国关系
第一节跨大西洋关系
德国的跨大西洋关系,也就是德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德国外交政策中的核心支柱之一。无论是冷战时期,还是后冷战时期,无论是波恩共和国,还是柏林共和国,在德国的外交定位和外交取向中,美国作为“大西洋联盟”中的核心领导,始终是德国对外关系中的优先考虑对象和关注焦点。
在冷战时期,德国始终致力于建立德美“联盟”和德美“特殊关系”,并心甘情愿地扮演美国的“忠实的盟友”和“听话的小伙计”角色,在对外政策上对美国亦步亦。趋。这种政策的确立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方面,在面临来自苏联的强大军事压力面前,德国在安全方面需要美国的保护和保证;另一方面,战后德国在经济重建、获取完整主权、实现民族的最终统一等重大经济政治问题上都仰赖于美国的襄助和恩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战后的德国坚定地选择了亲西方、特别是亲美的路线。正如阿登纳在成为联邦总理前夕所写到的那样:“在外交政策领域,我们的路线确定。它首要的方向是建立与西方邻国的密切关系,特别是与合众国的密切关系。”而战后,出于遏制和对抗苏联的目的,美国对于德国(西德)的扶持也不遗余力。在经济上施行马歇尔计划,帮助德国重建其衰败凋敝的经济,在政治上促成了《伦敦一巴黎协定》的签订,使穗国重新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并获得了加入北约、重新武装自己的资格。由此,德美之间形成了一种“天然伙伴关系”,一种由德国人的感激、折服与投靠的情感水泥同德、美之间几无冲突的互补利益钢架共同构筑而成的基础牢固的友好关系。
但是冷战时期,在这种“天然伙伴关系”背后,美德之间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分歧和不和谐因素。从阿登纳20世纪60年代早期“亲法疏美”的戴高乐主义倾向,到勃兰特在新东方政策上罔顾美国意见的独立姿态,从施密特与卡特总统的交恶,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导弹危机(missile crisis)”,两国在对外关系上不再是一唱一和,亦步亦趋,而是开始凸显出不同的政策优先着眼点(policy preferences)。而且随着德国经济实力的迅速窜升,随着德国与苏东地区在对外关系上的缓和,德国对美国的依赖性逐渐减少,独立性和自主性却日益攀升。正如1980年施密特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所指出那样:“我们不再被迫毫无批判地采取美国人的任何立场了。今天,美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关系与15年前或20年前不同。那时我们处在从属地位,今天我们是美国的一位重要伙伴。”但是,在冷战这样一种极端两极化的世界格局当中,德国争作美国“平等伙伴”的雄心只是美丽的一厢情愿而已。因为无论是从力量对比,还是从相互的依赖度上看,德国和美国都处于一种绝对的“不对称”地位:德国所求于美国的多,而相对而言,美国所求于德国的少。这样,在对美关系中,德国并没有多少可以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在战略空间上,德国也缺少足够的回旋余地。而且,在冷战期间,德国在西方世界的政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其与美国所结成的紧密同盟,不仅如此,德国的一切外交活动都是嵌入在由美国所主导的西方政治架构(如NATO)当中。在这种背景下,德国的政治精英和民众都维持着一种“跨大西洋认同”,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具有共享价值的大西洋共同体的一员,所以,德美之间即便存在着争吵和利益分歧,也被看成是“属于家庭内部的争吵”。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德国的重新统一以及冷战的结束,整个世界格局经历着剧烈而复杂的变动。在这种背景下,德美关系也开始出现了适应性的调整,由以前的美国的完全领导权和德国的依赖转向一种较平衡的伙伴关系。随着两极格局的解体,以及一个相对平衡的多极世界的出现,德国的安全环境大大地改善了,在这样的条件下,德国在冷战时期对于美国的无条件忠诚已无多大必要了,德国大战略的中心不再是培植与美国的紧密关系,以反对一种可辨知的苏联的威胁,而是去寻找一种确当的(appropriate)平衡,在与美国这个超强大国(hyperpower)的良好关系和与欧洲其他大国——包括其东边的欧亚大国——的良好关系中寻找一种确当的平衡。这样,美国就失去了大西洋共同体的当然的领导者的地位,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开始逐渐地把美国看作是伙伴,而不是领导。与此同时,在跨大西洋两岸,美德各自在对外战略方面都做出了结构性的调整。首先,在苏联解体,俄罗斯沦为一个二流国家的情况下,美国的战略重心开始调整,由以前的欧洲向亚太和中东地区转移。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把再度统一的德国看作是美国在欧洲建构一个新的安全秩序的核心伙伴。出于这样的战略意图,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美国领导人——从老布什到克林顿——都希望德国在欧洲肩负起更大的责任,扮演一个欧洲领导者的角色。如老布什希望德国能成为美国“领导权上的伙伴(Partnership in Leadership)”,而几年之后,克林顿则称美德之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关系(Unique Relationship)”。但是,为了消除其欧洲邻国的疑虑和维护法德轴心关系,德国婉拒了美国的邀请。其次,与美国的战略重心的转移相一致,德国的战略重心也出现了转移,由“华盛顿”向“巴黎”转移。随着来自于东部的威胁的消失,随着美国对于欧洲安全的关注度的持续下降,随着EU作为多边合作的框架在地区和全球事务的重要性方面目益凸显,德国开始一改其在巴黎和华盛顿之间搞平衡和“等距离外交”外交的传统,开始让天平向欧洲和巴黎倾斜,开始强调“欧盟”作为一个国际行为体的自主性和独立行动能力,开始大力提倡并着手建立截然不同于美国的“欧洲安全与防务身份”。例如,在欧洲,法国一直强调需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具有内聚力的CFSP(欧洲共同外交安全政策),ESDP(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以便它可以在那些美国不想介入的地方有能力在NATO的框架以外展开行动。但是与法国不同,德国并不试图把CFSP、EDP看作是在多极世界中抗衡(counterbalancing)美国的一种有效工具,也不打算把EU发展成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对此,有学者评论道:“巴黎想把欧盟发展成为美国的一种抗衡力量(a counterweight),而柏林则把一个强大的欧洲看作是美国的一个可信赖的伙伴。德国想维持一个大西洋联盟,以作为行动的跨大西洋框架,作为危机管理和维持和平的一种工具。”这意味着,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德国虽然不再把美国看作是当然的领导,但也不会把美国视为当然的竞争对手,而是把美国看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伙伴。实际上,尽管冷战结束了,维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以及在NATO框架下维持美国对欧洲事务的高度关注都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利益。尽管赋予法德关系以重要性,德国仍然是美国的忠实的盟友。事实上,正是美国政府第一个站出来完全支持科尔的寻求德国“再统一”的雄心,这是德美关系中的一个标志(landmark)。对于德国而言,在冷战结束后与惟一的超级大国保持亲密关系仍然是必不可少的。正是出于这种立场,德国一方面强调强化NATO和EU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合作,认为EU的外交政策行动和发展必须置于与美国磋商之下,并在与美国的磋商中建构。另一方面,德国努力阻止跨大西洋关系中的未来可能的破裂(rupture),作为一个欧大联盟(Euro-Atlantic Union)的热心支持者,德国致力于美国主导下的NATO东扩,致力于提升美国对于欧洲安全——特别是在巴尔干的安全——的介入,致力于把合作由安全政策领域拓展到经济和文化领域,致力于按照西方的意识形态来重构欧洲的政治经济版图。
但是,在世纪之交,随着小布什的上台,随着美国国内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美国外交政策中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从而造成了德美关系中的结构性变化和冲突。在国际事务中,德国外交中的强调协商、对话的多边主义传统,以及其后主权的“文明国家”身份,与美国外交中的单边主义作风和在国际事务中滥用武力的黩武主义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从其上台伊始,小布什总统就由于其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我行我素的做法遭遇了德国的极大的不信任。德美之间的第一个重要分歧是由小布什政府不顾德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而计划发展“国家导弹防御体系(NMD)”引发的。德国人认为美国这一举动违反了“反弹道导弹条约(the 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而对德国而言,这一条约对于确保美俄关系的持续稳定以及欧洲的长久和平是极为重要的。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