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在我的国家,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被视为二流作家。<br>很长一段时间,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位自由思想的先行者、这位20世纪末反极权主义潮流的先知、这位汉娜·阿伦特的先驱——倘若我们对他的重要性早有了解——或许能为我们节省宝贵时间,使我们免于卷入旷日持久的毫无意义的争论中。法国的大学几乎从不教授这位启蒙使者的著述。<br>事实是在我前半辈子的时问中,同我的同龄人一样,我把这位理论家——他恰巧还是位好作家——看做是一个旧式的、悠闲的贵族,一位懒洋洋的思考不走极端的专家,一个富于狡辩、过于审慎的鉴赏家,一个无病呻吟的多愁善感者,一个悲伤的自恋者,一个乏味的、反动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个爱说教的积极分子,一个以自命作家来自娱的机智的男人,一个失败的政客,一位孟德斯鸠苍白的仿效者;然而和伯父夏多布里昂(他似乎抢占了所有具有吸引力的角色)相比,他是个轻量级的人物。他写的回忆录只能当做一个消逝时代的佐证来读。之前他还写过一本冗长的游记,但迥异于这类专门题材的作品,几乎马上被人遗忘。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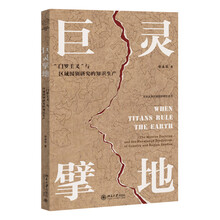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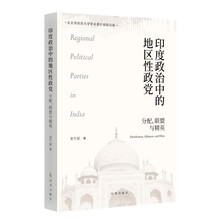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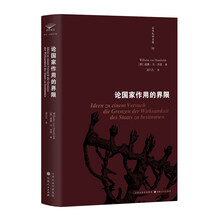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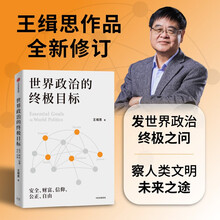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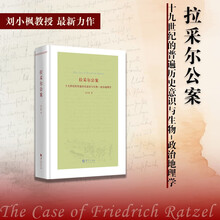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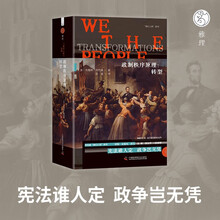

——《纽约时报》
美国没有任何一位哲学家能够集莱维的魅力、文笔和政治参与于一身。
——《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