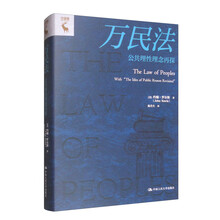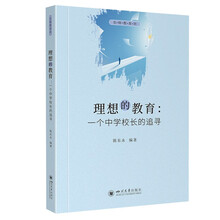这就是海德格尔所谓的基本本体论。在这个意义上,“不能经验”的就是“不可理解”的。因此,我们只要对于一个“人类之初”和“人生之初”的世界作出理解,就不能不把它看作是一个可以经验的世界。这个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是相关的,可理解的,也是可经验的。否则,就是不可理解的,甚至是不可说的。
因此,我认为,在讨论“人生意义”的问题时,把一种“不可经验”的世界作为“可理解”的世界来描述,可能只是一种没有内容的纯形式的语言游戏,没有实在的意义。
由此可见,从表面上看,你的解释似乎没有问题,例如:“庄子认为,在人生之初和人类之初,人均处于与世界整体本身或道同一的状态。在这时,人生和社会均没有问题。但是,随着人的心灵的出现或成熟,人们制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区别,首先是物我的区别,然后是物物的区别,接着大小、是非、美丑、善恶等等区别。有了区别,人们便要争夺。人生因此便出现了重重问题,并进而丧失了意义,社会也最终陷入大乱。要解决人生和社会问题,庄子认为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重新回到与世界整体本身或道同一的状态,而做到这点的唯一方式是安命,进而齐物,最终说来是心斋,即杀死经验主体的区别心。”即是让经验的主体退回到一个与经验世界全然异质的不可经验的世界。
但是,在我们的语境中,只要你描述了“人类之初”和“人生之初”的情况,就仍然是“可经验的”,也是“可理解的”。经验和理解在这里无法割裂。“经验世界”与“不可经验的世界”的不同、对立,只具有逻辑上的意义,不能解决任何“人生问题”。
讨论到这个地方,可能才触及问题的核心。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