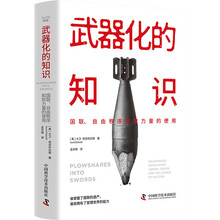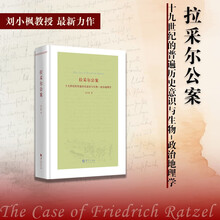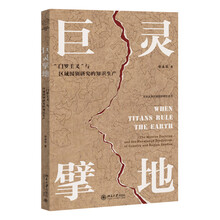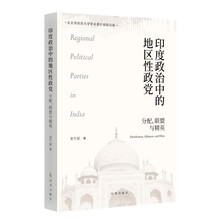不过,事与愿违。世俗化运动的兴起与蓬勃高涨,又加剧了天主教保守派与共和派之间的矛盾,双方在宗教修会(congregations religieux)是否可以被视为社团,是否应当适用“普通法”(loi commune)的问题上僵持不下,结社法案因此也成为其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仅就第三共和国参众两院提出的结社提案、草案以及相关报告的数量而言,我们便可以管窥世俗化对法国结社合法化进程的重大影响。1901年7月1日结社法颁布之前,人们曾经向议会提交了33个结社法提案。除了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的提案经过议会的修改与讨论,最终出台1901年结社法,以及1871年贝尔都德的报告和1882年茹尔·西蒙的报告得到简短讨论外,其他提案皆因为世俗化斗争或修会问题而被搁置。所以,努里松和罗桑瓦龙皆认为,反教权斗争和修会问题是结社法案屡屡流产的主要原因。
以上四种解释模式虽各有所长,但也有各自的缺陷。尽管它们分别可以阐明某个阶段或某个政权的反结社现象,但都不能为法国从禁止结社、宽容结社、肯定结社到鼓励结社的过程提供一种系统的解说。
笔者以为,无论是历史环境论、阶级对立论、公意政治文化论,还是世俗化论,都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从根本上说,近代法国在结社合法化的道路上所遇到的困难和挫折皆肇始于个人主义或现代民主的内在紧张。现代民主的核心是个人权利原则,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个人主义。这是不可否认也无庸置疑的基本原则。但是,个人权利是什么?它与家庭、地方、风俗、历史、宗教、社会和国家有什么关系?由纯粹的个人或原子化的个人所构成的社会是否可能?对于这些问题,由于种族、出身、宗教信仰、语言文化以及性别的不同,人们会产生分歧、矛盾甚至冲突。所以,近代法国在法国大革命、世俗化等重大问题上的争论及其对结社合法化的影响,主要来源于民主原则本身的这种内在的矛盾性。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