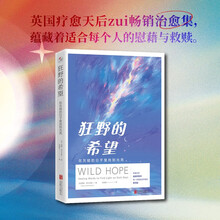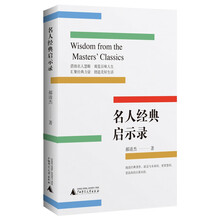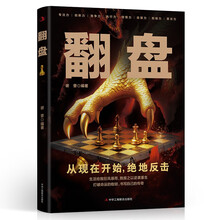泰勒先生回来了。我问他有我的信没有。“没有,什么也没有”。“要有耐心,”我对自己说,“他妹妹很快就要来了。”泰勒小姐回来了。“我没有给你带来埃热先生的片言只字。”她说,“没有手书,也没有口信。”等我回味过来这话的意思,我对自己说:如果别人遇到同样的情况,我也会这样对他说:“你应该想开些,首先,不要为你所不该遭到的不幸而悲伤。”我竭力忍住眼泪,不发怨言。
可是,当一个人不抱怨,当他试图用暴君的手腕强压自己时,他的官能是要起来反叛的,他要为外表的平静付出难以忍受的内心冲突的代价。日日夜夜,我既不能休息,也不得安宁。如果我睡着了,磨人的梦魔就来缠扰:我梦见你,老是疾言厉色,老是乌云满面,老是冲着我大发雷霆。如果我采取了再一次给你写信的办法,那么,先生,请原谅我吧。要是我不努力设法减轻生活的痛苦,我怎能忍受生活呢?
我知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一定会不耐烦。你又会说,我在发神经,说我思想阴郁等等。也许是这样的,先生。我不想替自己辩解,我甘受任何责难。我只知道,我不能、不愿听天由命,完全失去老师的友谊。我宁愿忍受生理上最大的痛楚,也不愿让我的心被痛苦的悔恨撕裂。如果我的老师全部收回了他对我的友谊,我就毫无希望了。如果他给我一点点友谊——只消一点点——我就满足了,我就快乐了,我就有理由活下去、工作下去。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