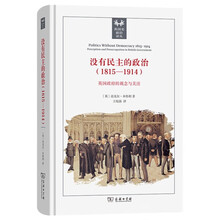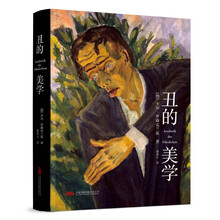第1章 欧文·白璧德及其“人文主义”思想<br> 第一节 白璧德:美国“人文主义”思想奠基人<br> 欧文·白璧德(Irring Babbitt,1865—1933)1865年8月2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城市代顿(Dayton),1933年7月15日病逝于波士顿康桥(Cambridge)家中。他的一生经历了美国历史上几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首先,1865年乃是美国内战——南北战争(theCivil War,1861—1865)——结束之年。南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点,北方的胜利为美国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彻底扫清了道路,使美国在19世纪后期迅速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以令世人瞠目的速度进入了现代。毕生以批判现代社会诸问题为务的白璧德,正是生于这样一个划时代的年份。<br> 1865年之后,美国开始了战后重建工作,在持续了十多年的重建期(the Reconstrucion Period,1865—1877)结束后,美国迎来了经济飞速发展的一个时期,铁路、石油、钢铁、电力诸行业突飞猛进,“强盗大亨”(robber’barons)横空出世,财富大量积累在个人手中,贫富分化日益加剧,政治趋于腐败,各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这个经济空前繁荣,然而政治日趋腐败、社会生活经历种种前所未有之巨变的时期,史称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1878—1900);美国正是在这一时期完成了从农业一农村联邦政府向工业一城市民族国家的转变。<br> 美国自建国以来便开始了历经百年之久的西进运动(the West,ward‘Movement,)。当战后重建工作初步完成、工业化进程如期实现之后,美国重新拾起40年代流行的“天命论”(the Manifest Destiny),开始“敕天之命”、走上对外扩张的老路。由于其领土在内战前已经从大西洋沿岸一路扩展到了太平洋沿岸,到了经济实力相对雄厚的镀金时代,“领土扩张论者”们(the expansionists)顺理成章地将目光进一步投向了太平洋与亚洲地区。1898年美国在美西战争(me Spanish-American War)中轻松获胜,领土扩大到了亚洲地区,自此“扩张论”(expansionism)在美国罡风日劲。以这场“辉煌的小战争”(the Splendid 12ttle War)为标志,美国的对外政策日趋强硬,并由此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the Age of Imperialism)。<br> 从文化思潮方面而言,这一时期人们的观念同样发生了剧变: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0f Species,1859)在1860年通过哈佛学者、博物学家阿萨?格雷(Asa Gray,1810—1888)的评论被迅速介绍到了美国。由此达尔文的“进化论”(idea of evohationary change)与“自然选择论”(idea CIf natural selection)在美国学术界、思想界,乃至整个社会中激起了极大的反响与争议。如果说“进化”是经由“自然选择”而产生的,那么这便取消了“造物主”存在的理由,从而构成了对“创世论”(creationism)这一传统世界观的直接颠覆。围绕这一关键论题,美国思想界在19世纪70年代初展开了一场“科学与宗教之战”(the Warfare 0f Scienceand Religion)。其间坚决抵制这一新观念者有之,与之妥协者有之,对之全面接受、乃至热情捍卫者亦有之,而论争的后果则是“进化论自然主义”(evolutionary naturalism)思潮席卷全国。1882年,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学的英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斯宾塞(Hefbett Spencer,1820—1903)访美,受到了空前盛大的欢迎,当时的美国人的热情程度绝不亚于杜威(John Dewey,1859—1952)访华时(1919—1921)兴奋的中国人。此后美国人开始仿效斯宾塞氏,将进化论引入政治经济学、哲学法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从而社会观念从整体上发生了改变——“科学与宗教之战”比中国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科玄之争”(1923)整整早了半个世纪,然而就论争的内容、对立阵营的构成及其后果而言,则似乎颇有异曲同工之妙。<br> 此外,作为文化储积、传播之地的传统型学院,亦在时代风潮的影响下进行着相应的变革,逐渐向现代意义上的大学转变。同时,这些得风气之先的教育机构反过来又开始引领时代风潮,对社会观念的转变施加了最为有力的影响。事实上,“科学与宗教之战”最初便是在以哈佛大学教授为主的学者之间展开,此后扩展到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密歇根大学等高校的学者圈内并最终由科学在更广泛的知识界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德国大学成为美国大学争相模仿的对象,美国各大学纷纷建立了名目繁多的新学院,德国式的“严格科学的研究方法”(strengwissenschaftche Methode)渗透到了各个研究领域。一方面旧式经典科目逐渐被自然科学课程所取代,另一方面自然主义的科学思潮开始入侵传统(即人文)学科,科学的语言文献学(scientific philology)的方法开始被用来研究文学本身。此外史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其他传统学科无一不受到科学“方法论”的侵染。伴随着美国现代工业、科技的发展,社会日趋世俗化,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便是:昔日的大学最初不过是以培养神职人员为目的、以研习希腊/拉丁经典为手段的附属性机构,如今已经和教会彻底脱离干系,成为鼓励科学研究、提倡科学精神的要塞,并逐渐演变为信奉科学这一新信仰(secular fairh)的世俗堡垒。科学与宗教之殊死斗争,以科学在大学取得全面胜利而告终。<br> 总而言之,从1865年到19世纪末,美国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潮各个方面均经历了前所未有的转型。白璧德便是在美国历史上的这个转型期度过了自己的青年时代。<br> 白璧德远祖系英人Edward Bobet氏(后转拼为Babbitt),1643年定居于马萨诸塞之普利茅斯。曾祖与祖父分别是哈佛与耶鲁神学院的毕业生,他们作为公理会牧师,坚持“饱学教士”的传统而反对福音狂热与泛滥一时的反理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可以说对学问与传统的尊重构成了其家族本身的传统之一。然而,白璧德的父亲埃德温(Edwin Babbitt,1828—1905)却在时代风潮波及之下,热衷“科学”研究与试验,自命为“医学博士”并著有关于“色彩疗法”(ChromopathiC)等迹近“伪科学”的著作,热心社会公益却忘记“慈善始于家庭”,在妻子早丧之后,不顾子女年幼送交亲戚看管,致使白璧德在年幼时便备尝生活之多艰。白璧德传记作者布伦南(stephen C.Brennan)曾论及埃德温对白璧德的“巨大影响”:“埃德温在诸多方面均代表了典型的美国19世纪的观念,代表了白璧德日后所憎恶的一切。”白璧德此后曾严厉批判治学者“印象主义”和“浅薄涉猎”(dfilettanteism)的倾向,并对“人道主义大忙人”深恶痛绝,这或许与其童年记忆多少有些关系。<br> 白璧德1881年从辛辛那提市伍德沃高中(Woodworld High School)毕业,学习成绩优秀,但由于经济原因未能进入大学。因此 1902年,白璧德在作了八年讲师之后被升为副教授。他迟迟得不到提升的主要原因,一则是由于其“科研工作量”的不足,二则是由于工作“小环境”不佳所致:他在哈佛近四十年的教书生涯(1894—1933)中,始终与学校及其所在系别的主流教育/文化观念格格不入,基至到了势如水火的地步。<br> 这一时期,他仅发表了三篇论文与其他一些零星的文字(包括评论五篇,书评、翻译文章各一)。据他本人所云,不轻易著述的原因有二:一则为了“观点蓄而不发……直至通过反思使之彻底成熟”,二则乃是出于“审慎”。不过,他最早发表的“The Rational study of the Classics”(《古典的理性研究》,1897)一文便实在称不上“审慎”,这篇文章针对美国文学研究的现状(亦即针对哈佛的文学研究者们)提出了相当犀利的批判;而他在成为副教授当年发表的“The Humanities”(《人文学科》)一文则更进一步,矛头直接指向了艾略特校长及其主持的“新教育”改革。这篇文章逐一批判了哈佛当时正在施行的“选课制”(the elective ystem)、“三年学位制”(the three years’degree)诸项重要的改革实践,批评了“实用教育”(practical edlacation)、“专业化”(specialiTation)等教育理念,并讥讽了“博士学位崇拜”(the fetish worshiD of thedoctor’s degree)、重“大学”(university)而轻“学院”(college)等流行风气,甚至直接点名批评了艾略特本人,将之视为“倾向于单纯使用量化检测手段并用自然科学术语来表达一切事物”的“科学自然主义者”(scientffic naturalist),认为这种人实与“情感自然主义者”(emotional naturalist)“殊途而同归”云。他没有被“解聘”,并且居然能够安然升为副教授,只能说明心系改革的艾略特校长不拘小节、有容人之雅量。<br> 然而,白璧德与“小环境”的斗争并未到此为止。作为一名年轻教师,他还曾在系务会议上公然向艾略特校长提出反对意见,并在1902年之后以更为犀利的笔锋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文章与1902年以前的文章已经开始有所不同:除了就哈佛“现行课程考察制度”、“学位制度”、“现行博士制度”以及“文学研究”诸题目展开讨论之外,其谈锋所向已不仅限于大学教育、文学研究等领域,而是开始涉足更广泛的文化、社会思潮诸领域,特别是其中关于“古今之争”(the Quarrel of Ancients and Moderns)、现代“进步观念”(the notion of Progress)、“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以及“现代”(modern)诸问题的讨论,事实上已构成了此后发起的“新人文主义”运动之最初的思想资源。<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