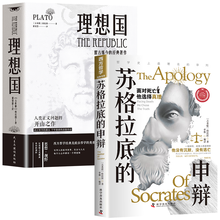2
实用主义和浪漫主义
(哥伦比亚版本)
实用主义的核心,是拒绝接受符合论的真理观,以及“真的信念是对实在的精确表象”这种看法。而浪漫主义的核心,则是“想象力优先于理性”这一论题——断言理性只能追随想象力开拓的道路前进。这两种运动都是对如下这种看法的反对:有某种非人类的事物在那里存在,而人类则需要与它相接触。在今天的演讲中,我想追踪如下两者之间的一些关联:一是詹姆斯和杜威对海德格尔所谓的“西方存在一神学传统”的拒斥,一是雪莱断言诗“既是知识的核心,又是知识的边缘(circumference)”。
我拟从对真正的实在者①的形而上学的、存在一神学的探索开始。常识在一事物表面的颜色和其真实的颜色之间、在天体表面的运动和它们真实的运动之间、在乳脂替代品和真正的奶油之间、在真假劳力士表之间作出区分。但只有那些研习过哲学的人才会追问,是否真劳力士表真的是实在的。[除了研习哲学的人之外]没有人认真对待柏拉图在以大写字母“R”[开头]的实在(Reality)②和以大写字母“A”[开头]的表面现象(Appearance)之间作出的区分。这一区分是形而上学的宪章。
巴门尼德通过构想出以大写字母“R”[开头]的实在的观念,发起了西方哲学传统。他将树、星辰、人类和诸神全裹进一个被称作“一”的全面之物中了。然后,他从这一全面之物那里往后退,宣称它是惟一值得知晓的事物,但永不能为有死的人所知晓。柏拉图因对某种甚至比宙斯都更庄严、更不可接近的事物的这一暗示而着迷,但他更乐观。柏拉图提出,为数很少的一部分有天赋的有死者可以通过效仿苏格拉底,赢获通达他所谓的“真正的实在者”的道路。自从柏拉图以来,就一直有人担心我们是否能赢获通达实在的道路,或者是否我们认识机能的有限性使得这样的道路不可能了。尽管如此,没人担心我们是否在认知上可以通达树、星辰、奶油或者手表。我们知道如何把关于这些事物的一种合理的信念与一种[关于它们的]不合理的信念区分开来。如果“实在”一词仅仅被用来指所有这类事物的集合,那就不会产生任何关于通达它的道路的问题了。[如果这样的话,]这个词永远也不会被大写。但是,当它被赋予了巴门尼德和柏拉图所赋予的那种意义之后,没人能说清楚什么能被视作对一种关于由此术语所指的事物的信念的辩护。我们知道如何更正我们对物理对象的颜色、行星的运动以及手表的起源的信念,但我们不知道如何更正我们对于事物的最终本性的形而上学信念。形而上学不是一门学科,而是一个理智游戏场。
日常事物和实在之间的区别是这样的:当我们学会如何使用“树”这个词时,我们就自动获得了关于各种树的许多真信念。正如戴维森主张过的,我们关于像树这一类事物的大部分信念必定是真的。因为倘若某人认为各种树都很典型地是蓝色的,而且它们从不超过两英尺,我们就会下结论说,不管他说的是什么,那都不是树。戴维森的观点是,在我们提出“是否关于某一事物的某个特殊信念错了”的问题之前,必定有了许多为大家所共同接受的关于这一事物的信念。一旦这样的问题被提出来,那些被共同接受的真理就都可以被质疑,尽管它们显然不可能一下子全都[受质疑]。一个人只能在愿意接受常识就某物持有的其余观点时,才能不认同常识就它所持的某一观点。否则这个人就无法说出他要说的话了。
然而,涉及实在时,没有任何像常识这样的东西。不像有关树的情况,不存在为俗众和有学问者所共同接受的任何平常的说法。在某些知识分子群体里,你可能发现他们一致赞同实在的终极本性是原子和虚空。在另外一些人那里,你发现他们一致同意实在的终极本性是非质料的、非时空性的、神圣的存在。形而上学家们之间关于实在之本性的争吵之所以看起来如此滑稽可笑,是因为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感到可以随意拾取他们最喜爱的某些事物,并宣称它们具有存在论上的特权地位。尽管实证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和解构主义者们作出了一些杰出的努力,存在论在当代哲学家那里仍然像在德谟克利特和阿那克萨戈拉的时代一样流行。
我关于为何存在论依然如此流行的猜想是,我们仍然不情愿对浪漫主义的如下论点让步:想象力设立了思想的边界。古代的哲学与诗之争和晚近的科学与人文之争,其核心就是哲学家们和科学家们对于如下看法的恐惧:想象力实际上可能会被完全接受下来。但事实的确如此。想象力是语言之源,而思想如果没有语言就是不可能的。对这样的思想的反感促使哲学家们受到这样一种需要的困扰:要获取通达实在的某种道路,这种道路没有被语言的使用所中介过,并先于语言的使用。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