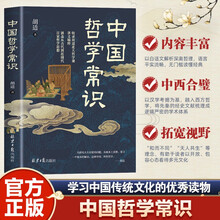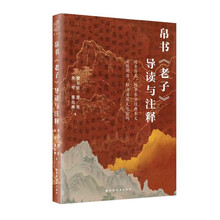不过,古代日尔曼法律传统中还是出现了一种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公私古典之分的“公共”与“特殊”(“gemeinlich”und“sundefiich”/“commen”und“particular”)之分。这种对立涉及到的是封建主义社会关系当中的共有因素。公有地(Allmende)为公共所有;井水、市场也是公用的(loci com-munes/loci publici)。从语言史来看,这种“共有制”和(今天所说的)公共福利(commonwealth/publicwealth)是一脉相承的,它和“特有制”相对应。这是一种私有意义上的特有,我们今天把特殊利益和个人利益等同起来,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在封建社会的法律架构里,特殊性另一方面也指某些人享有特殊权利,如豁免权和其他特权;从这个角度来看,特殊性和豁免权才是封建领主所有制的真正核心,同时也是其“公共性”的核心。只要把这些范畴从封建制度中抽离出来,就会发现,日尔曼法和罗马法对它们的分类刚好颠倒了过来——普通人变成了私人。这层关系在“国家卫士”和“私人卫士”这样的用词上可以看得-清二楚——普通人默默无闻,没有“公开”发布命令的特权。在中世纪的文献中,“所有权”和“公共性”是一个意思;公有意味着领主占有。“公有”作为共同所有与“公有”作为摆脱领主特权的“普遍所有”这样一对意义矛盾,至今依然表明,合作社的构成因素和建立在封建所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是融为一体的。
从社会学来看,也就是说,作为制度范畴,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和私人领域相分离的特殊领域,在中世纪中期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存在的。尽管如此,封建制度的个别特征,如君主印玺等具有“公共性”也并非偶然;同样,英国国王的公共性也不足为奇——因为所有权有一种公开的代表形式。这种代表型公共领域不是一个社会领域,作为一个公共领域,它毋宁说是一种地位的标志。封建领主的地位,不管处于哪个级别,都和“公”、“私”等范畴保持中立关系;但占据这一地位的人则把它公开化,使之成为某些“特权”的体现。代表概念在现代法学理论中还有。现代法学诀为,代表“只能出现在公共领域里,……没有私人”代表这一说。而且,“死掉的东西、价值不大或没有价值的东西、低级的东西都用不着代表。它们不够高尚,因而无法脱颖而出,进入公共领域而真正存在。伟大、崇高、尊贵、荣耀、尊严以及尊敬等词汇总是适合于这种有代表力的特殊存在”。国家代表或具体的议会代表和这种代表型公共领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种公共领域依附于现实中的领主,从而赋予其权威以一种“神光灵气”。如果君主把世俗的领主和精神领袖、骑士、教土以及城市代表都笼络到自己周围,(或者像1806年发生在德意志帝国的那样,国王邀请诸侯和主教、席国主管、帝国各直辖市代表以及修道院院长等参加德意志帝国议会),那么,所组织起来的就不是一个能够代表他人的代表会议。只要王侯和各特权阶层本身就是“国家”(朕即国家),而不只是国家的代表,那么,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是可以代表的;他们在民众“面前”所代表的是其所有权,而非民众。
以上论述想要阐明的是,意义理解方法使得我们熟知的认识客观性成了问题,因为解释者即便没有自己的行为意图,也必须依靠对交往行为的参与,并且看到自己面对的是客观领域自身当中出现的有效性要求。他必须用合理的解释来处理把有效性要求当作指南的行为的内在合理结构。解释者若想把这种解释中立化,就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即把自己明确为一个客观的观察者;但是,从客观化的立场出发,根本无法进入意义的内在关系当中。因此,在交往行为的理解与合理解释命题之间,存在着一种基本的关系。这层关系之所以具有基础意义,是由于交往行为不能从两个层面上加以解释:第一个层面是它的实际过程,第二个层面是一种理想型的过程。没有自身行为意图的潜在参与解释者,如果想通过描述来把握实际沟通过程的意义,就必须满足这样的前提,即根据他和直接参与者共同拥有的基础,来判断他所面对的共识与异议、有效性要求与有力的理由。社会科学解释者无论如何都必须满足这样的前提,因为这是他描述交往行为模式的基础。正如我接下来想要阐明的,交往行为模式是从这个模式更加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前提中产生出来的。
d.合理解释的不可避免
如果我们认为——个行为是目的行为,我们也就假定,行为者提出了一定的本体论前提;行为者所说的是一个客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会有所认识,也有所追求。与此同时,观察行为者的我们,也根据主观世界提出了本体论的前提。我们在“世界”与行为者眼中的世界之间进行了区分。我们通过描述可以确定行为者所说的真与(我们认为的)真之间的区别。在描述性解释与合理性解释之间进行选择,关键在于,我们决定,对于行为者在他的意见中提出的真实性要求和在目的行为中提出的与真实性相关的有效性要求,当作可以客观评判的要求,不是予以拒绝,就是加以认真对待。如果我们拒绝承认它们是有效性要求,我们就把意见和意图当作主观的事物加以处理,也就是说,如果意见和意图是行为者面对公众表现或表达出来的,它就必须属于行为者的主观世界。这样,我们也就把真实性要求和有效性要求中立化了,具体做法在于,我们把意见和意图当作表现性的表达加以处理;而这些表达只能从真诚性和本真性的角度加以客观评价。而这些视角在没有公众的孤立的行为者的目的行为中没有什么价值。相反,如果我们像行为者本人那样把他的行为当作是合理的,并予以认真对待,那么,我们也就对他(心目中的)效果进行了批判,而批判的基础在于我们的知识以及我们对于目的理性行为的实际过程与理想过程的比较。如果我们赋予行为者不同于目的行为模式所要求的其他潜能,行为者就会对我们的批判作出回应。而只有当行为者本身能够接受人际关系,并作出交往行为,甚至参与到带有各种前提的特殊交往过程当中,才能形成双向的批判。所谓带有各种前提的特殊交往,就是我们所说的话语(Difkurs)。
我们可以为如下情况提供一种类似的思想实验,即:我们把一种行为描述成规范调节的行为。在描述过程中,我们也就假定了,行为者所应对的是第二个世界,即社会世界,在这个世界中,行为者可以把符合规范的行为与偏离规范的行为区分开来。与此同时,作为观察者,我们也从行为者主观世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本体论的前提,因此,我们可以把行为者所说的社会世界与其他社会成员所说的社会世界以及我们所说的社会世界区别开来。在合理解释与描述解释中进行选择,其关键在于确定我们是认真对待行为者的行为所关涉的规范有效性要求,还是把它曲解成纯粹主观的东西。这里的描述解释也是建立在对行为者在遵守合法规范过程中所认为的合理内容加以重新解释基础上的。而在这里的合理解释中,我们和行为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对称的关系,行为者在规范行为模式中不可能作为话语的参与者用假设的立场对规范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我们要是循着概念史来考察“现代”一词,就会发现,现代首先是在审美批判领域力求明确自己的。18世纪初,著名的古代与现代之争导致要求摆脱古代艺术的样本。主张现代的一派反对法国古典派的自我理解,为此,他们把亚里士多德的“至善”(Perfektion)概念和处于现代自然科学影响之下的进步概念等同起来。他们从历史批判论的角度对模仿古代样本的意义加以质疑,从而突出一种有时代局限的、即相对的美的标准,用以反对那种超越时代的、即绝对的美的规范,并因此把法国启蒙运动的自我理解说成是一个划时代的新开端。尽管名词“modemitas”(同表示相反意思的复合形容词“anticqui/modemi”一道),早在古代后期即已具备一种编年意义,但现代欧洲语言中的“modem”一词很晚(大约自19世纪中叶起)才被名词化,而且首先还是在纯艺术范围内。因而,“Moderne"、“Modernitaet/modemite”等词至今仍具有审美的本质涵义,并集中表现在先锋派艺术的自我理解中。
对波德莱尔来说,审美的现代经验和历史的现代经验在当时是融为一体的。在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经验中,确立自我的问题日益突出,因为时代经验的视界集中到了分散的、摆脱日常习俗的主体性头上。所以,波德莱尔认为,现代的艺术作品处于现实性和永恒性这两条轴线的交汇点上:“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这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自我煎熬的现实性成了现代的起点,它不具备漫长的过渡期以及在现代中心建立起来的、长达几十年的“当代”。真实的当代也无法再从与已被摆脱和克服的年代、即一种历史形态的对立中意识到自身的存在。现实性(Aktualitaet)只能表现为时代性(Zeit)和永恒性(Ewigkeit)的交汇。通过现实性和永恒性的直接接触,现代尽管仍在老化,但走出了浅薄。根据波德莱尔的理解,现代旨在证明瞬间是未来的可靠历史,其价值在于它终将成为“古典”;而所谓“古典”,不过是新世界开始时的那一“瞬间”,因而不会持续太久,一旦出现,随即便会消亡。这种有关时代的理解,后来被超现实主义者再次推向极端,并在“现代”和“时尚”之间建立起了亲和性。
波德莱尔继承了著名的古代与现代之争的成果,但他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改变了绝对美和相对美的比重;他认为:“构成美的一种成分是永恒的,不变的,其多少极难加以确定,另一种成分是相对的,暂时的,可以说它是时代、风尚、道德、情欲,或是其中一种,或是兼容并蓄,它像是神糕有趣的、引人的、开胃的表皮,没有它,第一种成分将是不能消化和不能品评的,将不能为人性所接受和吸收”。作为艺术批评家的波德莱尔强调现代绘画中所反映出来的当代生活中的瞬间美,读者允许我们把这种美的特性称作“现代性”。波德莱尔在“现代性”一词上加上引号,说明他是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独立地使用这个词的,并把它当作一个独特的术语。依波德莱尔之见,独立的作品仍然受制于它发生的那一瞬间;正是由于作品不断地浸入到现实性之中,它才能永远意义十足,并冲破常规,满足对美的不住的瞬间要求。而在此瞬间中,永恒性和现实性暂时联系在了一起。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