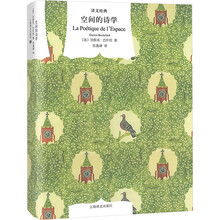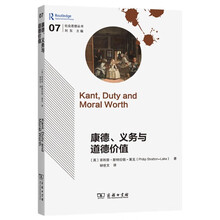德是什么?
已成绝响的arete
“我想,‘德’——这种被我们称为阿烈特(arete)的东西——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德”这种东西已经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了?这怎么可能?
我此刻身处希腊雅典历史悠久的阿格拉(agora),刚才我提出了“德是什么”这个问题。在这个蔓生着四百万人口、正忙着准备主办2004年夏季奥运会的大都市无尽的车马喧嚣下,我们一群约二十个人紧密地相偎于其中静谧的一隅。“阿格拉”一般译为“市场”,但我却认为译作“聚集处”更为恰当(其实,agora这个名词源于希腊文的动词ageiro,意为“聚集”)。千百年前聚集到这个商业及市民生活中心的人,不只是来此地以物易物、兜售百货,也是来这里交换并检验彼此的观念与理想。阿格拉坐落在雅典城邦的中心,而雅典城邦则是第一个真正民主政体的摇篮。它被普利策奖得主、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汀(Daniel Boorstin)赞为“西方世界赖以定义道德、肇造社群、陶铸国族、建立帝国”的发祥地;不仅如此,这么多光辉焕耀且历久不衰的成就“竟然来自为数这么少的一群人”——当时它的人口不过区区八万而已——更让布尔斯汀叹为“古希腊的又一项奇迹”。
我们坐在希腊神祗宙斯·艾琉瑟丽欧斯(Zeus Eleutherios,即“拯救者”宙斯)神庙废墟的拱廊阴影里,多数在当地兜着圈子四处浏览的观光客,对于我们的存在丝毫未在意。这座拱廊是为了纪念那些为争取希腊城邦的自由而战的斗士所建,也是为了供奉宙斯所建——当时的希腊人相信是宙斯解救了他们,让他们得享自由。在曾经是廊柱的大理石残垣断砾之上,我们所坐的地方,几乎正是公元前5世纪苏格拉底与朋友、相识者和论敌们聚会、展开哲学辩难之处。
此刻,大家的目光都盯在刚才说话的玛丽亚身上。除了我之外,似乎还有不少人被她这一记当头棒喝给打晕了。正当我打算问她,为什么相信德或者阿烈特已经不存在时,一位对话者抢了先。他看着她说道:“德这个东西以前曾经存在过吗?”
“噢,当然,”玛丽亚说,“这是毫无疑问的。”
“怎么说?”我问。
她没有马上回答我的问题。身为艺术家的玛丽亚是我的远房表亲,但我们到昨天才头一次见面。十年前,她从火山岛尼希洛斯(Nissyros)搬到了雅典。尼希洛斯是希腊多德喀尼群岛(Dodecanese Islands)的一部分,1922年我的祖父母移民美国之前也住在该岛。当时在乔治二世(GeorgeⅡ)立宪君主体制统治下的希腊陷入悲惨的经济困境,而与土耳其之问旷日持久的战争,更进一步恶化了经济的危局,于是我的祖父母取道艾利斯岛(Ellis Island)进入美国;在艾利斯岛上,他们的姓氏Philipou被简化为Phillips。
“看看周遭这一切,”玛丽亚发话了,“你们看到的是什么?是宏伟壮观的废墟,你们所看到的,就是一个充塞着‘德’的社会的遗存。我们此刻所坐的地方,就是苏格拉底聚众论道之处,也就是世界上最有德的所在——好比一座德的绿洲。”
她遥对着高踞于远处卫城(Acropolis Hill)上的那座令人屏息、大体上完好无缺的帕特农神殿——雅典统治者伯里克利为纪念在其主导之下雅典所成就的文治武功而下令建造的一座纪念碑——做了一个横扫千军的手势。玛丽亚说:“帕特农神殿,和我们周遭这所有废墟一样,都是德的果实,也就是不为谬见错觉所拘泥、飞升到空前绝后的高处那些伟大的心灵与魂魄的产物。”她的声音充满激情,接着说:“他们让你的灵魂飞升,他们激发你去想像作为一个人有些什么新的可能性。”
然后她说:“当我说我怀疑德这种东西已经不存在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不再创造出德的成果,在我看来,就表示德本身已经无法再存在。我们再也不能自我吹捧说我们正在创造伟大的艺术品和建筑,我们再也不能自夸拥有一个举世艳羡的民主政体,我们再也不能自吹自擂说我们拥有伟大的剧作家和伟大的公众知识分子,好比苏格拉底和他的同辈埃斯库罗斯及索福克勒斯,这些人不仅是在创作德的产物,其实他们本身就是德的产物。我们已经千百年未曾创作出任何一件像这样的德的产物了,所以我们怎能说自己仍拥有德本身呢?”
在我们正逐渐进入正题时,名叫乔格斯的男子刚巧从旁边信步而过,被我们的话题吸引而决定加入讨论。他发言道:“一直到几十年前,阿格拉才被发掘出土。它在苏格拉底过世后不久便被废弃,公共生活随之消失。没有一种公共生活,一种能让所有人觉得他们正在合力企及每个个人所不可能达到的更高境界的公共生活,就不可能有德存在。”
他陷入了沉默。爱琴海上吹来的善变的海风摆弄着他的长髯。然后他说道:“苏格拉底就是在此处问道:何谓正义,dikeosyni?何谓德,arete?中庸,sophrosune,是什么?而勇,andreia,又是什么?善,agathos,为何物?而虔心,eusebeia,又为何物?他问这些问题,不只是想获得一种对于德的本旨及其特质更好的理解,更想将他的发现发扬光大,以便使自己及其他人借以了解到自身所禀赋更为崇高的潜力。在他之后,又有谁做过这样的事呢?”
坐在他旁边的女子瑞妮说:“我想,在苏格拉底遭遇那样的下场之后,人们都吓得不敢重蹈覆辙了。他们强加给他妖言惑众和叛国这两桩大罪,借以警告那些与他一同谈玄论道的人,停止批判腐败的统治者。”说着,她指指旁边长着野花的土地说:“那儿,就是传说他饮下那一小杯鸩酒从容就义之处。原本他期望自己做出这个榜样会激励其他人的士气,使他们继续提出更多质疑,不幸自他成仁之后,德也随之消失了。”
玛丽亚的朋友、图书馆管理员埃拉芙瑟莉雅这时说话了:“我们希腊宣布2001年为‘苏格拉底年’,搞出一大堆研讨会和书单,还把柏拉图写的苏格拉底对话录搬上舞台重演。在我们这儿模仿苏格拉底的人,怕比你们美国模仿猫王的人还多。不过,我们却没有办过像我们现在在这里举行的这种对话,说实话,我们根本想都没想过。我们距离苏格拉底亲身践履的那种质疑方式已经太遥远了,我们只是把苏格拉底当成博物馆必备的收藏品,完全没想要再实践苏格拉底身体力行的那种慎思明辨的生活。”
“照这么说,”我接上了话茬,希望借此导引她此后的响应能逐渐接上我们正在检讨的问题:“德是……”
“德,”埃拉芙瑟莉雅接口道,“就是怀抱着‘发掘生命更崇高的意义’这样的动机去质疑既存的信念,继而追索那样的意义,以求使自身更为超卓,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激励你所处的社会,使之亦更趋于完美。”
“你所说的‘更崇高的意义’是什么?”我问。
“就是一些比你自己更伟大的东西,”接话的是高中生派蒂——当天稍早我们才发现她也是我的远房亲戚,“苏格拉底成年以前曾经存在过的那种雅典文明是最好的例子。他们合力创建了一个开放的社会,在其中,每个人都能将他的天分发挥到极致。他们有一种自私与无私的完美混合,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能协助你所处的社会达到更高的境界,你自身也就不可能达到更高的境界。”
接着初中生尼可斯说:“说实在的,德不是一种可以定义的东西,它是一种活出来的东西。就好像当苏格拉底在这里和人们对话的时候,他身处的那个社会所过的已经不再是一种有德的生活。苏格拉底和他的伙伴们之所以开始问‘德是什么?’,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丧失了活生生的德。当你必须开始去问德是什么,就是你已经不再有德的一个确定无疑的征象。”
“这句话是百分之百正确的吗?”我质疑道,“你一方面过着有德的生活;另一方面不时地质问德是什么——只是为了确定自己的确没有误入歧途,或者为了要看看自己相信的德的理念是否与他人一致,这样也无伤大雅,不是吗?”
他的女朋友柔伊接口说:“这也许就是最开始时的问题。早先的雅典人未曾退后一步反躬自问他们自己究竟在做什么,直到为时已晚的一刻才想到。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探索什么是德、什么不是德——便可以算是一个活生生的德的例子,因为我们有了一个机会去学习更深、更广地理解德,并且学习如何去实践我们的所学。就好像这场对话让我想到:通往德的道路是你为自己创造出来的,似乎从来没有哪两个民族或哪两个社会是经由相同的途径而变得更为有德的,但我想他们都有相同的起点——他们都从提出‘德是什么?’这个问题开始,因为惟有通过回答这个问题,你才能接着回答‘我们如何才能变得更为有德?’的问题。”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