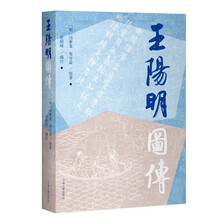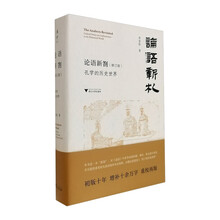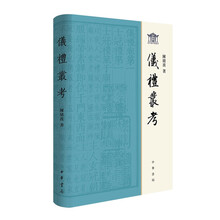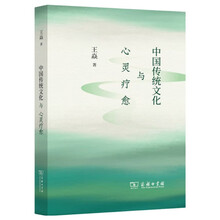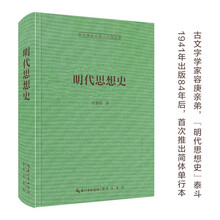第一讲 平民圣人
墨子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评价。在我们看来,他既不像孔予以贵族自居,摆圣人的架子;也不像庄子珍视自由之身,做一个洒脱逍遥的隐者。他坚持平民的立场,勇于牺牲自己、拯救世人,他是不亚于耶稣的一位东方圣哲。
当今的社会,贵族出身成为炫耀的资本,小资情调成为时尚的象征,而草根阶层则逐渐被人遗忘。作为一位平民圣人的墨子,自然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然而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在贵的没落、贤的兴起的春秋战国之际,墨子立志“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以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为榜样,成为当时颇为有名的北方圣人。
一、贵的没落
墨子的生卒年代至今未有定论,这种疑问自司马迁时就已产生。《史记·孟子苟卿列传》说:“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汉书·艺文志》也只是大概地说:“墨子在孔子后。”《后汉书·张街传注》稍微确切一点:“公输盘、墨翟并当子思时,出仲尼后。”对此,近人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聚讼纷纭,奠衷一是。但是认定孔子活动于春秋末期,墨子活动于战国初期,基本是各家的共识。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牛耕的使用和铁器的出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加剧了贫富的对立,“贵”的投落和“贤”的兴起成为突出的社会现象,所有这些都构成墨子出生的时代背景。 春秋末期,和牛耕有关的记载出现了。孔子的弟子冉耕字伯牛,司马耕字子牛(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司马犁字牛(见《论语·颜渊篇》注)。按中国古老的习惯,社会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不仅有名,而且有字。《说文》中说:“字,乳也。”叙云:“字者,言孽乳而浸多也。”也就是说,字是从名的含义中衍生出来的,二者的意义是相关联的。当时人的名字已有牛、犁、耕的字样,说明牛耕在春秋末期已是社会上引人注意的现象。
铁表具的出现,比起牛耕,对农业生产力有了更大的推动。有了铁农具,就能进行深耕,使过去不能开垦的土地开垦出来。当然,铁农具的使用和耕牛的使用,是相互关联的,只有使用畜力,特别是耕牛,才能更好地发挥农具深耕的效力。《国语·齐语六》记载,管仲对齐桓公说:“及耕,深耕而疾援之。以待时雨。时雨既至,挟其枪刈耨镩以从事于田野。”由此证明,当时铁农具已经出现,深耕因此有了必要的条件。从牛耕、铁农具的使用来看,春秋战国之际是农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时期。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基础。
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井田制的破坏,赋税制度受到影响。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开始按亩征税。按亩征税的结果,使贵族土地的所有权更加确立,更为鲜明,农民对于自耕的小土地所有权也逐渐确立。春秋战国之际,在贵族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一部分贵族在斗争中失败,下降为自耕农民。一部分军功人员通过赐予和买卖取得土地,一部分商人和货币持有人也通过买卖取得土地,他们成为大土地所有人。这样贵和贱的对立逐渐变为富和穷的区别。
对于贵族世代相袭的特权,墨子进行了抨击。他在《尚贤下》篇中说:“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贵,皆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也。……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国家,则其国家之乱可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然女何为而得富贵而辟贫贱哉?曰:莫若为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王公大人骨肉之亲,无故富贵,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学而能者也。”在墨子看来,贵贱是靠血缘关系划分的,所谓王公大人的“骨肉之亲”是“无故富贵”的,这是“非学而能者”。这些人不具备治理国家的知识和才能,使用他们治理国家必然导致国家的混乱。
二、贤的兴起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生活变得日益复杂。在这个变化过程中,不学无术、以土地收益为生活基础的氏族贵族,正日益失去它的生命力和活跃性。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