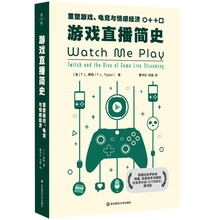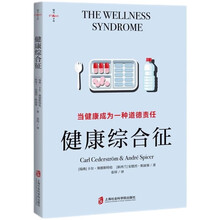凯恩斯主义的观点来看,今天我们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比较肯定地说的也许只是,我们都将死去。既然这些经济的、政治的问题如此有争议,如此不确定,也就自然会形成一系列不同的措辞反应,来表达、倡导、鼓吹各种不同的解决方式和策略。
由于我们相信这些争议论辩都是真诚的,而非只是流俗的人云亦云,同时,我们亦相信,这些争议所涉及的那些潜在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没有简洁明了的经济解决方式,因此,我们才采用“措辞”这一术语,而没有采用“意识形态”。在过去,“意识形态”这一词汇通常被用来意指福利承诺的虚幻性质(Clarkeea1,1987)。但存今天的情形下,把“管理主义”说成是一种削减福利的意识形态是欠妥的,当然,这部分也是因为它还不够成熟。如果“管理主义”仅仅意味着实践中的“问责制”(accountability),那么,就没有什么理由反对这种管理策略。但我们目前还不能作出这样一种明确的判断。此外,我们还承认,福利所遭遇的各种困难——对这些困难,管理主义的某些方式是可能的解决途径——都是些真正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下面这一系列的变化,如人口的老龄化,不断增长的健康需求,不断提升的服务期待,福利官僚机构的膨胀,作为关怀的一个主要来源的社群的销蚀,由于家庭转型而导致的老年人的孤立,家庭和亲属义务的瓦解,工作的衰退,以及随着技术的革新而来的医疗费用的不断上升,等等。管理主义也许真的会成为一种导致大量人口贫困化的削减福利的意识形态,但是,作出这种判断应该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而不应成为我们研究的一个预设。先人为主地认定新自由主义之前的福利体制在交付方式和当事人的满意度方面是最成功的,只不过是怀旧病的作祟。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让我们觉得用“措辞”比用“意识形态”更贴切。在不确定的全球经济环境下,当代有关福利的社会和经济情况瞬息万变,经济增长的总体态势也前景莫测。由此,一些解决福利的方式也就往往是一些临时的、应急性的方式。“风险社会”(Beck,1992)这个概念为现代社会增添了一个重要的词汇,因为它揭示了一个缺乏控制的全球体系所具有的诸多不确定性。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