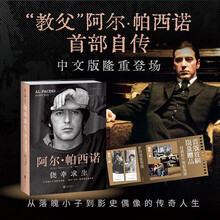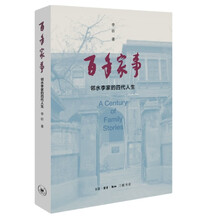第一章<br> 我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写作中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时隔多年,仍要提起笔来尝试写作,心里真有一丝轻微的发自内心的不安。<br> 这不安首先是因为缺少一个理由,或说是一个借口:上学的时候,出于学生的义务几乎一直在写作;有时,也会写信给远方的朋友,作几首小诗或沉迷于类似的少年闲愁里。<br> 而现在,我只是想在空闲的时候,叙述一个真实的生命,而不是无所事事地虚度光阴(对于一个在我这样的年纪临时充当起作家角色的人,如果这还可以算得上是充分的理由的话)。<br> 我承认,那些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对着这几张可怜的书页大打哈欠的读者并不是我最担心的,对他们来说,随时可以把书丢在一旁睡一觉;我真正担心的是当我写作的时候,那双观察着我的,阅读我思想的眼睛。<br> 那是一位老人的眼睛,来自一张亲切的面孔,带着满意的表情,那微笑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他是如此洞察生活的悲喜,又有一丝厌倦和漠然。激情,在这样一位老人的脸上,已经再也看不见了,已经被岁月无情的力量和刚毅的思想所磨灭。而那张安详的,仿佛被思想的火光映亮的面孔,正严厉地审视着我:在那目光之下,我发现自己可笑、怯懦,又一无所能,可是一秒钟以前,我还像某些自以为掌握了绝对真理的学生般的自命不凡,充满幻想。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看到老人慈善的脸上,还掠过一丝讽刺。于是我问自己:为什么他对我不像对待别人那样宽容?为什么要对我如此认真严苛?<br> 或许你们已经认出了这位年长慈善的审视者,他那刻不容缓的目光始终落在我肩上,每时每刻,凝视着我的每一次行为,每一个决定。<br> 第二章<br> 我在自己的房间里:一间三平方米的屋子,两把扶手椅、一个洗脸池、一面镜子、一张小桌和一个壁橱。一扇临街的窗户照亮了屋子。现在是下午两点,我要在这里呆到很晚。过会儿会有人叫我去排练,然后化妆,再带我去喝点东西,比如一杯咖啡,总之,和往常一样。于是,为了消磨时间,我开始讲述这个故事。电脑已经打开了,现在,我只缺少一个主语。<br> 我需要自我疏离,但那对我来说很困难。我在屋里踱来踱去,怀念着那些远去的人和事,脑海中忽然浮现出一个穿着短裤的男孩,他干瘦得像木柴,略微弯曲的双腿强劲有力,布满了青肿的疤痕,他的头发漆黑,五官相当端正,一脸小大人的表情,是惹人反感还是讨人喜欢则见仁见智了。如果你们不反感,我就跟你们聊聊他,因为我太了解他了,绝对能够从容地做个事后诸葛,来思考评判他的性格、他的思想和他每一次重要的抉择。即使那些如今都已众所周知的事实让他的生活变得有点不同于常人,但我们仍可以把他称为一个“正常的男孩”。我说他正常,指的是在他身上,优点与缺点各占一半。虽然我不愿意,却不得不承认,他的身体有相当严重的残疾,但我仍然要说他是正常的。不过,在讲述之前,我要先给他取个名字。<br> 既然名字和名字间没什么分别,我就叫他阿摩司吧。曾经有一个令我终生感激的人也叫这个名字,我在他身上受益良多,对他却亏欠无比,知之甚少,我曾试图像他那样去生活,却不怎么成功。阿摩司,这也是一位先知的名字,或许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这名字很亲切,也很适合一个——在十二岁时,由于一次鲁莽行为而丧失了全部视力的——小男孩。那时,他用了整整一个小时哭尽了所有惶恐和无措的泪水,而用了足足一周来习惯他的新处境。之后,阿摩司忘记了这一切,他也令家人和朋友们忘记了这一切。关于这方面,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些了。<br> 他的母亲为了让她那活泼的长子重新振作起来,常常详细地讲起他小时候的样子。“你一刻都不能分心,一眨眼功夫,他就又搞了个鬼。”<br> “他总是喜欢冒险,有一天,我找他,他不在,叫他,他不应,我一抬头,看到他站在我房间的窗台上。我们住在二楼,而那时他还不到五岁。为了让你们更明白我所经历过的,我跟你们讲讲这个。”于是,她又开始讲述,带着她那托斯卡纳 口音、丰富的手势以及满腔的激动:“有天早晨,在都灵,我和他手牵着手,我们沿市中心的一条林荫道,边走边找一个电车站。我在第一个车站前停下来,瞥了一眼橱窗,当我转过身来,我全身的血一下子都涌上来了:那孩子不见了!我绝望地找遍了所有的角落……他不在。我喊他,没人应!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抬起头来的,我已经不知道该看哪儿了,然而我看到他在上面,爬到了车站牌的顶上……”<br> “等等,这还没完呢!”她继续打断聆听者的惊叹,“起初那几天,他一直没有胃口,我不得不到处跟着他,到拖拉机上、到工人们的小摩托车上,只为了往他嘴里喂一勺汤!”<br> 倘若哪位听众对她的故事产生了兴趣,我们就能看到埃迪夫人更加高兴,更加不知疲倦,她会继续用各种细节来充实她的故事,除了个别出于她强烈的爱而显得有些夸张和自相矛盾外,这些细节对故事并没什么价值,但却让故事变得真实。<br> 我还清楚地记得,有一位年长的女士听那母亲讲起小阿摩司的艰难童年时,脸上流露出真挚的感动。“那时他才几个月大,他受着剧烈眼痛的折磨。他有一双蔚蓝色的眼睛,美极了……可是不久,像晴天霹雳,医生们诊断那孩子得了先天性青光眼,这种畸变会让那小可怜完全失明。于是,我们四处奔走,从一个大夫到另一个大夫,从专家到江湖郎中。我丝毫不会为了走过那样一段路而羞愧。我们的苦难之路一直通往都灵,到了著名的加兰卡教授那里。我们在那家医院里呆了好几个星期:频繁的手术,企图能挽救那一点点残留的视力。旅途令我们筋疲力尽,恐惧、不安、惊慌更令我们消沉,不公的命运在对那可怜的孩子大发雷霆,而我们在它面前却无能为力……第二天早晨,我丈夫又出发了,留下我和孩子在一起。教授很善解人意,给我们安排了一间两张床位的病房,这样我很快就和医护人员熟悉了(在以后几年中,每当阿摩司的活泼好动到了无法控制的时候,这就显得尤为有用了),阿摩司八岁的时候,他们甚至还把一辆小自行车带进了病房,好让那孩子能够发泄一下。”<br> 那位年长的女士显然非常感动,她突然打断了她,大声喊道:“夫人,我非常理解您的感受,但请原谅我的好奇,那孩子的眼痛持续了很久吗?”<br> “亲爱的夫人,您知道……我们根本就没法让他平静下来!有一天早晨,经过一整夜地狱般的痛苦后,突然间,那孩子静了下来。那一刻真是难以形容:一种不是对某个人,而是对所有人的深深感激,是在令人恐惧的风暴中,不期而至的平静所带来的极乐。我努力想弄清楚这突然的平静的原因,也热切地盼望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好让我能够凭直觉觉察到它,并从那一刻后将其化为己有。我仔细地观察,思考,想遍了所有可能性,却得不出什么结论。突然,我看到那孩子转过身,用手贴着靠床的墙。过了一会儿,我不记得到底过了多久,直到房间里出现一种刚才我没注意到的安静,而顷刻间,那孩子马上又哭了起来。这是怎么了?是什么中断了吗?还是那突如其来的安静让我的儿子变得不安?我又着起急来,但没过多久,那孩子又平静了,像刚才一样,手贴着墙。不知为什么,我紧张到了极点,侧耳去听,我听到隔壁房间传来的音乐。我走近一点,屏息凝神,是我所不熟悉的,很可能是古典音乐,室内音乐。我听不懂,但却相信我孩子的平静正是来自于它。这小小的希望让我欣喜若狂,那喜悦几乎和我的痛苦一样深,那是我从未体验过的,也许只有当付出了沉重代价、经历了深刻的苦痛之后,它才会到来。我扑向隔壁的房间,毫不犹豫地敲门。一个外国口音请我进来。我走进大门,一位病人坐在他的小床上,倚在,更确切地说,瘫在两个靠垫上,好让他那强壮的肩膀舒服点。我还记得他那强健的胳膊和因劳作而僵硬的双手,一双工人的手;我还记得他微笑的脸,缠着绷带的双眼。他是一位俄罗斯工人,不久前一起事故夺走了他的视力。一台小小的电唱机就足以令他开心了。我还记得当时深深的感动,哽塞了喉咙……<br>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努力地度过了那个时刻,我记得我们聊了很久,跟那个善良的人讲了之前发生的一切,请他允许我偶尔带着儿子来他的房间坐坐。他那和善的招待,他那富有感染力的快乐,他那简单又伟大的非凡的灵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够用那只有几个词语组成的却又非常有用的意大利语来招呼我们。”<br> 埃迪夫人常常怀着这样激动的心情向别人讲起,她是怎样发现儿子对音乐的热爱。<br> 第三章<br> 我总有种不可抑制的渴望,想要赋予音乐这门高贵的艺术一个不同于以往的全新定义。因为音乐曾经带给我无数幸福的时光,也同样带给我许多困扰和不安。<br> “有许多个不眠之夜,在结束了一整天辛苦的学习和工作之后,我常常想要努力整理一天中积累下来的纷乱的思绪。长久的思考再思考,而有时,唯一的结果,却只是渐生的困意,毫无什么创见,也毫无有价值的哲学或艺术见解。即使没有我的定义,音乐本身就已经很丰富了,比人类所有的谈论和描述都要丰富。那么,我只有在日记本单薄的某一页上,写下这世上也许是最平庸、最可笑的字语,但那却是我曾经无数次对着天空呼喊过的心声:‘音乐对于我,是一种需求,如同爱;音乐对于我,更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如同死亡。’”<br> 我在阿摩司的日记本里发现了这一段,那本日记本很旧,里面有许多他创作的小诗,还有他从小到大各种各样古怪的念头,就像上面我摘录的那段。我摘录那段日记,只是为了更好地向你们讲述他的故事,也是因为,往往这些看似不经意的偶然,看似漫不经心的话语,却恰恰最能勾勒出日记作者的性格和他最真实的内心世界。<br> 妈妈发现阿摩司热爱音乐的故事,惹得亲戚们争先恐后地把一切会发出声音的东西都送给他。于是,他收到了各种各样能够制造出简单音符的玩具、电子钟琴,最终还得到一台非常漂亮的电唱机和他的第一张唱片。他很喜欢这张歌曲唱片,也很好奇,但是却没有表现出更多的热情。<br> 有一天,年长的叔公激情澎湃地对他说起了一位刚刚辞世的著名男高音,和他美妙的歌喉,阿摩司听了,迫不及待地想要听一听他的这位新偶像——神话般的歌唱家贝尼亚米诺·吉依——的唱片。阿摩司听到那声音时,激动万分,于是叔公只得继续把故事讲下去,甚至最后还不得不编出一些情节来满足小阿摩司丰富的幻想。接下来的日子里,小阿摩司需要越来越多的唱片和越来越多的新生歌唱家的故事,才能平息自己的好奇和那突如其来的狂热。<br> 阿摩司总爱把他最近偶像描绘成最棒的那一个,孩子们都是这样,为他们的新偶像而激动。<br> 就这样,家里面又增加了许多朱塞佩·迪·斯特凡诺 、马里奥·德尔·莫纳科 、奥列利亚诺·佩尔蒂雷 、费鲁乔·塔里亚维尼 等人的唱片。后来,叔公又和阿摩司谈起了卡鲁索 ,他用上自己全部的口才和激情,肯定地告诉阿摩司:卡鲁索才是最优秀的歌唱家,他拥有最强劲、最明亮的声音,是所有歌剧爱好者的宠儿。不久,家里便出现了第一张恩里科·卡鲁索的唱片,但却是它第一次令阿摩司感到失望,这个完全不懂得录音发展技术的孩子,一点也不喜欢那像是从坛子底下传出来的声音。岁月磨损了卡鲁索的音色,对小阿摩司来说,这无法和德尔·莫纳科那贵族般的威严嗓音相媲美,也比不上令人印象深刻的吉利 那既甜美又充满激情的嗓音。<br> 很多年以后,经过了种种奇特经历的阿摩司会重拾起对伟大的卡鲁索的信任。这段漫长岁月中的经历,也正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主题。<br> 有天早晨,阿摩司独自一人在院子里苦思冥想,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他踱来踱去,从大门到车库再到公路口的栅栏,还不时地低声哼上几句在熟悉的空气中随性创作的旋律。突然间,他停了下来,听到他的塔塔(阿摩司这样称呼奥莉亚娜,她在阿摩司家做过女佣,曾经看着阿摩司出生,阿摩司对她怀有真挚的热爱)独特的脚步声。<br> 奥莉亚娜刚从商店买东西回来,一打开栅栏门,就看到阿摩司朝她奔过来,她露出母亲般的微笑,把他叫到身边,对他说有很重要的东西要念给他听,还是刚刚在爸爸的报纸上看到的。她赶忙把买来的东西放到家里,然后拿着报纸出来。<br> “好好听着。”读报之前,她一字一顿地说。<br> “超强震撼!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弗兰科·科莱里 。”<br> 阿摩司那时已经八岁了,他知道什么是米兰斯卡拉歌剧院,却没有一个人,包括叔公在内,向他提起过这位神奇的歌唱家。<br> “塔塔,谁是科莱里?”阿摩司跟在她后面跑着,匆匆问道。好心的塔塔便开始为他念那篇文章。文章描述了歌剧《胡格诺派教徒》中的第一幕,这位著名的男高音从中脱颖而出,尽情地向世人炫耀着那极其丰满又极富青铜般质感的声音,和他丰富的共鸣,他自如转换的高音令在座的观众震惊。据记者描述,赞美声、歇斯底里的喊叫声和反复要求返场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在整个剧场久久回荡。<br> 念完了文章,塔塔拿着报纸,静静呆了几秒钟,一动也不动;而阿摩司的心中却涌动起某种潜藏的思绪,然后他看到塔塔合上了报纸,弯下腰对着他,塔塔轻轻地说:“真美啊!”接着她又补充道:“你应该送自己一张他的唱片,我也很好奇,想听听他究竟有怎样一副嗓音……”<br> 就这样,几天后,家里又有了第一张科莱里的唱片。奥莉亚娜找到了那张唱片,并送给了阿摩司,在她不同寻常的好奇心背后,她真的想了解那孩子在想些什么。<br> 阿摩司立刻跑到老留声机旁,打开唱机,放上唱片,他把唱针臂往外掰开。在之后的岁月里,这根唱针还将陆续滑过他自己的四十五张新唱片。这时,乐队开始演奏乔尔达诺 的歌剧《安德莱·谢尼埃》的即兴曲宣叙调,终于,在乐队演奏的间歇,一个声音填补进来,独自深入到听众的耳中。是一个完全与众不同的声音,它伴随着“Colpito qui m’avete”这几个唱词而来,一个无比响亮无比宽广的声音,饱含深情,满载着难以言说的痛苦,直抵人心。绝对舒展的,自由的,自然的歌声,时而甜美,时而怒号,却总是威严庄重。这首即兴曲的确是个精彩的段落,但需要诠释者融入角色,体会出这位身处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诗人谢尼埃的复杂情绪。<br> 谢尼埃为了感情来面对爱的主题,而在那张唱片中,科莱里则似乎是为了他的艺术而面对着爱:为了这门能够感染人、感动人、改变一个因生活的磨难而冷漠了的灵魂的——歌唱艺术。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