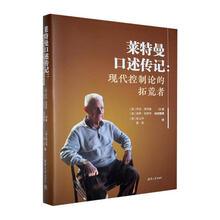八、人格分裂:两度批顾
应该说,童书业在从“实验主义史学”皈依“马列主义史学”之初,有一个问题他是察觉到了的,这就是:假如“马列主义史学”应该领导、改造“实验主义史学”,而他自己已经皈依了唯物史观,那么,他将如何处理与还未表态皈依唯物史观的顾颉刚的关系?童在最初的两年,苦口婆心地劝导顾,当然一方面是出于初皈依者的真诚,另一方面,很可能是更主要的方面,是童自己缓解内在紧张的举措:假使也能促动顾先生皈依唯物史观,那么他师徒俩就又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否则的话,在“亲不亲阶级分”的气氛下,他如何协调“阶级立场”与“师生感情”的矛盾?!对这两方面看得都很重的童书业,可能时刻有一种被撕裂的痛楚。后来,可能当他得知顾颉刚以“无暇”为由拒绝阅读流行一时的唯物史现书籍,也可能是当他被撕裂感折磨得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他致信顾,开始用“阶级分析方法”来反省“疑古学派”的“阶级属性”了:
两年来学习马列主义之结果,觉得日日考据之学确为形而上学者,尤其是正统派考据学确欠辩证。如以辩证法掌握考据学, 考据学当有大进步。我师旧日之考据,在考据学界中已为比较能把握全面者,已为比较能有发展观点者。如能再进一步,掌握矛盾统一观点,成就必更大。然吾人过去所以不能掌握辩证法,不能了解真正唯物论,实由于吾人阶级意识作祟。吾人旧有之史学确是资产阶级之史学。当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比较发展,疑古思潮确负有若干反对封建传统使命。故疑古思潮之真正来源,实为工厂及商店,并非凭空由头脑产出者,吾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说话而不自觉耳。吾人著述中虽亦有若干唯物论成分(如承认经济决定政治、文化),然只是机械只唯物论(经济史观),离辩证唯物论尚远。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卷土重来之外国资本主义之压迫,疑古思潮遂见低落, 吾人之史学转与封建主义妥协,至抗战后期,吾人已完全丧失进步性而变成封建主义与买办资本之附庸。吾人必须承认过去吾人之民族资产阶级立场之不稳定,经自我检讨后,始能接受无产阶级思想而改造故我。
把“疑古派”的“阶级属性”定位于“民族资产阶级”,并且强调“疑古派”随政治形势的变化,时而“左”些,时而“右”些,但最后终于“完全丧失进步性而变成封建主义与买办资本之附庸”,也就是说变成“反动一帮”,说明童对当时流行的“阶级分析方法”的理解与运用,完全纯熟,也说明他对“疑古派”的反思已达到系统化的程度。但见不及此的顾颉刚,对童书业的这番议论,大概不愿接受,且可能比较生气,故在眉批上写道:“此丕绳自道耳。我则学由宋人来,不至如此随时代变化也。”与童书业正积极地、义无反顾地丢弃过去完全不同,这时的顾颉刚则正在为捍卫过去而进行“垂死挣扎”。他们师生之间的冲突势所难免。
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经历了多座精神炼狱,从1951年开始至1952年形成高潮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他们通过的第一座炼狱。无论多高级的知识分子,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这两年里,可以说都低下了他们一贯高昂的头,都弯下了他们素来挺直的腰,都交出了他们平时不容伤害的自尊心。“古史辨”派成员这时简直像热锅上的蚂蚁,急躁、焦虑、惶恐不安。在上海学院参加思想改造运动的顾颉刚,1952年7月9日在日记中说:“此次学习,可怕者三:天正热,不堪炎蒸,一也。刺戟太甚,使予接连不得安眠,二也。开会太多,无写作自我批判之时间,三也。” 对于后一点,顾颉刚又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本年三反、五反、思想改造三种运动,刚无不参加,但每一运动皆过于紧张迫促,无从容思考之余地,而工作同志要人对马列主义一下就接通,以刚之愚,实不知其可。童书业的日子似乎比他的老师还难过。1956年3月山东大学有关组织所写的《童书业补充鉴定材料》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三反、五反运动中,他表示拥护,但抱着与己无关的态度,怕惹是生非,在会议上不敢大胆发言。思想改造运动中作过九次思想批判,但未被通过,情绪上烦躁,经耐心帮助,自己反复斗争后,才写出了较为接触思想的思想总结,主要是批判他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所涉及的方面有,最初他是陈独秀经济史观的信徒,并依此写了春秋史,后来自己独创“三合史观”,认为经济、地理、民族性三者为历史的重心。后又放弃“三合史观”,主张地理、经济史观。这些东西都是属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体系的。在考据学方面则批判了他一向崇拜顾颉刚、胡适的实验主义,同时也初步批判了自己为反动报刊写的反动性文章,如“双十协定”前后污蔑我党无和平诚意等。在“有何政治历史问题、结论如何”题下,《鉴定材料》说:童交待解放前尤其是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时期思想反动,学术上一贯用“三合史观”猛烈攻击唯物史观,辱骂拥护马列主义的人,如,“妄人”“重复欧美资产阶级御用哲学,互助论”;反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主张蒋介石的独裁政治,对我党进行严厉镇压;仇苏亲美,说:“中共认苏联为祖国”,中共就是实行苏联法西斯独裁政治,发表了许多反共文章,得到当时上海国民党非常器重,被称为反共英雄。经查对与本人交待基本相符、运动中对其进行了批判,撤销对他的怀疑:
在仅有一顶“资产阶级史学家”的帽子就足以将人压倒的“思想改造”背景下,竟还有这么多“反共”言论在,童书业所感受到的思想压力之大、政治包袱之重,完全可以想见。而且,当思想改造运动如排山倒海之势汹汹而来的时候,过去与旧政权有过这样那样联系、曾与马克思主义或相对立或相疏离的士子们,对这一运动究竟会进行到什么程度,大都心中没底,因而惴惴不可终日。许多人(当然包括童)当时思虑的焦点,可能并不是真正改造自己——“思想而能改造,在我的旧脑筋里简直是一件不能想象的奇事” ,而是如何干方百计使自己“过关”。至于朋友、老师怎么办,对这些急于过河的自身难保的泥菩萨们来说就顾不了那么多了。能“出卖”的且“出卖”,能拉来垫背的且拉来垫背。童书业的出路看来必须是当机立断,与老师顾颉刚划清界限,把自己从“古史辨”派的阴影中撇出来。何况顾颉刚亦已经与他的老师斩断葛藤了。
现在回过头来,遥看当年那些热锅上的蚂蚁,真是觉得十分残酷,于走投无路之际,只得层层“出卖”:学生“出卖”老师,老师也在“出卖”自己的老师,最高目的,倒不是“升官发财”,而是逃出“热锅”。做一个不受歧视、不遭白眼的普通公民,以便有一个老老实实干活的环境和机会。谁都知道,顾颉刚是胡适的高足弟子,他对“适之先生”执礼之殷,在《古史辨》第一册及其《自序》中一览无余。可是,胡适已经“溜之乎也”,并被宣布为“战犯”,可怜的顾颉刚只好比较实际地用斥胡来开脱白己。于是,我们看到,远在大规模批胡的1951年,顾就开始与“适之先生”划清界限了,在《大公报》(1951年12月11日)上发表了《从我自己看胡适》一文。 至于顾颉刚此文受谁的启发,无法确知。但罗尔纲的一段经历和感悟有助于我们的推断。罗说:
1950年8月,我又从家乡回到我的单位。那时陶孟和先生已经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来南京,对我说胡思杜写有篇《我的父亲》同胡适划分界限,写得很好,叫我看看。那时初解放,我在家乡未经学习,还不懂得什么叫划界限。而胡适的问题却正在沉重地压在心头,我听了孟和先生的话,立即去图书室借了《人民日报》来看。我看后启发我认识到胡思杜与胡适还可以划清敌我界限,我做学生的,更可以与老师划清敌我界限了!从此解决了心头的难题,豁然开朗了。二十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师,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师了!
顾同罗尔刚一样,同属胡适的得意门生,是不是也从胡思杜文章中受到启发,不得而知,反正他写出了与老师划清界限的文章。既然他能批自己的老师,童书业起而步其后尘,撰文批他,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同样自然而然的是,当1958年,山大历史系把童抛出来作为“史学革命”的对象时,他的助手和学生也就起而步童的后尘,揭发、检举童引导青年“走白专道路”,陷童于十分狼狈的境地!揭发、检举者也无非是借“出卖”老师来解脱自己,一如童所做的一样。
前面说过,童书业对主流话语掌握得非常娴熟,他的这篇批顾文章的题目更近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文章一上来就曲折交待了自己的处境和苦衷:“解放以后,我曾好几次在学习讨论会上和报纸上批判了自己过去的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但所批判的几乎只限于我自己的东西,不曾对我过去所隶属的学派——疑古派的史学作过整个的检讨,这篇文字就是想试从根源上批判疑古派的史学,以消除史学上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一环。” 这段话大概是想告诉世人、特别是自己的老师,不批判自己所隶属的学派、不批判自己的老师,自己无法过关。这和鉴定材料提供的事实是一致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作过九次思想批判,但未被通过。”自述年谱上也透露了相关信息:“(1951年)学习党史,写学习党史后的自我检讨,交持主要历史问题。发表于《新山大》。” 童的日子看样子非常难过,所以,他对这篇文章自然有着很高的期待。此文一上来就抓“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实在不是偶然的。态度不积极,批判不深入,上纲上线不够高,就难免意味着自己与“古史辨派”的决裂不彻底。
在透露了自己的隐痛后,童接着就说,“所谓‘疑古派史学’是美国实验主义传到中国后的产物,它的首创者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当前的战犯胡适。”这是从起源和发端上暗示“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而后,童从“古史辨派”对抗唯物史观的角度,进一步揭露了“古史辨派”的“阶级本质”。童说:唯物史观是无产阶级的史观,资产阶级要压制无产阶级,“就不得不压制无产阶级的思想,所以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就必然反对唯物史观,但是反对的方法不必—致:或者尽情诋毁,或者托词抗拒,或者截取变质。而这三种方法我们这批人之中就都用过的。”这句话非同小可。因为童自认为也是用“这三种方法”反对唯物史观的重要当事人之一。童以顾颉刚的一段著名声言为例,边引述边揭发了“古史辨派”抗拒唯物史观的手段。童说:疑古派的人们沉醉在实验主义的毒素里而不能自拔,以致看不见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是寻求社会法则,反说寻求社会法则的“唯物史观不是味之素,不必在任何菜内部渗入些”(《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二二页——原注)。疑古派认为:“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基本观念。”“等到我们把古书和古史的真伪弄清楚,这一层的根柢又打好了,将来从事唯物史观的人要搜取材料时就更方便了,不会得错用了。”疑古派以为自己的“下学适以前唯物史观者的上达”,自己“虽不谈史观,何尝阻碍了他们(唯物史观者——笔者)的进行”。童书业说:这种话好像对唯物史观者贡献好意,其实都只是抗拒唯物史观的一种巧妙手段,上引文字的作者把历史学机械地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归唯物史观统治,一部归校勘学和考证学统治,以为校勘学和考证学是基础,而唯物史观是建筑,要等疑古派把“坚实基础”“准备”好了,然后再请唯物史观者动手造建筑。疑古派说:“须待借助于我们的还请镇静地等待下去罢”。“镇静地等待”到什么时候呢?疑古派自己承认:“得到结论不知在何年?”这就是说现在还是我们的天下。你们的天下还早呢,这不是“阻碍了”唯物史观者“的进行”是什么!疑古派又说:“如果等待不及,请你们自己起来干罢!”这就是说你们也来干校勘学和考证学罢,不要再谈唯物史观了,也就是说古代思想及制度不必研究(因为研究这些就“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基本观念”)。现在只须“研究古史年代,人物真迹,书籍真伪”就够了,请问提倡这种史学的“效果”是什么呢?童书业这里所分析的《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中的这段话,几乎被公认为“古史辨派”向唯物史观派表示友好的著名言论,现在,经童书业这位当事人一番剔肤剖骨的工作,这段话所包藏的“险恶用心”几乎“昭然若揭”。可以想象,顾颉刚看到这种深文周纳的分析后,一定会胆战心惊、不寒而栗的。
经过上述铺垫,童书业的文章直奔主题:“疑古派史学的真实意图.是右面抵抗封建阶级,而左面抵抗无产阶级,这是最初的意图。”“右面抵抗”的意图表现在“摧毁封建的圣经贤传(辨伪经)和封建的道统偶像(辨伪史);“左面抵抗”的意图表现在“否认原始共产社会”——无产阶级史学坚决认定中国历史经历过一个“原始共产社会”以为未来的共产社会提供历史根据。而到了后来,据童书业说,“这派的史学家多数与封建阶级妥协,只坚决抗拒无产阶级了,这表现在‘疑古’精神的降落,考据精神的加强,同时诋毁或不采唯物史观。”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阶级本质”的位移呢?童从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作了说明,这种说明就是上引他致顾颉刚信中所说的那段引起顾反感的话。看来,从写那封信时,童就开始酝酿写这篇文章了。
对“古史辨派”在史学史上地位和作用的估价,大概是童书业这篇文章中最令顾颉刚心凉的地方。郭沫若一向对“古史辨派”高看一眼,《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所作的论述众所周知。在1940年代所作的《古史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中,在强调史料批判的意义时,郭沫若又肯定了“古史辨派”,甚至说某些唯物史观派成员还不如“古史辨派”。他是这样说的:某些新史学家,“对于旧文献的批判根本没有做够,不仅古史辨派的阶段没有充分达到,甚至有时比康有为阎百诗都要落后,这样怎么能够扬弃旧史学呢,实在是应该成为问题的”。这里,显然有把“古史辨派”与“乾嘉学派”相提并论的意思。童书业现在断然指出:“我们认为这段话是错误的,因为‘古史辨派’,(疑古派的别名——原注)与康有为根本就不能与阎百诗相提并论。”在童看来,“阎百诗是位比较单纯的考据家,而‘古史辨派’与康有为并不是单纯的考据家。”这显然是在强调“古史辨派”也像康有为一样具有学术之外的目的,因此,“阎百诗的考据是可以供参考的,而‘古史辨派’与康有为的作品,在考据学上说,也没有什么价值”。
童的文章对“古史辨派”学术地位的一笔抹煞,与此文同期推出的顾的另一高足杨向奎《“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一文,认定顾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造成古史的混乱”的断语一起,对顾的学术自尊伤害之深,难以估量。 来自一贯的敌人的攻击,尽管很恶毒,可以一笑置之;来自朋友、助手、学生、盟友和圈内人的打击,再轻微也觉伤心,何况这两篇文章并不轻微,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所以阅完这两篇曾是自己最亲密的追随者的文章后,顾在1952年3月12日的日记中记道:童杨两文“均给予无情之打击”。 哀伤、绝望之情溢于言表。但他并不服输。针对两文对《古史辨》的总体判断,5月4日,顾颉刚“写笔记数则,论《古史辨》之地位”。其中说:“《古史辨》是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所创造出来的知识总汇发展的结果。”“《古史辨》的工作确是偏于破坏的,所要破坏的东西就是历代皇帝、官僚、地主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而伪造或曲解的周代经典。这个反动政权是倒了,但他们在学术和历史上的偶像还没有倒……批判接受的前提就是要作一回大整理,使得可以以周还周,以汉还汉,以唐还唐,以宋还宋,表现出极清楚的社会性,然后可以与社会的发展相配合,所以《古史辨》的工作还该完成。” 在学术上历来极为自负的顾颉刚,在当时社会舆论极为不利的背景下,看来并不情愿就地倒下,反而强调要将《古史辨》继续下去。这既反映了他的骨气,也说明他对当时社会的陌生,没有看到这个社会的不可抗拒性。
应该指出,不管童杨二位的文章的写作与刊发,在当时有多少令人同情的社会和时代因素,文章本身的不公允是显而易见的:在笔者看来,绵延20余年之久的“古史辨”运动,可以说是一次大规模的对上古史资料的批判审查:这是继“乾嘉学派”之后,对先秦秦汉古籍的又一次整理运功,这次清查,为重建上古史系统,从扑朔迷离的神话传说中,打捞出了相对可靠的资料。从这一意义上看,把“古史辨派”看作中国的“兰克学派”并不过分。所以,被童书业判断为“完全错误”的郭沫若那段将“古史辨派”与“乾嘉学派”相提并论的话并不错误,乃是完全符实。经过时间的洗磨,郭沫若对“古史辨派”的下述看法,除了稍嫌不足外,还是比较中肯的:
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确是个卓识。从前因为嗜好不同,并多少夹有感情作用,凡在《努力报》上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是有先见之明。在现在新的史料尚未充足之前,他的论辨自然并未能成为定论,不过在旧史料个凡作伪之点大体上是被他道破了。
除了某些特殊的情况外,应该说,20世纪前半期的郭沫若,对整个史料学派的评论都还是比较公允的。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他评论过王国维、罗振玉、胡适、钱玄同和顾颉刚,这些评论意见,可以说他有史观偏见——这是任何史家都无法根除的“合法的偏见”,但不能说他有门户偏见。所以,他对顾颉刚的评价,为人所反复征引,井获广泛赞同。
童杨二位对“古史辨派”的全盘否定,在“思想改造运动”高压下,顾颉刚在感情上确实一时难以接受。但顾毕竟有批判“适之先生”的经历,他应该能体验到学生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刻,是不会起来揭发批判“先生”的。所以,顾在1952年3月12日的日记中既说童杨两文“均给予无情之打击”,又言:“盖思想改造,有大力迫之,使不得不然也。” 一段时间之后,顾的创伤也就弥合了,感情上也渐渐平静下来。1954年5月,顾的另一个学生王树民来信,对童杨二位的文章对“古史辨”派所持完全否定之态度“窃未敢以之为然”。信中说:
近来史学方面出版物虽多,可观者似颇寥寥。前者杨拱辰与童丕绳二兄在《文史哲》上发表批判《古史辨》的论文,完全为否定的语气,窃未敢以之为然,盲目的崇拜与盲目的否定,乃同为失其正自者也。无原则的疑古自然是错误的,而古史传说应该按照考据学的方法彻底整理一番却是肯定的。硬以社会发展史的方式套上去,所以西周为封建社会或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诸说之纷纭不绝,实即为此“近视眼断匾”之规律所支配也。
于鹤年也是顾办禹贡学会时的熟人,当年禹贡学会会员,当他看到童杨的文章后,“亦为此事抱不平,来信时时提起,一人之思想固可变,但不能变得太快,亦不能变成极端之不同,否则便是作伪矣”。有这些学生来为他鸣不平,不能不使顾感到慰藉和温暖,所以,他在复信时,也就表现出对童杨的为师者的大度、宽容和理解。先在回复于鹤年的信中说:
承嘱勿好胜,此切中弟病。十余年前曾自作一联曰:“好大喜功,永为怨府;贪多务得,何有闲时。”惟其有此病,所以有此名;亦惟其有此名,所以得此谤。解放以来,弟无名无谤矣。(《文史哲》上之两篇文字,非存心谤我,乃在思想改造阶段中,非如此不足以表示其忤悔,犹之昔日以附我为敲门砖也。观两文登出后曾无反响,可知弟于今日已到无名无谤地位,此卅年来求之而不得者也。)所恨者,成功之心尚未戢,无论时代如何,总想把旧稿编定, 已研究而未得结果之问题又总想研究出结果来,俗习如此,奈何奈何!
这是一封写于1952年10月23日的信件,从中可以看出愤激的情绪尚未完全宁息下来。到1954年6月11日写“致王树民”的信时,顾的心境看来已明朗多了,且已完全原谅了童杨二位。在谈到上述两篇文章时,顾十分肯定地说;“此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时之自我批判耳,以彼辈与《古史辨》之关系太深,故不得不作过情之打击。”此前不久,童杨曾联名致信顾颉刚,邀他为《文史哲》撰稿。这一举动传达了什么信息?顾在致王树民的信中也作了猜测,并得出了较积极的结论:“苟我之学术工作已不足存于今之世,胡近来二君又为《文史哲》向我索稿乎?故其为否定之批判,是可以原谅者也。”
顾颉刚原谅了当年的学生所给予的“过情之打击”、“无情之打击”,但当年的学生与他的冲突并未随着他的不计较而终结。他的学生对他的批判,本来就是以政治压力的大小为转移的,可以说是应付外在社会环境的一种手段。思想改造运动起来了,他们就通过对老师的“过情之打击”来跨过这一关,高潮过后,他们就又恢复了与老师的联系。可是,1949年后,运动接二连三,一个比一个严厉,所以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也就益发复杂化了,背景复杂的学生也就只好一而再、再而三地靠批判老师来超度自己。继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席卷知识界的另一场运动,是由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引发的对胡适的大规模批判。这一运动可以看做毛泽东发起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继续和深化。胡适是“现代中国的圣人”,1949年后,要想在中国文化界、思想界树立新的权威,非推倒胡适这座偶像不可。批判俞平伯不过是一个可供选择的突破口罢了。但这个突破口的选择与运动的真实指向,却对顾颉刚形成了双重的压力。一、顾颉刚不仅是俞平伯早年的同调和朋友,而且现在正作为靶子来批判的《红楼梦研究》的前身《红楼梦辨》的成书,亦与顾颉刚关系甚深。在《古史辨?自序》中,顾述及此事时说:红楼梦问题是适之先生引起的,1921年3月,他草成《红楼梦考证》,我最先得读。“我的同学俞平伯先生正在京闲着,他也感染了这个风气,精心研读红楼梦。我归家后,他们不断地来信讨论,我也相与应和,或者彼此驳辨。这件事弄了半年多,成就了适之先生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和平伯的《红楼梦辨》。” 现在,俞平伯的这本《红楼梦辨》受到清算,这当然构成顾的思想重负,也似乎强化了顾在当时的反面影响。二、批判俞平伯是为了进而铲除胡适在思想界、学术界的广泛影响,而顾颉刚是胡适的高足,学林无人不知。假如,俞平伯可以说明胡适在文学界的影响的话,顾颉刚则完全可以证实胡适在史学界的影响。所以,当批判《红楼梦研究》的运动迅速过渡到批判胡适运动时,顾的处境就日益因难与窘迫。
1955年3月5日,在中国科学院批判胡适思想会上,顾颉刚曾发言一小时,并在当天的日记中说;“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会上说个明白。” 当时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主要是在文学、史学和哲学三大领域中进行的,“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不可能不牵扯到顾颉刚和《古史辨》。当时,大概稍有头脑的人都很明白,胡适与“古史辨派”的渊源是如此之深,要搞臭胡适,不搞臭“古史辨派”是不可能的。于是,当时几乎所有批判胡适历史学的文章,无不明里暗里以“古史辨派”和《古史辨》为陪绑者。“古史辨派”又一次披放在了热鏊子上。看来,“古史辨派”成员除了进一步反叛师门之外,再无别的选择了。童书业不得不再一次走上了对“古史辨”进行“过情之打击”以实现自我超度的道路。
在批胡高潮期间,童先后著文3篇,刊发在《文史哲》杂志和《光明日报》上。据有关历史学论文索引,当时从历史学领域批判胡适的文章共70篇。童的文章与其他众多文章相比,就对胡适的批判而言,老实说,非常普通,非常不起眼。因为童本人并无显赫地位,文章也无“高深”的见解(童对“唯物史观”的修养根本无法与当时另一些名人比)。但童也有他的优势:胡适的再传弟子,特别是《古史辨》的编著人之一。在搞臭胡适不能不推倒《古史辨》的背景下,他的这一身份也就具有了相当的意义。童充分利用了他的这一优势。与其他众多文章不同,他的文章的独特之处,在于深入清算“古史辨”的影响,竭力把“古史辨”与胡适绑在一块儿批判。其中,以发表在《光明日报》(1955年2月3日)上的《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考据学”》最为典型。
在这篇文章中,童书业指出胡适实验主义考据学可分为两类,一类“带有明显的思想性”,另一类“表面上没有什么思想性”。在童看来,这两类考据危害性都很大。而“表面上没有什么思想性”的考据,因其“表面看来似乎无甚大害,实际上它的危害性是更巨大、更深刻的!”童把“表面上没有什么思想性”的考据视为“钻牛角尖”。他指出:“我的师友和我个人,过去也最喜欢作这类钻牛角尖的‘考据’。例如顾颉刚先生,对于‘红楼梦’,就下过很多这类‘考据’工夫,俞平伯‘红楼梦辨’里的‘考据’,许多都是采取顾先生的研究成果的。”——这时强调《红楼梦辨》与顾的关系,只能加重顾的“罪行”。尽管钻牛角尖的考据危害性“更巨大更深刻”,但童书业文章的重心,是批判胡适“带有明显思想性”的考据。在童看来,“完全继承并发挥”胡适“钻牛角尖”的考据的是“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而完全继承并发挥胡适富有学术之外的目的的考据的是顾颉刚的《古史辨》。所以,童书业此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顾颉刚的,是通过批判顾来批判胡适的。
据童说,有人为减轻顾的压力,说顾所接受的胡适的实验主义并不完全,顾也这样自认。童接着指出:“但我觉得在‘古史辨’中,实验主义的精神是很显著的。”童的强硬根据是:
顾先生的有名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分明是“井田辨”的“考据”方法的发挥和发展。胡适的“井田辨”认为井田本来是没有的,孟子凭空虚造出井田论来,自己并未曾说得明自,后人一步一步的越说越周密。这也就是“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观”。顾先生说:尧、舜、禹等人和他们的历史,都本来是没有的,西周以后的人一步一步的造出这些人和他们的历史来,越说越周密,所以这些人和他们的历史,都是“累层地造成”的。“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受胡适实验主义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胡适曾赞赏顾颉刚的下面这段话,并认为这是顾讨论古史的根本见解与根本方法:“我们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凡是一件史事,应看他最先是怎样,以后逐步逐步的变迁是怎样。” 童在另一篇文章中却强调指出:其实这种“根本见解”和“根本方法”,就是胡适自己传授给顾颉刚的。胡适说:“顾颉刚先生在他的古史辨的自序里,曾说他从我的水浒传考证和井田辨等文字里,得着历史方法的暗示,这个方法,便是用历史演化的眼光,来追求每一个传说演变的历史。”童据此断定:“这段话可以证明顾颉刚先生最早所用的讨论古史的见解与方法,就是胡适的见解与方法。” 在《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考据学”》中,童仍以铁案难移的口气说:“井田辨”就是七大册“古史辨”的前驱,在“古史辨”中,充满着胡适“井田辨”的精神。
1920年,在孙中山创办的《建设》杂志上,围绕着中国上古有无“井田制”及“井田制”的性质展开了一场论战。这场论战是由胡适向胡汉民的观点发难引起的。胡汉民在当时刊发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的研究》的文章中认为,井田制是自古相沿的一个共产制度,计口授田,土地公有。而胡适则致信商榷认为,井田制度是孟子理想的乌托邦,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存在这种制度。他的这一看法受到廖仲凯等人的反驳,他接着又作进一步驳辨,提出了“井田论沿革史”,这就是章书业所转述的那种“层累地造成”的过程。胡适对他这篇论井田的文章非常自负,童也认为“井田辨”是胡适“带有明显思想性考据”的代表作。胡文的结论是:“井田论是孟子凭空虚造出来的”,童认为:他这个结论的目的,是企图证明:“井田的均产制乃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古代并没有均产的井田制度”,“因为古代本没有均产的时代”。童感到,这些论断“完全显露出他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本质来了”。否认井田制在古代的存在,为什么和胡适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本质”有关呢?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都肯定人类进化史的初期有一个原始共产制或公有制存在,而且为他们所向往的未来社会是对原始共产制的否定之否定,是共产制在更高阶段上的回归。当时中国思想界左右两派都认定,原始共产制是未来共产制必定实现的历史根据。所以,胡适否定原始共产制的存在,一直被认为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铁证。童认为,“古史辨”派也自觉不自觉地具有这种企图:“胡适考证‘井田’的用意,是在证明‘古代没有均产的时代’,而‘古史辨’在胡适的实验主义指导之下的‘疑古’,也就变成原始共产社会的抹煞论了。”又说:“古史辨”派中了实验主义的毒,“所以敢于大胆抹煞古代的传说,抹煞史料的真实性,把中国原始社会完全否定”。还说:“古史辨”派认为“任何历史事实都可以用‘神话’两个字一笔抹煞:他们就用这种方法抹杀了全部的中国原始社会史”。而且,“古史辨”的理论,“不但是原始社会抹煞论、简直是历史抹煞说,这就是他们的所谓‘疑古’”。 可以感觉得到,童书业在写这些文字时,肯定是满怀“革命义愤”的。这进一步坐实了他在1952年的文章对“古史辨”派的定位:最初是右面抵抗封建阶级,左面抵抗无产阶级,最后则“只坚决抗拒无产阶级了”。这使人们意识到,“古史辨”派并不单纯是一个学术派别,而和胡适的考据学一样,带有一定的政治性质。
在童书业看来,撇开“古史辨”派的政治属性不论,仅就其史学方法看,也是非科学的。1925年4月,历史学家张荫麟曾在《学衡》第40期上刊发《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的文章,认为顾颉刚在论证“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时,其错误“半由于误用默证,半由于穿凿附会”。 他所指出的无限度地使用“默证”这一点,在当时被广泛认为是从方法论上击中了“古史辨”派的要害。现在,童书业重申了张荫麟当年的批评,认为这是“古史辨”派的史学方法非科学的强硬证据。他说:
这种史学方法不科学的最明显的证据,是它往往采用“默证”的方法。譬如顾先生说:西周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春秋时才出现了尧、舜,到战国时又出现了黄帝。他的根据是《周书》和《诗经》中只看见禹,而没有尧、舜,《论语》等书中只有尧、舜,而没有黄帝。到战国的书中才看见黄帝。所以尧、舜比禹晚出,黄帝比尧、舜晚出。但是短短不到二十篇的《周书》和三百篇古诗,其中还只有一部分是西周的作品,根据这么少的文献,就断定西周时还没有尧、舜;又根据短短二十篇的《论语》,就断定春秋时还没有黄帝:这样的方法,还能说是科学的么,万一《周书》和《诗经》中提到禹的那八篇失传了,《论语》中提到尧、舜、禹的那两篇也失传了,我们是否可以断定尧、舜、禹在春秋时还没有,而到战国时才出现呢?这种史学方法的错误,只要一研究后出的历史,立刻就会发现出来……
童的结论是:“古史辨”派的“考据”方法是不科学的:针对“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是建立在“默证”方法基础上,而“默证”方法众所周知是不科学的批评,当年被童书业许为“古史辨的集大成者”的杨宽在1991年指出:“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古史传说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依靠默证来建立的,不是仅仅由于某个时期不见某帝或某王,到某个时期新出现某帝或某王。古史传说的层累地造成,主要从神话的层累地发生演变而形成。神话演变的现象才是他的主要论据。张荫鳞的批评只是误解。”杨宽的评判看来包含有更多的合理性,可以看做是自张荫麟以来所有从使用“默证”的角度对“古史辨”发出的批评的总回答。
让我们继续看童书业对他老师的史学方法的批判。随时把他的老师与胡适绑在一块批判,是童前后所写几篇文章区别于当时众多文章的特征。他从1952年的文章就说顾颉刚运用了“默证”方法,现在他更深入地剖析道:
“古史辨”派的“默证”“考据”法,是与胡适所说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实验主义“考据”方法分不开的。根据“默证”,就可以否定一切,这不就是所谓“大胆的假设”吗?但是“古史辨”派在初期时,使用罗织锻炼的方法,即所谓“小心的求证”的方法,还不很够,充分使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在“古史辨”派后期的著作中,才显著起来。应当承认:我就是使用这种方法最充分的人。抗战前夜,我与顾颉刚先生合作的“夏史三论”,就是使用这种方法的最典型的作品,这篇文章最主要的结论,是:夏代不自中绝,后羿篡夏,寒浞篡羿,少康中兴等故事,都是东汉光武中兴以后的人所伪造的。这个“假设”,不能不说“大胆”了,所搜罗的证据,有正面的,有侧面的,有明证,有默证;可说极罗织锻炼之能事;在“小心的求证”方面,确实超过胡适而“青出于蓝”了。当时颇有人相信这个结论,但是根据我现在的观察,这个结论是完全不可靠的!
童书业接着阐述他现在的认识,以说明原来的结论之不可靠。后断然指出:
实验主义者所谓“大胆的假设”, 实际上就是主观武断,所谓的“小心的求证”,实际上就是罗织锻炼。所以实验主义的“考据学”,确实是主观唯心论所支配约“考据学”,根本谈不上有一丝一毫的科学气息!“古史辨”派中了实验主义的毒,所以敢于大胆抹煞古代的传说,抹煞史料的真实性,把中国原始社会史完全否定。
上纲不可谓不高,批判不可谓不激烈。至于童这时对“古史辨”的总体估价,与1952年的文章—样,仍然近于全盘否定:
自从胡适挥起实验主义的斧头乱砍,再加上“古史辨”派的附和,许多古书、古事和古人,就都被砍掉。他们的余毒一直留存到今天,现在还有许多人不敢根据《周礼》、《管子》等古书来研究古史。这样就把许多宝贵的史料丢弃不用,严重影响到古史真相的探索。
顾颉刚对童书业这几篇文章所持的严厉态度有什么反应,受材料限制,不得而知。不过,既然顾在1954年就已认识到童书业1952年的“过情之打击”是“渠等应付思想改造”的权宜之计,那末,面对童书业的新的批判,顾颉刚也可能仍会以政治表演视之,不可能认真对待的。
假如真的是这样,那顾颉刚不愧是“先生”。童书业的日子这时实在太难过了,在随后而来的由批判胡风引起的肃反中尤其如此。前曾指出,面对一道又一道难关,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为了解脱自己,不惜牺牲师友。而且,从批判胡适运动来看,谁过去的成就越大,现在的表态和表现就越积极,过去的声名、影响越高,现在批判起别人来就越卖力。对多数人来说,公开场合的积极和卖力,并不说明他们“立地成佛”了,很可能是他们的一种生存策略,一种掩盖,一种对自我的洗刷,一种自我防护。童书业是这样,顾颉刚也并不例外。顾颉刚在“思想改造运动”之前,就与“适之先生”划清了界限;在胡适批判高潮中,又在全国政协第二届全体会议上,当众检讨了自己的兴趣主义的治学倾向,并认为胡适的实验主义研究方法,“乃是腐朽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方法,他的一切学术工作乃是替封建势力和美帝国主义服务、转移青年目标、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手段”,承认自己“是在一定程度上替他造成他的虚名和声势的一个人”。 顾这样做,很可能也是在“应付”思想改造等运动。因为顾后来坦言:他虽然参加了当时的“思想改造运动”,但那是为了能“在大学教书”。而真实的想法是:“思想而能改造,在我的旧脑筋里简直是一件不能想象的奇事。”他自己认为,自从“入了社会,就只知道发展个性,过自由散漫的生活,永远‘称心为好’,不知道有什么服从领导、集体生活、群体路线这些事情”。现在“要我‘舍己从人’,抛却我原有的看家本领而唯党是从”,于心不甘。所以,当他到京之后,所在单位负责人批评了他,他反应强烈:“我一向‘傲骨凌嶒’,受不了别人的‘气’,听了这些有强烈刺激的话直使我眼前发黑,几乎倒了下去。”认为这位领导“损伤了学术研究的尊严,因此要和他拼一下”,以至“逢到公开场合要我说话时,我就把这些事提了出来”。一时“反领导的情绪十分高涨”。 在他看来,这是在“抗拒改造”,而在这同时,他正在当众大批胡适,以示接受改造。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