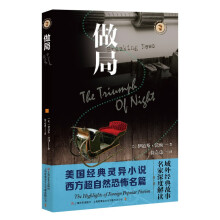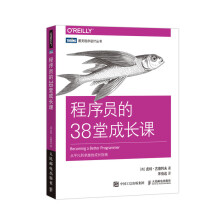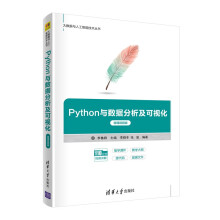第一章 我们为什么藏书<br> “不问从哪儿来,不问到哪儿去,我只惊讶我怎么这么快乐。”天使般快乐的漫游者所吟唱的这些轻松(也许只是看似轻松)的诗句必定博得许多收藏家的共鸣,他们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对收藏的动机以及何去何从的问题做出解释。确实,最重要的是让收藏成为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不要过于瞻前顾后,更不要劳心费力地试图去为一件别人反正不熟悉、不理解的事情进行辩护。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收藏家和非收藏家没完没了地苦苦追究收藏的意义和动机。各种文献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解释和分析,有人慷慨激昂地高唱赞歌,也有人以怀疑的眼光对收藏活动提出了道德批判。本书既不可能一一罗列所有这些意见和看法,更不可能对它们进行比较和评估,然后得出某种结论来。<br> 但是如果一个收藏家对正反两面的意见都稍加研究,然后细细斟酌他自己的收藏动机和立场,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几乎每个收藏家的动机都不止一个,而是由各种不同的动机组成了一个混合体。单个动机在混合体中的分量对比就构成了这个收藏家的独家特色。而且,这个动机混合体在收藏过程中极有可能发生变化和挪移,比如一个收藏家收藏了三十年后,可能突然改变初衷,从别的动机出发,采取别的标准继续他的收藏活动,甚至在一开始对他特别重要的起主导作用的动机,到后来变成了他自己批判和排斥的对象,这种情况也不罕见。<br> 美国记者尼古拉斯.A.巴斯班斯(Nicholas A.Basbanes)几年前曾写过一本讲藏书家的书(重点是美国的藏书家),写得非常引人人胜,书名也很可爱:《文质彬彬的疯狂》。如果允许我现在就预先透露结论,那么我要说,对于几乎每一个收藏家都适用的真正的关键词也许就是:傻得可爱(那些身陷其中的人还傻得不亦乐乎)。<br> 为了在一开始就对收藏活动中情感因素的魅力有所认识,让我们来看看瓦尔特·本雅明(Waiter Benjamin)是如何评说收藏动机的,他在一篇小随笔《我清理我的藏书室》中说道:<br> ……反正我下面的这些话,意在说明某些浅显明白的道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让您了解藏书家与他的藏书的关系,了解收藏本身,而不仅仅是了解藏品……每一种激情都近于骚动,而藏书的激情则近于回忆的骚动,但我想说的还不止这些。在我眼前,过去的岁月被染上了偶然和命运的色彩,而在那些我已司空见惯的乱书堆中,也正有这种色彩在熠熠生辉。藏书家所拥有的无非是混乱,他们对这种混乱如此习以为常,以至于视之为秩序。您肯定听说过有人因为失书而抑郁成疾,有人为了得书而成为罪犯,在这些情形中,每一种秩序都不过是悬浮于深渊之上的暂时状态。“唯一确切知道的,”阿纳托尔·弗朗斯曾说,“就是书籍的出版年月和开本大小。”说真的,如果说还有什么东西能与藏书室的杂乱无章相抗衡,那就只有井井有条的藏书室目录了。<br> 于是,藏书家的生命线就紧绷在混乱与秩序这一对辩证关系的极点之间。<br> 当然还有许多别的因素,比如藏书家与他的占有物之间不可思议的关系——这个后面还会提到——在这种关系中,物对于人的价值首先不在于它的功能,也就是它的实用性,而在于人可以将它看成它自己命运的活动舞台,从而研究它,爱护它。最让藏书家陶醉的事情就是把一件件藏品关进禁区,让它们在最后的惊悸——被俘的惊悸——烟消云散之后,呆呆地站在里面发愣,他的一切回忆、思想和意识就是他的财产的基石、底座、框架和锁闩。对于真正的藏书家来说,他的每一件财物的产生年代、产地、工艺和前任主人都能汇集成一部引人入胜的百科全书,所有这些因素构成的整体就是藏品的命运……重建旧世界——这是藏书家寻求新藏品的最深层的动力。<br> 瓦尔特·本雅明这些玄妙的思想可以让我们做好情绪上的准备,下面我们就以比较客观冷静的方式展开关于收藏动机的讨论。<br> 每一个上过历史课的人都知道猎人和采集者的概念,那是人类最早的存在形式。很多人都在思考,在现代社会文明的收藏方式中是不是还有这种以狩猎和采集为生的早期人类的原始本能在微微发光。反对这种说法的理由首先在于:绝大多数现代人对于决定生活方式的收藏活动并不理解或不太理解,再说,性情中带上原始人烙印的也并不一定非得是藏书家。但是,对于不少藏书家来说,猎取和猎取中的乐趣是最重要的——就像猫捉老鼠——这也是不可忽略的事实。在苦苦寻觅了很久之后,意外收获的时刻往往是极为难忘的,以至于——瓦尔特·本雅明也提到这一点——这份感情牢牢地固结在猎物上,决定了猎物的价值。关于收藏中的原始冲动的因素,让我们就这样点到为止,下面我们来对别的收藏动机进行归纳整理。<br> 很多收藏家的首要动机是喜爱美好的事物。阿路易斯·哈恩(AloisHahn)在一篇名为《收藏家社会学》(1984)的文章中说道,收藏家往往对艺术有强烈的亲和性,藏书家肯定也不例外。对于他们来说,书不仅仅是文本或知识载体,而且还是艺术品,这一点我们将在第三章中详细讨论。很多人认为,把书籍当成艺术品看待,一如洛可可的银器或青春艺术风格的玻璃杯,对书籍的外表和内容一视同仁,甚至把外表看得更重,这有失书籍的身份。1965年曾有过一次令人难忘的展览,展出的是大藏书家汉斯.菲尔斯滕贝格(Hans Fiirstenberg)收藏的法语书籍,展览的主题就是“书籍作为艺术品”,在第三章中将对这个命题做出论证。<br> 收藏的第二个重要动机是抢救与保存。收藏行动表达的是怀念和崇敬之情,其对象是我们文化中的有形遗产,是那些曾经辉煌的东西,如果没有收藏家,它们最终将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得无影无踪,所以本雅明谓之“重建旧世界”。但是,要想在收藏实物的过程中通过“抢救工作”把过去“如实”地保存下来,那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就像史家撰史一样,也不过是一种构想,不论收藏家怎么努力,不让自己的好恶左右他的收藏行动,他自己一手缔造的那个属于他一个人的世界还是难免要带上主观色彩,这既表现在他选择最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的藏品的过程中,也表现在他阐释他的选择的意义的时候,本雅明指的也许就是这样的主观再造。<br> 即便不可能通过收藏如实地再现过去,深藏其中的那种动力还是有其重大的文化意义乃至社会意义:无数的文化物质遗产,如果不是古往今来的收藏家在它们濒临灭绝的紧急关头收藏和保存它们,它们早就失传了。<br> 有些收藏家也许一开始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保存工作的重大意义,他们的出发点只是一个“慰情聊胜无”的念头,就像维吉尔的诗句所说的:forsan et haec olim meminisse juvabit——“说不定哪天这能帮助回忆”。而在字面意义的回忆之外,一件件实物还能让我们在主观想象中再造过去——每一件藏品中都有一个世界,那是核桃壳中的世界,或水滴中的世界。很多收藏家都是为情所动,陈年旧物会勾起他们浓浓的怀旧之情。烫金已失去光泽,纸张已泛黄,昔日存书的屋子已不复存在,但屋里的幽香沁人书中,让我们重温了当年读者们发自内心的欢笑、悲泣或惊叹,而这些读者逝去已久,如今已无人记得他们了。<br> 藏书的第三个动机是个人对于某个特定主题或人物的强烈兴趣,比如拿破仑的忠实崇拜者就可能收集一切与拿破仑有关的书籍。如果一个人非常热爱他的家乡或别的什么地方,他就可能收藏地貌学书籍,以此熟悉当地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简直想要把它们都吞到肚里去。收藏家借助藏品不断地深入这个领域,每增加一件藏品,他的收藏主题就更加丰富、更加深化、更加清晰。 <br> 在个别情况下,收藏家可以“发明”一个领域,或至少是“发明”一个视角,也就是在赋予意义的再创作中创造新的价值。这听上去很玄妙,但并不一定非得是多么复杂的收藏。比如有人决定收藏所有18世纪在莱姆戈(Lemgo)印刷的书籍,而有人想收藏包括文字在内完全用铜版印刷的书籍。乍一看,这都算不上是什么野心勃勃的计划,但实际操作起来绝对是要求很高,困难很大的。事实将证明,像这样收集起来的书籍,会开辟一个此前无人认识到的全新的关联环境。整体价值大于个体价值之和,按照这条规律,这样的藏书可以获得新的内容价值,甚至经济价值也会得到提高。当然,一般说来,后者绝不会是这种有创见的固执的收藏家的动机,他们更注重的是创造一个自己的“世界”,通过将彼此和谐的藏品收集在一起,使这个“世界”成为一件独特的艺术品。<br> 当国王问特利沃尔齐奥元帅发动战争最需要什么时,元帅答道,最需要三件东西:钱、钱、钱。但是收藏不然,首要的并不是钱,我也想并不十分正式地归纳出三样收藏所需的不同的“Ge”来:耐心、记忆力、金钱,其中前两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补足后者的不足。<br> 在耐心和记忆力之外还有一些别的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纽约的艺术品大收藏家冈茨(Ganz)所具有的那些品质。1998年,冈茨的遗产拍卖收入超过两亿美元,创下了私人艺术品收藏的拍卖收入纪录。冈茨夫妇虽然比较有钱,但并不是富得流油,他们收藏成功有别的奥秘,克里斯蒂拍卖行在拍卖通告里以感人的笔触,对此做出了非常中肯的评价:<br> 激情,无穷无尽的精力,也许再加上点儿好胜心,这就是大收藏家的品质。在任何自己所钟情的领域里都想拥有最好的物品,最稀有的式样,这就是所有的收藏背后的推动力。但是,使得整个集合体出类拔萃的却是它的基础结构,积累不等于收藏,毫无意义的堆积是没有价值的。大收藏家总是从认知意义的角度安排他的藏品,试图通过出入意外的组合加强整体效果,在看似零散的物品间建立某种关联,往往以标新立异的构成挑战精神的眼睛。<br> 这几句话也许对任何一个收藏家都有用。在这儿也许该暂时中断关于收藏动机的讨论,而先来看看该如何定义藏品,在值得收藏的物品和其他普通物品之间是不是可以通过某种定义划出一条实用的界线来。只要对收藏活动稍加注意,就会发现划清界线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因为其价值得不到广泛认可就不可以系统收藏的。一个巴洛克绘画的收藏家也许会瞧不起纸印章的收藏家,或者一个收藏古钱币的人会瞧不起收藏橙子包装纸的人,即便在藏书家内部意见也并不一致,许多藏书领域让某些人乐此不疲,却让另一些人摇头不已,表示不理解。<br> 所以说,一样东西能否成为藏品,没有客观标准,不能指望谁都理解自己的决定。藏品几乎只能通过循环论证法来加以定义:一样东西只要有人收藏,它就是藏品。所以我们可以考虑收藏一本别人作为宣传品赠送的儿歌小册子,要是能攒起上百本这样的小册子,那无疑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小收藏。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难以驳倒的结论,那也就无所谓什么是真正的(重要的、有意义的)收藏,什么是非真正的(没有文化品位的、无价值的)收藏了。成功的收藏更多地取决于行动的决绝和藏品的丰富精炼,而不是取决于主题和藏品的“重要性”。所以,很多以歌德为主题的收藏并不见得有多大价值,而一些出色的收藏却以“不重要”的作家为主题,或者有着别的冷门的主题。决定收藏质量的不是有些人观念中的主题的崇高或平庸(只有盲目崇拜文化教育的庸俗之辈才会这么想),而是做事的方式。<br> 按照时下流行的观点,定义一件物品是否具有艺术性,要看它在艺术爱好者(艺术学家、批评家,还有收藏家)眼中能否算得上是艺术品,别的藏品也是这样,书也不例外。很多被人收藏的书并不比决斗用的手枪或中国瓷器更有用,它们就是藏品,别的什么也不是。它们的意义随着收藏理念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br> 通过博物馆化,也就是通过被人收藏,物品的意义发生了变化,<br>正因为如此,收藏活动才如此引人人胜。文化哲学家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在不久前阐明了这一点,他的论述是非常令人信服的:把一件农具放进陈列柜,它的功能和意义就会发生根本的变化,就像被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放进展览馆的布里洛盒子3一样,如果这件农具又回到商店或粮仓里,那么它就又失去了艺术性。物品被人收藏后就脱离了原来的用途,而进入一个新的环境。书也一样,虽然书的“真正”功能——可读性——始终保持不变,但是它的收藏价值越高,这个功能就越靠后,而跃居首位的是它作为实物、作为历史与美学的见证的功能。同样一本书,被A收藏也被B收藏,其意义可能是根本不同的,甚至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只有那些从一开始就是为了收藏目的而制作的书籍,尤其是豪华版书籍和艺术家书籍,才能在被人收藏后保持原来的功能,其他所有的书一开始或多或少都带些日用性质,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地物以稀为贵了,才在收藏中变成了另一件东西。<br> 这一点被藏书家们奉为圣物的初版书表现得尤为明显:当初普普通通的一本书(作者在当时往往还名不见经传),如今虽然本身还是其貌不扬,但被人当宝贝似的藏在金饰辉煌的摩洛哥羊皮书套里,最初的买主花几个小钱就能买回家的一本平装初版书,如今它的功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阿路易斯.哈恩在前面已提及的那篇文章中说道:“这里所说的藏书家事实上并不使用他的书,他只是喜欢它们的存在……这样的使用已经带有亵渎的性质……偶尔使用一次,简直像在举行庆典仪式。”<br> 这就像一个焦点,其中融合了人们对,于收藏的正反两面的评价。正面评价:收藏使得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保存,并得到毕恭毕敬的呵护;反面评价:收藏的原动力是一种贪欲,收藏家意欲建立一座宝库,这座宝库任何人不得靠近,有时甚至包括他自己。<br> <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