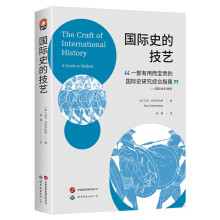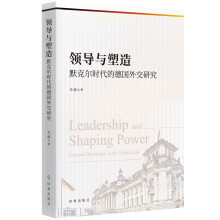第一章 每日每处
半真半假
1014年,伍尔夫斯坦大主教(Archbishop Wulfstan)在约克郡布道时宣称,“世界一片混乱,末日即将来临”。至少从那时起,甚至更早,人们就相信一切正变得越来越糟,美好的事物正一天天离我们远去。许多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与此相似,都有一个预设,即世界正迅速地陷入毁灭之中。几年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回应了他一千年前的同事,用下面的话概括了世界的发展。
各地都在见证着某种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的复兴,它使人类盲从于市场力量,并使人类的发展受到这些力量的限制……因此,在国际社会中,我们发现一小部分国家正变得极其富裕,他们富裕的代价则是其他大多数国家日益贫困化;结果是富者更富,穷者更穷。
据说,这世界正变得越来越不公平。关于市场经济的辩论异口同声地说道:“富者更富,穷者益穷。”这一论述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自然法则,是一个毫无疑义的论题。但如果我们透过这一耳熟能详的口号,去研究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半真半假”的命题。命题的前半部分是正确的,富者的确变得越来越富——尽管不是所有富人都更富了,但总体而言,的确如此。我们这些有幸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在过去几十年中的财富增长相当可观,那些第三世界中的富人也一样。但这个命题的后半部分则完全是错误的。从总体上来说,在最近几十年中,穷人的境况不仅没有变得更糟糕,相反,绝对贫困已经大为缓解。
在贫苦者数量最多的地区——亚洲,数亿人的生活已经有了一定保障,甚至达到一定程度的富裕;而就在20年前,他们还在为满足最基本的需要而苦苦挣扎。在全球范围内,贫困都已经减少,人们已经开始解决严重的不公平问题。作为全书开篇的本章,将为大家呈现一长串的数据和趋势描述,而这些数据和描述,对于纠正对世界状况的普遍误解是必不可少的。
在近几年出版的妙趣横生的著作中,有一本叫做《亚洲的时代:印度、中国和日本1966-1999》。这是一本游记,瑞典籍作者莱斯。伯格(Lasse Berg)和摄影师斯蒂?卡尔森(Stig Karlsso)在书中描绘了他们曾经踏足的这些亚洲国家。他们曾在20世纪60年代到过这些国家旅行。那时,他们触目所见的尽是贫穷、无望的悲惨和即将来临的灾难。跟来到这些国家的其他许多旅游者一样,他们对这些国家的未来不抱有太大希望,并且认为,社会主义革命是唯一的解决办法。20世纪90年代,当他们再次回到印度和中国时,他们发现,自己曾经的判断是多么错误。在这两个国家,越来越多的人从贫穷中解脱出来;饥饿问题正稳步消除;街道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破旧的泥草屋让路于整齐宽敞的砖瓦房,家家户户都用上了电,屋顶上也支起了电视天线。
在伯格和卡尔森第一次访问加尔各答时,有10%的居民无家可归,每天早晨,政府或教会组织会派出卡车,四处寻找并收集这一夜中死亡者的尸体。30年后,当他们准备去拍摄街头流浪者时,他们发现,很难找到这样的人了。黄包车已经在这座城市中消失,人们的出行工具变成了汽车、摩托车和地铁。
当伯格和卡尔森拿出他们上次访问时拍摄的照片,就在这些照片被拍摄的同一地方,给印度的年轻人看,而这些年轻人简直无法相信这居然就是同一个地方。他们不能相信,这个地方曾经是如此苦难和可怕!在他们书中的第42页有两张图片,可以用来说明这一惊人的变化。摄于1976年的旧照片中,12岁的印度小女孩萨图(Satto)伸出了由于多年的辛苦劳作而满是裂口的双手,相对于年龄而讲,这双手实在是太粗糙了。而最近的照片拍摄的是萨图13岁的女儿舍玛(Seema),她伸出的是一双年轻而柔软的,属于孩子的手,这说明她的童年没有被劳作剥夺。
最大的变化其实在于人们的思想和梦想。电视和报纸带来了世界另一半的观点和图景,打开了人们的视野,让他们能够设想,自己能够做些什么。为什么我们要将自己的终身耗在同一个地方?为什么妇女必须被迫早生孩子而牺牲掉自己的事业?为什么婚姻必须被包办?为什么贱民(the untouchables)必须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为什么其他国家的家庭关系可以是那么自由?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可行的政治制度,而在这里却只能是这样一种政治制度?
莱斯.伯格以一种自我批评的口吻写道:
我阅读了我们这些观察者,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印度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写的东西,在这些分析中,我不能找到任何有关今日印度的痕迹。通常都是噩梦一般的景象——人口过多、喧嚣、动乱或者是停滞不前,那时的我们不能想象会出现现在这样稳定的发展,更不用说是现在随处可见的现代化的思想和梦想。有谁预见到消费主义的生活观会如此深入到偏僻的乡间?又有谁预见到经济状况和普遍的生活水平都是如此之好?回想起来,这些描述的共性是,它们都夸大了异乎寻常的、令人恐惧的或不确定的事情(大多数作者有个人的情结、喜好或习惯),同时却低估了发展的固有的主导力量。莱斯?伯格展现给我们的累累硕果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恰恰相反,是过去几十年中追求更多个人自由的运动的结果。自由选择和国际交流增多,投资和发展援助既传播了思想,又带来了资源,使得发展中国家也可以从他国的知识、财富和发明中获益。
医药的进口和新的医疗保健体制大大改善了人们的生活状况。现代技术和新生产方法提高了产量,增加了粮食供给。公民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出售自己的产品。通过统计数据,我们可以说明这如何增加了国家财富,减少了贫困人13。但最为重要的还是自由本身,是自治将独立和尊严带给了曾经饱受压迫和欺凌的人民。
由于人道主义观念(humanistideas)的传播,几世纪前还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奴隶制度,在一个又一个大陆被推翻。时至今日。尽管它还非法存在着,但自从1970年阿拉伯半岛上最后一批奴隶解放之后,奴隶制几乎在地球的每一处都被禁止。前资本主义经济时代盛行的强迫性劳工,正迅速地被市场蓬勃发展带来的签约自由和流动自由取代。
缩减贫穷在1965-1998年间,全球人口的平均收入实际上翻了一番,根据购买力和通货膨胀进行了调整之后的数字是从2497美元增长到4839美元。这一增长并不是由工业化国家增加了其收入而带来的。在这一期间,世界上最富裕的五个国家的人均收入从8315美元增加到14623美元,也就是大约75%。而世界上最穷困的五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更快,在同一时期翻了不止两番,即从551美元增加到了1137美元。到了今天,全世界的总消费量是1960年的两倍还多。
多亏过去半个世纪的物质发展,全世界有超过30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上。这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联合国开发署(UNDP)观察到,总而言之,在过去50年中世界贫困水平下降的程度比先前的500年中所下降的总和还多。联合国开发署《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写道,人类正处在“第二次大上升”(Great Asced)时期。第一次大上升始于19世纪,当时的美国和欧洲工业化处于兴起阶段,繁荣随之迅速扩展。第二次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在正处于全盛时期。这期间,首先在亚洲,然后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反对贫困、饥饿、疾病和文盲的战斗取得了从未有过的伟大胜利。报告最后宣称:
20世纪减少贫困的伟大胜利表明,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根除严重的贫困是可以实现的。山
贫困仍将迅速地减少。通常人们将“绝对贫困”定义为每天收入少于1美元的生活水平。在1820年,世界人口的85%生活在低于每天相当于1美元的水平。到1950年,这一数据下降到50%,到1980年,则进一步下降为31%。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80年以来,绝对贫困率从31%下降到20%-24%这个数据也经常被提到,这是指不计人发达国家中的绝对贫困人口,发展中国家中绝对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为24%)。在过去20年中出现的这种快速下降现象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因为它不仅意味着绝对贫困人口比例的下降,更在于绝对贫困的总人数的下降——而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要知道,在这20年中,世界总人口增加了15亿,但绝对贫困人数依然减少了2亿。这一下降与经济增长是密不可分的:在经济增长最快的地方,贫困也消除得最有效。在东亚(除了中国),绝对贫困从15%下降到略多于9%;在中国,则从32%下降到17%。1975年,亚洲人中十个有六个处于绝对贫困状态,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现在,每十个人中只有不到两个人还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这些数据令人鼓舞,但还是明显高估了世界的贫困程度,因为世界银行采用了大家都知道不大可信的
调查数据作为其评估的基础。世界银行前经济学家瑟吉特。巴拉(Surjit S.Bhalla)最近发表了他自己的计算,作为对以国家统计数据为基础的调查结果的补充。他有力地证明,这一方法的重要意义不仅仅在于提供精确的测量方法。巴拉发现贫穷急速减少。从1980年44%的水平下降到2002年底的13%,这一数字要比世界银行的数字更为可观。如果这些数据是正确无误的,那么过去的20年就出现了贫困率非同寻常、史无前例地降低的现象——至少是其他任何有记录的20年中所能达到的两倍。这样,联合国的目标,即到2015年将贫困人口减少到15%以下,不仅早已达到了,而且大大超过了。山
“但是,”怀疑主义者追问,“在发展中国家,人们难道真的需要消费和发展吗?为什么我们要将我们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他们?”答案是,我们的确不应该将一种特别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任何人。但是,不管他们的评价是什么,世上的大多数人都非常渴望更好的物质条件,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们将会因此而拥有更多的选择,而用不着我们去考虑他们到时如何决定使用这笔新增财富。如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Sen)所强调的,贫穷不仅仅是个物质问题。贫穷是一个更广泛的范畴:它意味着没有权力,意味着被剥夺了基本的机会和选择的自由。收入低下通常表明人们缺乏这些东西,表示人们被边缘化或者受制于高压统治和强制。人类的发展意味着可以享受健康并且不为生存担忧,意味着达到一个良好的生活水平并且能够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研究物质的发展是很重要的,因为它不仅能给出如何创造财富的建议,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能对发展作出贡献。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物质资源,都能使人们填饱肚子、接受教育、获得医疗保健,而且,不用再忍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死亡的痛苦。人们发现,一旦人类被允许自己做出选择,以上这些就是全世界每个人的愿望。
人类状况的世界性改善反映在平均预期寿命的迅速提高方面。20世纪初,发展中国家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还不到30岁,1960年增长为46岁,到1998年是65岁。发展中国家人口现在的预期寿命比一个世纪前处于世界顶尖经济体的英国的预期寿命还要高出大约15岁。非洲南撒哈拉地区的发展是最慢的,但即使在那里,预期寿命也出现了增长,从20世纪60年代起的41岁增长到现在的51岁。在最富裕的国家,平均预期寿命仍然保持最高——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平均寿命是78岁,但最快的改善发生在穷国。1960年,穷国的人均寿命是富国的60%,现在已经超过了80%。当今世界90%的人都有可能活到60岁以上,这是100年前平均预期寿命的两倍。
在《亚洲的时代》一书中,伯格描述了30年后第二次访问马来西亚的情况,他突然意识到,在这30年中,平均预期寿命增长了15岁。这意味着,按当时的预期寿命,他上次访问时看到的那些人,本来只有半年可活了,但实际上,现在他们却仍然可以好好地活下去。
健康的改善部分源自饮食习惯和生活状况的改善,但也得益于医疗保健的改进。20年前,每千人中才有一位医生,现在是每千人有1.5位医生。在极度穷困的国家,1980年,每千人有0.6位医生;现在,这一数据几乎翻了一番,为1.0位医生。衡量穷人生活状况的最可信的指标,可能是新生婴儿死亡率,该指标在发展中国家正在快速降低。1950年,18%的新生婴儿——几乎是五分之一!——死亡,到1976年,这一数据下降为11%,1995年只有6%。在过去的30年中,死亡率几乎又减少了一半,从1970年的每千名新生婴儿死亡107人,到1998年每千名新生婴儿死亡59人。尽管仍然没有脱离贫困的苦海,但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生存下来。尽管穷国有越来越多的人生存下来,然而,全球人EI处于贫困状态的比例却日益降低,这反过来证明了,贫困率下降的幅度要比肤浅的统计研究显示的结果大。
饥饿
更长的寿命和更好的医疗条件与欠发达的另一个最为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饥饿——的减少有关。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第三世界的人均卡路里摄人量增长了30%。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统计,70年代,发展中国家有9.6亿人营养不足。1991年,这一数据是8.3亿,到1996年为7.9亿。根据人口比例,这个改善速度非常迅速。30年前,发展中国家大约37%的人口受到饥饿的折磨。今天,这一数据少于18%。仍然很多,是吧?是的。太多了,对吗?当然是的。但数量在急剧减少。瑞典用了20世纪的头20年来消除长期的营养不良,相比之下,仅仅在30年中,世界的饥饿比例就下降了一半,并且有希望进一步减少,到2010年达到12%。
地球上从来没有今天这么多的人口,也从未有过如此充足的食物供给。在20世纪90年代,就饱受饥饿之苦的人口而言,绝对数量平均每年下降600万人,而同期,世界人口大约每年增长8000万。在东亚和东南亚,这一切发生得更快,饥饿比例从1970年的43%下降到13%;在拉丁美洲,从19%下降到11%,北非和中东则从25%下降到9%,南非从38%下降到23%。发展最糟的地区是撒哈拉以南非洲,饥饿人151数量实际上增加了,从0.89亿到1.8亿人。但是即使在那里,处于饥饿中的人口比例还是下降了一些,尽管微不足道:从34%下降到33%。
在过去半个世纪,全球粮食生产已经翻了一番,在发展中国家增加了三倍。1961-1999年间,全球粮食供给增加了24%,人均每日热量摄人量从2257卡路里增加到2808卡路里。最快的增长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热量摄人量增加了39%,每日卡路里消耗从1932增加到2684。这一发展不是由于将新的土地转变为农业用途,而是由于原有土地的耕作效率得到了提高。每英亩可耕种地的产量实际上翻了一番。小麦、玉米和稻谷的价格下降超过了60%。
自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食品价格下降了一半,某些地区的土地产量增加了25%——这一过程在穷国比在富国更快。这是“绿色革命”的胜利。人们培育出了产量更多、抗病性能更好的作物,同时,播种、灌溉、施肥和收割方法都有了重大改进。产量更高的小麦新品种占了发展中国家小麦总产量的75%,估计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由于这一改变,已经获得了大约50亿美元的额外收入。在印度南部,据估计,在过去20年中,绿色革命已经使农民的实际收入增加了90%,使无地佃农的实际收入增长了125%。绿色革命的影响在非洲是最小的,但即使在那里,它也使短莲亩玉米产量增长了10%-40%。如果没有绿色革命,据估计,世界小麦和稻谷价格将比现在的价格高出大约40%,而且世界儿童会另有大约2%——这些孩子现在有足够的粮食——将遭受长期的营养不良。今天的粮食问题与人口过多没有关系。今天的饥荒问题是如何得到知识和技术,如何得到财富,以及如何保持使粮食生产能够正常进行的稳定环境。许多研究者相信,如果我们能将现代化的农业技术运用到全世界的农业生产中,我们现在立刻就可以养活另外10亿人口。
严重饥荒的发生率也显著减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主制度扩散的结果。饥荒在每一种社会形态下都发生过——共产主义社会、殖民帝国、技术官僚主导的国家和古代的部落社会。在所有的饥荒中,都存在着中央集权的政府,以及压制自由言论和市场运行的情况。阿玛蒂亚.森观察到,在民主政体中,从未有过大饥荒。即使民主不发达的国家,如印度和博茨瓦纳,也成功地避免了大饥荒,哪怕这些国家的粮食供应比发生饥荒的国家还要少。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如中国、前苏联、柬埔寨、埃塞俄比亚和朝鲜,以及殖民地,如英国统治下的印度,都经历过大饥荒。这表明,饥荒是由独裁政权引起的,而不是粮食短缺造成;饥荒是由于领导者毁坏生产和贸易、制造战争并忽略饥饿人口的困境才得以发生的。
森之所以坚持认为,民主政治下鲜有饥荒,乃是因为,如果一个社会的统治者愿意去防止饥荒,那就可以很容易地防止饥荒。统治者可以减少对粮食分配的各种阻碍来防止饥荒,可以在危机时为投有能力购买粮食的人创造就业机会。但是,独裁者没有任何压力:无论他们的人民吃得多么糟,他们自己都可以吃饱;而民主政体中的领导者如果不能解决粮食分配问题,他们就会下台。另外,自由的舆论可以使普通公众意识到问题所在,使得这些问题可以得到及时处理。而在独裁政体中,即使是领导者也有可能被新闻检查制度蒙骗。许多证据表明,在1958-1961年的“大跃进”时期,中国有3000万人死于饥荒,但中国的领导人却相信了他们自己的宣传和下级操纵的统计数字。
在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他们所需要粮食的同时,饮用水的供给也翻了一番,这对发展中国家减少疾病和传染病是非常重要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大约80%的人都可以得到纯净的水。而在一代人以前,世界90%的农村人口得不到纯净的水,今天,这一数字只有25%。在20世纪80年代初,印度只有差不多一半的人可以得到纯净的水,而十年后,这一数据超过了80%。在印度尼西亚,这一比例从39%上升到62%。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国家使用的水,大部分都是通过海水淡化处理的,因为海水可以无限制得到。海水淡化的费用很高,但这恰好表明了,社会繁荣可以解决资源稀缺的问题。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