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千年史看百年史——从中西文明路径比较看当代中国转型的意义
万古长存的山岭并不胜过转瞬即逝的玫瑰。——黑格尔:《历史哲学》
内容提要:欧洲文明是建立在小规模多元体相互竞争基础上的文明,中国古代文明是大一统的以安分敬制为基础的非竞争性文明。后者在前资本主义时代虽然可以通过规模效应来形成对前资本主义西方的优势,但这种砖墙式的帝国结构,与西方文明的类生物细胞体的多元结构相比,缺乏面对环境挑战的适应力与微观试错的变异能力,这就导致了它既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在近代也无力应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日本作为东方国家应对西方挑战的成功决非偶然,其关键在于其结构内部具有类似于西方的多元性、分散性、竞争性的特点。中国改革开放的意义就在于,在政治威权体制的推动下,激活了社会内部的微观个体、地方与企业的竞争机制,从而使小规模、多元性、自主性与流动性相结合而形成的竞争机制,在中华大地上得以形成。这一转型的意义就在于此。
在本文中,我尝试通过比较中西文明演进的路径,来分析传统中国文明存在的一些结构性的缺陷,并以此解释中国近代化为什么失败,以及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在文明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可以说,这是一个相当宏观的课题。我们将涉及文明的比较,不同文明社会的社会结构,涉及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对其后来现代化过程的制约与影响。
我在本文中对历史上的制度演变过程进行考察,受到了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的启示。新制度主义本来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学派,它也是当代经济学中的主流思潮。如果说传统的制度主义是把有形制度或成文制度作为研究对象,那么新制度主义则扩大了研究范围,它把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各种游戏规则,习俗、惯例、包括潜规则,也作为制度来予以认识,这样就大大扩展了研究范围,提高了对社会演化过程的解释力。在新制度主义看来,制度就是人们在适应环境挑战的过程中形成的、用来约束人们行为的游戏规则,新制度主义特别注意考察一种历史上的制度,是如何在适应环境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制度是通过什么路径进行演化的,新制度主义提出的试错理论以及路径依赖理论,对于我们研究人类的制度文明的演化机制的历史学者来说,在方法论上特别有启示意义。这种方法对于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活力,它已经逐渐扩展到政治学、社会学与其他学术领域。我也尝试运用这一理论方法。对中西文明中的制度演进做出自己的解释。
一 近代中国应对西方挑战失败谈起
中国近代化的失败原因,学术界存在着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我们在教科书中耳熟能详的。这种解释认为,如果没有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可以缓慢地通过自己的“资本主义萌芽”,同样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来,根据这一解释,这一“必然”过程却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而被迫地中断了,于是中国沦入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然而,这种解释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它是从外部因素来解释问题。它不能回答,日本同样是东方国家,时样受到西方的挑战,同样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压迫与文化冲击,为什么日本却能成功地经由这种挑战的压力,而发展为东方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则相反。我们必须从中国文明与日本文明作为两个应对西方挑战的文化主体这一视角,根据它们在应对西方挑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应对能力,去寻找造成这种不同历史结果的原因。不同的文化主体应对西方挑战有不同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考察非西方国家近代化的不同结果,涉及到一种新的历史研究范式,即文化范式。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前夕回忆说,在甲午战争前夕,他跑遍了整个北京城的书铺,却买不到一张世界地图。尽管此时已经离鸦片战争整整半个多世纪。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对来自西方列强的挑战,到这时仍然如此麻木,如此无动于衷?这是因为当时的科举考试不需要考生懂得世界地理的知识。因为中国知识精英完全被吸引到科举考试中去了,他们在价值观念上具有高度同质性,士绅阶层内部缺乏最起码的多元分化,难以产生知识分子士大夫个体的思想变异,以适应已经出现了的新的环境挑战。
另外还有一个同样很有说服力的例子,1866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出版了一本介绍西方的小册子,仅仅在出版后的一年的时问里,这本小册子就发行了二十五万册。而中国江南制造局自1856年开始出版介绍西方的书,在此后三十年时间里,总共加在一起,只销售了一万三千册。如果再考虑到日本人口只有同时期中国人口十二分之一,日本国土面积只有中国国土的二十七分之一。这个数字对比就更令人吃惊了。这个例子很能说明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挑战的迟钝与麻木达到了何等地步。我们还可以举出大量类似的例子。例如,根据当年清朝驻英国首使公使郭嵩涛在日记中的记载,他在国内招聘赴英国随员十几人,居然没有人应招。以上这些例子说明一点,那就是当时的整个中国的士绅知识精英阶层在思想观念上表现出了高度的保守性与同质性。在这种极度保守麻木的精神气氛下,像郭嵩焘这样少数主张改革的人,就会在广大士大夫中显得十分孤独,他们被视为千夫所指的“士林败类”。事实上,当年的洋枪队长戈登的给他母亲的信中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在信中写道:“我觉得中国是一个很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只有李鸿章一个人除外。”中国近代士大夫阶级在民族陷入如此严重的生存危机时,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封闭性与保守性,这说明了作为“士林华选”的知识精英们在思想观念与价值观上的高度同质性。由此可见,生活于不同的文化中的人们,对西方挑战的适应能力,确实有巨大的文化差异。如果用文化范式解释中国近代化的挫折与失败,以及解释日本近代化的成功,确实比前面所提到的教科书范式,更具有说服力。
要研究近代中国文化为什么不能成功应对西方挑战,从一个更深的层次上看,就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模式,缺乏一种对变化了的环境做出能动的反应的能力。当古老的中国文明不得不与另一种强大的西方文明相碰撞与冲突时,它就会陷入持续不断的被动与挫折,并最终使近代中国陷入民族生存危机的境地。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变的挫折,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为什么近代中国缺乏对外部挑战的适应能力?对这个问题的考察不能仅限于近代。这是因为,一种文明或文化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力,是在千百年集体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文明的适应能力的考察,就必须以千年史的长焦距作为基础。下面,我尝试把西欧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各自的演变路径进行比较,来分析西方的竞争性文明与中国的抗竞争性文明的区别,我们将分析,中国文化由于什么原因,从而缺乏一种内在的自发的演化机制,难以像西方社会那样产生资本主义。本文还将把日本与中国这两个东方国家应对西方挑战的文化适应性相比较,来进一步说明这些问题。最后,我们还将说明,这一对文明的演化能力的分析,对于理解当代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对于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运动具有特殊的意义。
二 欧洲文明的演化方式:小规模、多元性与竞争性
一种文明的基本特点,只有通过与其他文明进行比较才能把握。这是因为,人们总是生活在自己的文化中,对于自己的文化特点,往往由于熟视无睹而“不知庐山真面目”。西方文明的基本特点,被一个近代中国人把握住了,这个人就是中国19世纪以来最敏锐的思想家严复。严复在他早期发表的《上皇帝书》、《原强》等重要时论中,就强调了西方文化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它的多元并存的小规模性,二是这种多元性产生的竞争性格。他指出,在欧洲,“一洲之民,散为七八,争雄并长,以相磨淬,始于相忌,终于相成,各殚智虑,此日新而彼月异”。在严复看来,这些散布在欧洲大地上的独立的多元并存的国家,在竞争中求生存,而竞争又磨砺出它们的竞争能力与生命力,从而使它们的生存与发展能力在“彼此唱和”的竞争中,日新月异,最终发展到一个新的文明高度。严复还认为,在欧洲大地上,独立的共同体之间的“互相砥砺,以胜为荣,以负为辱”的竞争,从古代、中世纪,一直延续到现代而从来没有中断过。严复还指出,这种竞争性表现在西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场之间,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一名一艺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终于相成,日就月将,至于近今百年,其富强之效,有非余洲所可及者。虽日人事,抑也其使之然也。”概括地说,这种竞争性贯穿古今,广泛存在于欧洲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伸展到西欧所有地区。
严复还注意到,欧洲文明这种竞争性的文化性格的形成,与欧洲地理环境的多样性,以及地势之“支离破碎”直接有关。更具体地说,欧洲存在着山地、丘陵、平原与曲折多变的海岸区域,生活于这些不同地理环境的人们,发展出不同的生活方式,包括不同的经济生活、不同的语言、宗教,形成多元的民族。地理环境的差异性,形成生活方式与民族的差异性,他们很难融合成同一民族,他们只能在竞争中求得生存发展。
严复的这一发现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值得强调的必要。因为他实际上是从文明的结构层面来切入问题,而不仅仅是从各民族的观念文化角度来抽象地思考问题。他注意到欧洲文明的小规模性,多元并存性,以及长期竞争性这些结构性因素之间的关联。正是这种结构性因素,导致竞争性的普遍存在,使西方文明存在一种在多元竞争中形成的、内在的演化的机制与强大的文明生长能力。这种竞争性文明如何演变为生气勃勃的资本主义文明?这一点严复并没有进一步做出分析。严复在当时还不具备这样的理论与知识,对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的判断。
关于欧洲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发生机制,学者们有过很多的解释,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与社会学家都各自做出不同的理论分析,这些解释对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产生,均有其积极贡献,这里我要特别指出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因为这一研究视角特别有助于把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的演化路径的不同来进行比较,从而给够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
欧洲中世纪的国家与城市如何发展出资本主义?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了这样一种相当简洁明快的解释:欧洲地理的多样性,有利于形成独立的小国家或小共同体,有些小国家的统治者为了强化自己的竞争能力,通过无数次的尝试,逐渐形成这样一些新的办法,即采取吸引具有资本、技能与知识的人才的政策,来增强自己的生产能力与财富,他们还为了留住资本与人才,进而发展出一套能有效地稳定地保护工商业、私有产权、保护个人创新自主性的制度环境。此外,他们为了让自己领土上的生产经营者能有安全感,这些小国统治阶级也逐渐学会了接受规则的自我约束。统治者之所以这样做,主观上固然是为了增进王国的税收,而在客观上则形成有利于资本、人才相结合并产生强大的生产力的制度环境。在这样一些国家或城市共同体里,资本能够得到更好的回报,投资人又能生活得既安全又自由,这样的国家就具有了示范效应。于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家、资本与知识人就会从其他地区源源不断地流动到这样的国家与地区。于是这些地区进入良性循环,相对于其他地区而言,它们具有了经济上的、人才资源上的与制度上的区位优势。
这样的情况为什么会进一步引发整个欧洲的资本主义化?根据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的解释,这种新型的城市或国家,例如威尼斯、热亚那、佛罗伦萨、尼德兰可以源源不断地吸引越来越多的资本与人才,从而使资本、人才、技术、劳动力结合起来,造成经济的进二步繁荣与国力的强盛。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的欧洲国家不得不对此做出自己的选择:有些国家不甘落后,纷纷为了自身利益而仿效先进国家,而另外还有一些保守的国家,如西班牙、俄罗斯、奥地利,它们固步自封,继续保持原有的封闭性、专制性。于是,处于这样一些保守地区的企业家就会行使自己“用脚投票”的权利。他们纷纷离开这样的国家,到新兴社会去寻找发财机会。中世纪大批企业家与人才的“退出”的行动,是一种“用脚投票的权利”,这种权利对一个国家或城市的统治者构成了有效的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当保守地区的统治者意识到,只有留住人才、资本与企业家,才能在商战与富国强兵上不败于他国时,他们也就在左右徘徊之后,不得不为了留住资本、人才,从而纷纷仿效先进国家。建立起保证企业家利益与安全自由的制度。统治者也不得不接受法律来约束自己的机会主义行为。
于是,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欧洲中世纪后期,一种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与文化就由点到面,逐渐扩展起来。这种资本主义文化的特点是,通过法律制度来保护私有产权、个人自由,无需特许的投资,另一方面,由商业派生出来的道德与价值观也逐渐在这种制度环境中发展出来:商人们也学会了守时、诚实、礼以待人与信用。政府也学会了按法律来约束自己,不敢为所欲为,政府与公民双方都在这一互动过程中自我更新。这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新制度的国家数量不断扩大,最后达到了临界多数,整个欧洲也由量变到质变,从封建社会演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欧洲各国的封建政治体制,逐步转向君主立宪政体和选举民主政体。资本主义就这样,在欧洲由点到块,由块到面,最终连成一大片。德国学者柯武刚(wolfgang Kasper)与史漫飞(Manfred E.Streit)在其《制度主义经济学》一书中,曾相当详细地从新制度主义的经济学视角描述了西欧资本主义演变的这一过程。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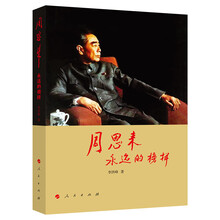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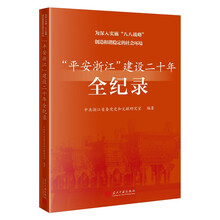
——Joseph Fewsmith,《亚洲观察》
萧功秦认为,变革过程会使旧的游戏规则瓦解,而新的游戏规则却一时无法建立,这种脱序状态,是改革的最大敌人。因此,中国需要一种新的过渡性的游戏规则,需要一种新的开放性的权威主义,这种新权威体制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中国的自由与民主,但他认为,这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
——Steven Mufson,《华盛顿邮报》
萧功秦指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倡导者们相信,只要抛弃了专权制度,中国就能实现世上最先进的代议民主政治,他认为这种乐观主义观点是“浪漫主义”的,不切现实的,相反,他更赞同梁启超与严复在二十世纪初那种似乎更为悲观低调的观点,即中国尚没有为成熟的民主做好必要的准备,因而中国现代化初期还需要“强人”权威的督导。另一方面,萧又认为,中国的这种“浪漫主义”,对于促进国民公共意识的现代化,以及对于防止“强人”滑向传统专制权威主义的泥潭,仍然有其积极的正面意义。 ——墨子刻(Thomas A.Metz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