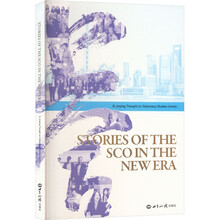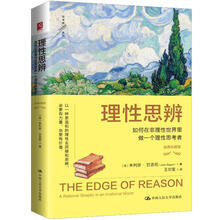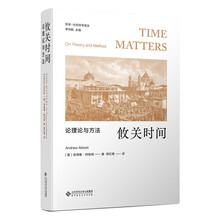第一章 法国大革命——世界
历史的大事件
分析法国大革命的重要意义或重要性,人们一直以来通常选用下列两种方法之一:1.将大革命作为法国历史上的大事件来分析它的起因和结果;2.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种对其他国家的历史产生了特殊影响的现象。但是,我希望在这篇论文中将法国大革命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也就是作为现代世界体系中的世界性的历史事件,看作世界体系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如我们所知,近三十年来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作反映了知识界两种主要思想流派的激烈斗争。争论的一方是所谓的社会解释学派,乔治·索布尔(Georges soboul)是其核心人物,其理论可以追溯到与之相关的勒费弗(Lefebvre)、马迪厄(Mathiez)、饶勒斯(Jaures)等人。这种观点的分析围绕着一个主题:法国资产阶级要推翻古代的封建制度就必须进行法国大革命。
第二个阵营是一些“修正主义者”,他们批判对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解释学派。第二阵营并没有一个公认的集体名称。支持这种观点的两位领导人物首先是阿尔弗雷德-柯班(Alfred Cobban),继他之后是弗朗索瓦·傅勒(Francois Furet)。这个阵营反对将法国大革命看作是资本主义革命,因为他们认为18世纪的法国已经不能再被称之为处于“封建制度”之下。他们更愿意将当时的法国描述为专制统治下的国家,法国大革命应该被看作是反专制的自由主义者们的一次政治爆发。
在对其间发生的具体事件进行分析时,产生的关键分歧都是对1792年8月10日的这场暴动的政治意义的思考。对索布尔来说,这场暴动是引领我们进入民主与共和的二次革命。而傅勒的观点完全相反。他认为法国革命关闭了通向自由社会的道路。毫无疑问,这确是一场二次革命,但它没有实现一次革命那样的价值,并使革命的意义发生了“侧滑”,走入歧途。因此对索布尔而言,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及山岳党代表了法国资产阶级最激进的一部分,代表了解放的力量;而对傅勒来说,罗伯斯庇尔及山岳党则代表了一种新的(更糟糕的)专制统治。
在这场辩论中,阵线划分得很鲜明,在20世纪的欧洲政坛我们也能见到他们熟悉的身影。实际上,如同我们经常所谈到的,这场辩论与关于俄国革命的讨论类似,只是它所讨论的是法国大革命。但重要的点是,我们要看到在这场充满豪言壮语、修饰措辞的论战中,两个阵营却运用了相同的假说。他们同样都使用了一种发展式的历史模型,并且认为发展的单位是国家(大西洋假说[The Atlantic thesis]也运用了这种模型)。社会解释学派认为,所有国家经历的都是连续的历史时期。而其中最要紧的转变莫过于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从一个被贵族统治的政权变成一个被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权,因此法国大革命只是一个戏剧性的或决定性的转变时刻;而这个时刻是必须,也是必然会出现的一个时刻。“自由的”学派则认为,现代化进程应该包括消灭一个专制的国家,以及在自由的原则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取而代之。法国大革命企图实现这种(并非必然的)转变,但是它并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对自由的追求一直潜伏在法国的政治体制中,未来它将会再次出现。对索布尔来说,因为这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它是法国自由民主的起点。对傅勒来说,在走入歧途以后,革命本身却成了实现自由民主的障碍。
有意思的是各方对待英国的长期战争,也就是从1792年到1815年(断续的)距离雅各宾时代已很远了。索布尔认为这场战争本质上是由境外的法国贵族挑起,因为在内战中失败的他们希望将矛盾冲突扩大到国际上,藉此夺回自己的地位。傅勒则认为这场战争恰恰是革命力量(或者至少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所渴望的,这些人希望通过战争来继续追随革命并加强革命的力量。
关于战争的直接原因的解释有很多种,毫无疑问,人们可以为每一种都找到一个看似合理的理由。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在这些分析中似乎没有考虑到如果没有出现类似法国内部革命这种事件,法一英战争在当时是否真的不会发生。毕竟在英国和法国之间连续爆发了三次主要战争,持续了一个世纪。从今天的观点看来,我们也可以把1792—1815年的战争仅仅看作是第四次主要战争,是两国为争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霸权所进行的长期斗争中的最后一次战争。
在此我想简单总结一下《现代世界体系》(1989B)中第三卷的第1、2章所详述的一个分析,为节省篇幅,此处舍去书中包含的数据。这么做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些背景资料,以便我下面进行的讨论。这个讨论是关于: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事件,法国大革命是如何从整体上转变了世界体系。我首先假设,自“漫长”的16世纪开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就作为一个历史的体系而存在。这个体系从一开始就包括了英法两国,所以这两个国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制约下一直在发挥作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系统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政治架构出现了,英法两国都是其中的成员。
这样一个“世界体系的观点”不承认关注法国革命的两个学派所持有的基本假设。法国大革命并不是一场资本主义革命。因为在法国所处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中,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的经济行为来看,他们已经是资本家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家不需要为了赢得公民权或者谋求基本的利益而在某些国家进行政治革命。当然也不排除资本家中的特殊群体可能对自己的公共政治地位的满意度或高或低,而愿意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考虑采取政治行动,并进而成为某些意义上的“暴动者”,藉此改变现存的社会阶层的组成结构。
另一方面,“世界体系的观点”同样完全不赞同修正主义学派的基本假设。这个(这些)学派认为每个政权的行为者的核心问题(这个核心问题还是指他们理论假说的中心)是专制与自由主义在政治原则上进行的,公认的宏观斗争。而且他们在推进自由主义运动中看到了一丝现代性的方向。从“世界体系的观点”来看,“自由主义”更是统治阶级运用的一种特殊策略,主要运用在世界经济体的核心领域,它也反映了一种不平衡的国内社会阶级结构——劳工阶级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比在边缘领域中所占比例要低得多。在18世纪末,不论是英国还是法国都还没有建立一种有效的自由的制度,它们在其他的时代也不可能建立这种制度。1792年革命的“侧滑”,如果有人想这么叫它的话,并不比与之相似的所谓1649年英国革命的“侧滑”拥有更伟大的历史意义。从20世纪的观点来看,“自由的”政治制度在英国和法国都流行了两个世纪,两国在这方面达到的成绩并没有显著的区别。瑞典并没有发生与英法革命可相提并论的戏剧性事件,而英法两国和它也没有太大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17世纪中叶,荷兰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霸权开始衰落以后,英国和法国成为竞争对手,都希望成为霸权的继任者。他们的竞争集中在两个主要领域:1.两国在世界经济的市场中运行的相对“效率”;2.在国与国的系统中两国相对的军事一政治力量。
在这个长期的竞争中,1763年成为“最后行动”的标志性起点。巴黎和约标志着英国在海上、在美洲大陆,以及在印度都最后战胜了法国。但是,同时它理所当然的也为未来英国(同时也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处理与其美洲移民者之间关系时面临的巨大困难埋下了伏笔,这最终引发了起源于英属北美的进而遍布全球的移民非殖民化的进程。
我们知道美国独立战争最终在18世纪80年代将法国也卷入其中,并且使它成为支持独立移民的力量,而这使法国政府的财政危机更加恶化。当然英国政府也面临巨大的财政预算的困难。但1763年的胜利使英国比法国更容易在短期内解决这些困难。“普拉西战争的战利品”减轻了英国政府欠荷兰的债务,这就是个例证。
法国政府发现在政治上不可能通过实行新的税收政策来解决财政上的问题,也无法得到和“普拉西战争的战利品”相同价值的财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自愿签订1786年的英一法贸易(艾登)条约,法国国王同意签署这份条约,是因为认为其可以帮助国家财政收入增加新的来源。实际上条约立即引发了经济上的灾难和政治上的紧张。法国第三议院的陈情书里充斥着对这份条约的抱怨。
如果你比较一下英法两国在18世纪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力的效率,你很难认为英国占有多少优势。就像在1763年,法国也不比英国先进多少。但是尽管经济状况非常相似,至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80年代英国才似乎稍有领先,在法国确实有一种(不正确的)观点那就是认为1763年以后法国开始落后了。这很可能是一个错觉,对它的解释变成了对1763年军事失败的一个理性说明。1763年以前在英国人中似乎也存在着类似的错觉,人们觉得英国比法国落后,而1763年英国战胜以后,这种错觉也消失了。无论如何这些错觉帮助了法国的受教育阶层在看待艾登条约时不那么刺眼。
当国王召集国会时,社会氛围(1763年的战败、国家的财政危机、错误地签署了艾登条约,而连续两年的农业歉收又把这些矛盾聚集在了一起)创造了一种“失控”政治空间,我们把法国大革命看作一种“失控”的状态,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15年。
1763—1789年法国最主要的思潮就是法国的精英阶层不愿意承认与英国在霸权争夺中的失败,他们认为国王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情去改变这种状况,因此更加不满。1792—1815年的战争因此成为法国大革命的根本逻辑的一部分,这一战争正是希望重建国家使它能最后战胜宿敌英国。
严格从法一英两国之间的斗争角度来看,法国革命成为了一场灾难。这场战争不仅完全没有最终弥补1763年的失败,法国在1815年所受到的军事打击远比过去的要沉重得多,因为这次失败是法国军事力量最强大的部分——陆军的失败。它也完全没有让法国追赶上与英国之间曾经存在的经济实力上的差距,实际这种差距大部分是想象出来的。相反,战争第一次使这种差距真的出现了。在1815年已经和1789年的情况不再相同了,英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商品生产的重要“效率”已经大大地超过了法国。
但是法国大革命完全没有让国内经济发生重大的转化吗?尘埃落定后,改革被发现没有人们常断言的那么惊人。较大的农业实体绝大部分依旧完好无损,尽管财产所有者的名字有了一些改变。尽管人们认为封建制度已经被消灭了,但对农业“个人主义”(用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说法)的束缚,比如vaine pature(田间,并非耕地,但牛羊可以在上面放牧)与droit de parcours(农民和奴隶不得随意走动搬迁)一直维持到19世纪末。自耕农阶级(比如labourellrs,种地的人)的力量比以前要强大,但大部分是由于最小的生产者(比如手工业者)力量削弱了。农业的改革不时会出现一些大的动作,但它却与西欧长达几个世纪的缓慢、平稳的变化发展曲线相适应。
在工业方面,行业协会确实被废除了。国内关税的取消产生了一个更为自由的国内市场。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1789年以前就已经存在了一个没有国内关税障碍的地带——五大农场——它们的范围包括了巴黎而且几乎相当于英国的国土面积。大革命当然确实废除了艾登条约,而且法国再次在很大程度上回到了保护主义。当时的法国需要新的有效管理(语言的统一,新的民法,建立一流的工程师学校与私立大学),这些无疑对法国在19世纪的经济状况非常有帮助。
但是纯粹从法国的角度来评价法国大革命的意义,讨论的范围很狭窄。如果把它看作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就不能说这种革命有多大的价值或者力量。如果把它看作是对专制制度的反抗,那么按照持这种观点的理论家的说法,法国革命并无特别突出之处。当然在托克维尔式的分析基础上我们可以赞美法国大革命是法国国家创造的成就。这种政治集权的形成正是黎塞留和科尔伯特想要实现却未能完成的。如果这样,人们就可以理解法国人为什么赞美大革命是法国国家主义的化身,但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赞美它什么呢?
但是我相信还是有一些观点值得我们注意,甚至可能值得挖掘。我相信法国大革命及其后继的拿破仑一世促进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转型为一个世界体系的意识形态并因此创造了三个全新的文化体系或者秩序。新的文化体系构成了世界体系的核心部分,时至今日依旧是如此。
我们必须从那个时代人们所觉察到的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开始。它当然是一次戏剧性的、充满激情的暴乱。从1789年(巴士底狱的毁灭)到1794年(热月政变),在此期间出现了“大恐慌”——消灭了“封建制度”、国有化了教会领地、处死了国王、发表了《人权宣言》——这都是暴乱的主要体现。这一系列事件使恐怖统治达到了顶点,最后因“热月反动”才得以结束。然而,戏剧性的事件并没有到此结束。拿破仑掌权了,法国的军队踏遍了整个欧洲大陆。最初,他们在各处被当作革命力量的使者而受到欢迎,而后却成为法国帝国主义的走狗而遭到了反抗。
在欧洲的每个地方当权者都对法国大革命病毒所带来的秩序混乱(现存的和潜在的)感到惊恐和害怕。每个地方都在努力对抗这种革命思想及其价值的传播,英国的情况最为突出。在英国那些可能同情革命思想的人所具有的力量被夸大了,从而引来了强力的镇压。
我们应该特别注意到法国大革命(包括拿破仑)对世界系统“周边”的三个关键地区——海地、爱尔兰和埃及的影响。法国大革命在圣多明戈的影响是迅速而具有催化性作用的。白人移民最初企图利用革命来提升自治的权力,结果却迅速导致了世界范围内的第一次黑人革命。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所有其他的所谓革命者(拿破仑,英国人,美国和拉丁美洲的白人移民革命者)都企图要摧毁或者至少控制住这场黑人革命。
在爱尔兰,法国大革命将新教徒过去对自治(如同在英属北美的新教徒团体所拥有的一样)的追求转化成了一种社会革命,在此天主教徒和长老会的反对者联合起来,共同进行了一场反殖民主义运动。这种努力正击中了英国的心脏,虽然这场运动最终改变了方向,并且被破坏和镇压了,而且1800年通过的《联合法案》将爱尔兰更紧密地融入了大不列颠。但这场运动给大不列颠内部所带来的政治风波在整个19世纪都挥之不去,这与黑人民权运动对美国政治的冲击极其类似,即使我们已经考虑了二者的不同。
在埃及,拿破仑的入侵导致埃及出现了第一个伟大的“现代主义者”——穆罕默德·阿里,他所推行的工业化和军事扩张严重摧毁了奥斯曼帝国,并几乎在中东建立起一个强大到最终可能在国际系统中扮演主角的国家。像本世纪所有发生在这些周边地区的革命一样,阿里的奋斗最终虽未竞全功,但依然影响深远.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