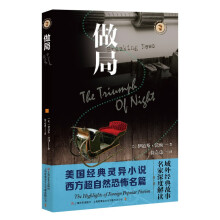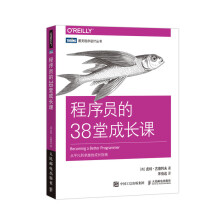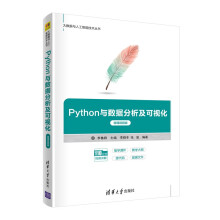第一章 占梦的起源
一 梦、梦兆与联想
梦,是科睡眠时特殊的意识现象。无人不做梦,中外古今,概莫能外。但上古时代的人类究竟怎样看待梦这一客观存在的现象,至今尚难以找到可以直接证明的材料。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上古时代人类思维特点、智力水平以及风俗习惯、神话传说等方面提供的原始信息,从中分析、推测先民关于梦的最初观念。
上古时代,人类由于不能清醒地认识客观事物之间的各种复杂联系,无力分清主体意识中客观表象与主观幻想的界限,他们的智力水平决定了他们往往把主观幻觉、幻象当作实在来感受,这一特征经过长期的衍化,构成了上古时代人类的心理定式。这一心理定式直接奠定了上古时代人类的思维特点,那就是,深信幻觉、幻象是什么样子,宇宙就是什么样子,对梦的认识也作如是观。
中国东北的赫哲族,在清代以前尚处在史前时期。在他们的宗教信仰当中,人有三种灵魂:一是生命的灵魂,二是转生的灵魂,三是思想或观念的灵魂。在赫哲人看来,生命的灵魂赋予人以生命的形式,转生的灵魂主宰着人的来世幸福与否,而思想或观念的灵魂则使人有感觉和思想。梦是第三种灵魂管辖之下的幻觉、幻象活动。这种活动受观念灵魂的指使,既可以脱离活人的身体四处游荡,也可以作为已经死去的人的阴魂再现。
据说,赫哲人常常通过梦中的幻觉来推测实际生活中的具体情形,用主客观幻化的思维方式来判断梦所兆示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如梦见喝酒、得钱,预示着打猎会满载而归;梦见死人、抬棺材,则意味着能获取野兽。赫哲人对梦幻的这种理解,一方面是基于蒙昧时期上古人的特有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是他们的生活经验和知识水平的反映。因为,拉回来猎物才能有钱有酒;反过来,喝酒、得钱之梦,只有拉回来猎物才能验证。同样,打死了野兽,必须像抬死人、抬棺材那样把它们抬同来;反过来,死人、棺材之梦,在打死了野兽之后也可视为应验。这种分不清客观事物与主观感受之间区别的思维方式和知识水准,是上古时代遗传下来的,在西方民族中也有极为相似的反映。英国的民间文艺理论家詹·乔·弗雷泽在所著《金枝》(1890)一书中载:在西方,通常将脱离人的肉体可以自由行走的灵魂视为随时可以飞去的小鸟。这一小鸟可以在梦境中代替人访问什么地方,去见什么人,做人想做的事。例如,一位巴西或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从酣睡中醒来以后,坚信他的灵魂确实出去打过猎,钓过鱼,砍过树,或做过他梦中所做的一切事情,而他的身体却始终一动未动地躺在吊床上。一次,一个博罗罗人的村庄里,所有居民全都陷入极度惊恐之中,并且凡乎逃避一空,仅因为有人梦见有敌人悄悄向他们的村庄进袭来了。一个马库西印第安人,身体不适,夜里梦见主人要他将一条独木船拉过一连好几处洪水激流的险滩。第二天早上醒来后,他竟痛骂主人不体恤他。
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上古时代遗留下来的民间风俗习惯,同样为人们提供关于梦观念的最早信息。
据《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和《云南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资料选辑》等书籍记载,居住在中国大西南的僳僳族,1949年以前虽大多已进入封建社会,但某些地区仍停留在刀耕火种的原始阶段。傈僳族的风俗习惯不但仰灵魂,而且还有梦中“杀魂”的说法。他们一向认为,有一种人名叫“扣扒”,他的灵魂是一只鹰鬼。由于鹰鬼可以在梦中“杀魂”,人对“扣扒”不仅害怕,也非常愤恨。倘若有人梦见一只鹰,同时又梦见某个人,那么,某人就是“扣扒”。如果梦者因此得病惊恐而死,那就意味着梦者被“扣扒”把魂杀了。为了证明某人是“扣扒”和追究“杀魂”的责任,巫师要举行骇人的捞油锅仪式的“神判”,“扣扒”将因为“杀魂”而受到严厉的惩罚。
又如,景颇族和瑶族的社会发展在解放前已达到较高的水平,但在一些地方,文化生活仍十分落后。他们普遍迷信上古流传下来的梦魂观念,对此可以视为上古原始观念(关于梦)的一种遗存。
景颇族一般把灵魂称作“南拉”。他们认为,人之所以做梦,就是因为灵魂离开了自己的肉体。如果灵魂不离开入的肉体,人就不会入睡做梦。有时候,人入睡却不做梦,那是因为灵魂外出没有碰见什么东西。假如灵魂外出游动碰到什么怪物,人在睡眠中就会做起怪梦来。按照景颇族的风俗习惯,梦见矛枪、长刀之类的物品,是怀孕的妻子生男孩子的兆示;梦见铁锅和支锅的三角架之类,则是怀孕的妻子生女孩子的兆示。这与弗洛伊德的梦见条、杆之类的东西和圆圈之类的器物,就意味着男女生殖器的梦说观念有些相似。同样,在景颇族看来,如果梦见黄瓜、南瓜结果结得多,而且自己又摘了一大筐背回来,那就意味着是凶兆。梦见太阳下山、牙齿脱落,以及喝酒吃肉,也是凶兆,不是家里死人,就是邻里死人。
瑶族对梦的观念也有特殊解释。梦见太阳下山,就说明父母有灾难;若梦见刮风下雨或与女子相爱,意味着自己有不幸;梦见唱歌,预示与人吵架;梦见吃肉,有病有灾;梦见吃饭,将终日辛劳;梦见解大便、蛇行或者自己把木头、石头滚下山,则都是要破财的兆示。与此相反,梦见打小蛇或房屋失火,则要进财或发财;梦见野火烧山或者梦见父母,天要下雨;梦见别人或自己死亡,那就意味着自己或被梦者有福有寿。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上述种种民间风俗习惯,也从侧面反映上古时代先民关于梦的最初处于萌芽状态的观念,他们往往把梦看作梦者(自己)和被梦者(梦中的他人)灵魂的相互交往的活动。
如何较客观地认识上古时期先民关于梦观念的最初理解?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说,梦是梦者“与精灵、灵魂、神的交往”,梦是“神为了把自己的意志通知人而最常用的方法”。明代陈士元在《梦占逸旨·真宰篇第一》中曰:“梦者,神之游知来之镜也。”意思是说,梦是神灵的游动,从中可以知晓来日的景象。对此,恩格斯根据北美原始人的材料,分析先民的梦魂观念,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了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之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恩格斯的这段话可以帮助我们这样来理解上古时代先民关于梦的释义:洪荒年代,当先民躺在洞穴里睡眠的时候,他们的躯体并没有脱身而去,为什么却在梦中常同伙伴一起去打猎呢?按照当时人的理解、想象,梦中外出打猎的那个躯体显然不是那睡在洞穴里的躯体,而是不受自身躯体约束的另一个可以游动的东西。以此推论,他们还认为,已死去的亲人,虽然他们的肉体已死,但他们那种可以游动的东西依然存在。因为在梦中,先民常常因此与他们的亲人会面、交谈。
那种无肉体、又不受躯体束缚的东西,究竟是什么?经过长期的思索,先民结合自己做梦的经验,逐渐在头脑中形成这样的观念:当人做梦的时候,在肉体当中存在着一种支配肉体而又不是肉体的东西;而且,入睡眠的时候,这种东西可以离开人的躯体四处游动,即便是人的肉体死亡后,它们仍然存在着、活动着。因此,人在梦中既可以到野外去打猎,也能够与死去的亲人相会。后来,先民给这种莫名其妙的东西起了一个名称,叫“灵魂”。但这里仍然存在一个令先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灵魂”来自何方?为此,先民必须在梦魂之外去寻找另一种原因或力量。在他们看来,自然、社会的万事万物都有“灵”,各种各样的“灵”,在冥冥中由无所不能的神来支配。至此,我们可以看出上古时代先民关于梦的观念是,他们用主客观幻化为一体的思维方式,将梦想像为神灵的兆示,反过来,又用这种神灵的观念来解释梦中的景象。由此可见,上古时代的先民是如此地将神灵、幻觉与客观存在的人和事物难解难分地融为一体。显然,限于他们的知识水平和思维特性,这其中含有浓厚的神秘色彩,为梦兆迷信活动提供了广泛的天地。
理解了上古时代先民关于梦的观念,就可以进一步认识他们梦兆迷信活动的本质和意义所在。梦魂观念是梦兆迷信的思想基础,因此,我们可以对上古时代先民的梦兆活动考察一番,然后正确地把握梦兆的意义。
上古时代,先民由于无力把握自然、社会的变幻和人生际遇的旦夕祸福,凡事在行动之先都得有一个征兆,以乞求神灵降兆示知,得以免灾获福。从《尚书·洪范》中可以看出,先民把征兆叫做“庶征”,吉祥的征兆叫做“休征”,凶灾的征兆叫做“咎征”。征兆这一迷信活动在当时非常盛行,涉及的范围极为宽广,几乎包括所有为人所知的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在众多的征兆迷信活动中,最为普遍流行的是以梦为征兆的迷信。
关于梦兆这一迷信活动,中国最古老的记录是殷墟卜辞。例如:
壬午卜,王曰贞,又梦。
丙戌卜,故贞,王出梦示。
贞王梦,不佳祖乙。
从这些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殷人较重视梦兆,殷王一有梦,就要占卜。但是殷人所重视的梦兆是什么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记载梦兆的具体情形最早的记录,可能是《诗·小雅》的《斯干》和《无羊》二首古诗。
下莞上簟,乃安斯寝,乃寝乃兴,乃占我梦。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
——《斯干》篇
在这里,梦的内容和征兆的内容都非常具体、清楚,即人们在梦中见到熊罴是生男的兆示;梦见虺蛇是生女的预兆。再如: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旒维放放*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旒维*矣,室家溱溱。
——《无羊》篇
这首诗表明,梦见众多的鱼是丰收年的前兆,梦见旗帜飘扬是家室众多繁荣的兆示。
《国语·楚语上》记有:“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于神明,……如是而又梦,使以象梦(梦象),旁求四方之贤,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即是说,殷王武丁欲求一位好的帮手,辅助他料理国家大事,在梦中上帝赐给他一位良臣,后来,他按照梦中良臣的容貌找到了傅说来做宰相,共谋国事。
又如《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盛其脑。是以惧。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这一梦兆活动与上述几例有所不同,它兆示人们,恶梦可以成为吉兆,关键是怎样理解、释义。晋王梦见与楚王相互搏击,楚王以极强的力量压在晋王的身上,并且不断吸吮着晋王的脑浆。晋王因此而惊恐不安。大臣子犯却解释说,这倒是大吉大利的兆示。因为晋王虽然在梦中被压在楚王的身体下面,但面却是朝天的,这是受命于天的表现;楚王虽然压在晋王的身体上面,恰恰是违背天意,伏身向晋王请罪的样子;楚王吸取晋王的脑浆,则兆示着晋王对楚王能以柔克刚。后来,晋军与楚军大战,晋王尚梦而战,果然大败楚王。子犯的解释是牵强的,仅从迷信的角度满足了晋王的心理需要,梦后的战事却偶合梦兆的释义,因而在当时令人深信不疑。这当然是梦兆这一神秘的精神现象善于类比、诡辩的结果。
梦兆这一迷信活动,后来越来越复杂。例如,《:左传·昭公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赵简子梦童子裸而转以歌。旦,占诸史墨,曰:‘吾梦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对曰:‘六年及此月也,吴其入郢乎!终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谪。火胜金,故弗克。”’这里面,日食之兆、梦兆、星辰运行的因素等结合在一起,如此复杂,若无专门的史墨之客,是无法圆梦得兆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五行相成相克的理论,已成为梦兆迷信的哲学基础。文中断定,吴会入侵郢,其根据就是辛亥的“亥”字,所谓亥为水,水为六,火胜金,故弗克,结论完全是依据五行相克的观点引伸出来的。
从上述诸种梦兆的实例中,我们不难看出,梦兆的形成,是上古时代先民在神灵观念作用下,对事物因果关系直观认识的迷信活动。从这些梦兆活动的内容和形式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梦兆的本质意义,在上古时代是通过圆梦的方式来满足先民的心理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上古时代的梦兆是根据惯例来类比、联想,最后得出对凶吉的判断。这与后来渗入更多的“人为”因素的占梦术有所区别。
梦兆迷信和占梦术都是基于神灵能以某种征兆,给人预示某些事物发展趋向的思想和方法,但这两者之间仍然有较明显的不同。一般来说,梦兆的兆象多为人体自然发生,具有较大的偶发性,所兆示的内容和形式受制于兆象;而占梦多是人为的,其内容和形式可以由人在主观上加以预先规定,不受时空的限制。可以这样说,梦兆是人被动接受神灵的启示,而占梦术则是人主动求助神灵给予的启示。
梦兆之转化为占梦术,一方面是由于梦兆的虚妄性质决定它要在发展进程中复杂化,以达到不断取信于人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有其必然的社会动因。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产范围的扩大,人对各种事物的发展变化需要预知的范围也相应增广,靠人体自发产生的梦兆已不能满足上述扩大了的需要。为了增强自信心,在没有相应的征兆出现的情况下,人不得不在原有的梦兆迷信中,找出一些可以人为制造的兆象内容,加以主观分析,并主动求助于神灵的保护。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占梦术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占梦理论,这样,原先在不自觉的精神状态下的梦兆迷信活动,渐渐地过渡为自觉的占梦。由上述可见,梦兆与占梦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