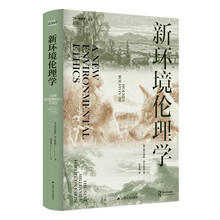以学术为业<br>应诸位的要求,我来谈谈“以学术为业”。我打算沿用咱们国民经济学家总是从外部关系人手的迂腐作法,先从这样一个问题谈起:物质意义上的职业学术是如何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这在今天来说,实际上主要指:一个决心职业性地献身于学院生活中的学术研究的大学毕业生的前途如何?为了了解咱们德国情况的特殊性,用比较方法来了解并设身处地地设想一下外国的情况,是合宜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最尖锐的对立面在美国。<br>众所周知,在咱们这里,一位有志献身于学术之业的年轻人,往往从当“编外讲师”开始他的生涯。这之前他要和有关的学科代表人物磋商并取得人家的同意,然后写出一本书来,通常还要通过系里的正式考试,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取得授课资格,然后按照自己的专长开一门课,但是不领薪水,报酬来自学生的听课费。在美国,学术生涯通常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开始,即先受聘当“助教”。类似咱们的自然科学与医学系的大型研究所的做法,助教中只有一部分可以争取到编外讲师的正式授课资格,而且这种机会常常来得很迟。这种区别实际上说明,在咱们这里,一个从事学术研究的人的生涯基本上以财富为前提。一个一贫如洗的年轻学者,要完全正视学术生涯的条件,需要超乎寻常的胆量。他至少要苦熬几年,还不知道以后是否有机会接替一个职位,使日子过得下去。与此相反,美国有科层体制,那里的年轻人一开始就有薪金。虽说工资往往比不上一个半熟练工人的收入,可是他毕竟一开始就有了一个似乎可靠的职位,因为能领到固定的薪金。不过,他也和我们的助教一样可以被解聘,这也是个通例。他必须对自己可能不符合人家的期望这一点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期望无非是:他能使课堂上“座无虚席”。一个德国编外讲师不会碰上这种事,人家一旦请了他,就不会赶他走。他虽然没有任何“要求”,但是有一种可以理解的念头:在他工作几年之后有一种道德权利,要求人家考虑他。并且——这往往很重要——在讨论其他编外讲师的授课资格问题时,也考虑到他。究竟是原则上让每一位能干的、受到承认的学者都取得授课资格,还是考虑到“教学需要”,让在职的编外讲师垄断教学,这是一件让人左右为难的事,它与学院职业的双重性有关,不久我们就要涉及这个问题。人们往往采取第二种选择。但是,这也增加了某种危险:当事的学科终身教授尽管主观上坦荡之极,仍难免偏袒自己的学生。我本人奉行的准则是:在我这里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必须在另一所大学的另一位教授那里,而不是在我这里,得到承认并取得授课资格。结果却是:我最优秀的学生中的一位没有被别人接受;因为谁也不相信,他是由于上面的理由才去投考的。<br>与美国的另一个区别是:在咱们这里,编外讲师所开的课通常比他希望的少。虽然他有权选择本学科范围内的任何一门课,但这样做不合适,因为没有考虑年长的在职编外讲师。通常,“大”课都由学科代表人物来讲,讲师要是能开次要课程,就很知足了。好处是:他年轻时有充分的时间进行研究工作,虽然有些不自愿。<br>美国的制度有原则的差异。只因为讲师挣薪水,所以在他年轻时代工作绝对超负荷。例如在德国语言文学系里,正教授只要讲一次三小时的歌德课就够了,而一个年轻助教一周要讲12课时,除去德语听读练习,如果他能讲到乌兰德一级的诗人,就很知足了。业务主管部门制订教学计划,助教也像咱们这里的研究所助教一样受制于主管部门。<br>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广大的科研领域中,咱们的大学也朝着美国的方向发展。医学与自然科学的大型研究所都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没有庞大的经费,它们就不能维持下去。这里也和所有进行资本主义经营的地方一样,出现了“工人与生产资料分离”的状况。工人,也就是助教,完全依赖国家交给他使用的工作手段;因此,他也像工厂里的职员一样依附所长——因为所长满心以为,这个所是“他的”所,并且自己去管理——他的境况十分艰难,很像“无产阶级”的一员,酷似美国大学里的助教。<br>咱们德国的大学生活在很重要的方面完全美国化了。我确信,这种发展将波及那些“手工业者”占有工作手段本身(例如图书馆)的学科。在这些学科中,人们酷似过去行会内部的手工业者那样工作,我这一行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这种发展正在全速进行。<br>像在一切资本主义的科层化企业中一样,这种发展的技术优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科层化企业中笼罩的精神却不同于德国大学的传统气氛。在这样一种大型的资本主义大学企业的领导者与平常的旧式教授之间,无论在外表上还是内心里,都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也表现在心态方面,不过,我不想过多地解释。旧的大学宪章,无论从实质上看还是从外表上看,都已成为泡影。然而,大学生涯的一种特点保存了下来,并且有重要的发展:一个这样的编外讲师,尤其是一个助教,有朝一日是否能当上终身教授,甚至所长,纯粹是撞大运。当然,偶然事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是它一般在很大程度上起着决定作用。我几乎不知道世上还有哪_种生涯,能让偶然事件扮演这样的角色。我能够说这种话,何况我本人的,升迁也仰仗几个绝对的偶然事件,我很年轻时就当上了一门学科的正教授,而当时一些同龄人对这一行的贡献无疑比我要大得多。我自然以为,由于这种经验,我能敏锐地看到许多人的不平命运。在这些人身上,偶然性起了相反的作用,并且现在还在起作用。他们尽管才华横溢,但是,在这、种筛选机构内却不能取得应有的地位。<br>撞大运,而非真才实学,之所以能起如此重要的作用,并不完全在于人性,也不主要在于人性。当然,在这种筛选过程中,也同在其他筛选过程中一样,有人性这个因素。如果将这么多平庸之辈在大学里扮演重要的角色这样一个事实归咎于系或各部的个人水平低,那是不公正的。原因在于人事协调制度,尤其是几个单位之间的调配制度,在这里则指负责推荐人才的系与各部之间的协商原则。这里有一种相似的情形,所幸我们可以追溯一下几个世纪以来的教皇选举史:这是同类人事选拔中最重要的可以监督的例子。呼声最高的红衣主教最后能当选的十分罕见,通常倒是排在第二位或第三位的候选人被推举上来。美国总统的选举也是这样:只有破例,最佳人选,也就是最坚定的人,才能获得党代会提名,多数情况下都是排在第二位,往往第三位的进入候选人提名,然后参加竞选。美国人早就为这个范畴发明了一套社会学的术语,以这些为例来考察通过形成集体意志来进行选拔的法则,将会妙趣横生。不过我们今天不在这里进行这种考察。这些法则也被视为德国大学的章程。人们吃惊的倒不是常常挑错人,而是通常看来正确的人选尽管有种种困难,仍然占有相当的比重。只有当议会(如在某些国家)或君主(如咱们这里迄今为止)——两者的作用完全相同——或目前的革命掌权者出于政治原因插手时,才能肯定,只有得过且过的平庸之辈和野心勃勃的人才有上去的机会。<br>没有哪一位大学教师喜欢回味任命讨论,因为这种事很少让人感到好受。不过,我要说:在我所知道的大量事例中,无一例外都有让纯客观的理由来作决定这种良好的用心。<br>还必须进一步弄明白,学术命运的决定如此广泛地靠“撞大运”,还并不仅仅由于靠形成集体意志来选拨人才之不足,每一位有志于成为学者的年轻人都必须明白:等待他的任务具有双重性。他不仅要当个够格的学者,同时也要具备做老师的资格。这两者并不完全吻合。一个人可能是一位杰出的学者,同时却是一个蹩脚的老师。我想起了赫尔姆霍茨和兰克这些人上课时的情形,这绝非罕见的例外。现在的情况却是,我们的大学,尤其是那些规模很小的大学,处于一种十分可笑的招生竞争中。大学城的房东们,在学生人数突破1000大关时,要像过节一样庆祝一番,超过2000时,还要办一次火炬游行。学费收入——应该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受到邻近学科“吸引”学生的影响。除此之外,听课的人数成了一项可以用数字表示的鉴定标志,而学者素质却是无法称量的,碰到勇敢的创新者,更是大有争议(这也是很自然的)。因此,听课人数多,成了_种无法估量的幸事与价值,往往一切都处于这种巨大的诱惑之下。说一个编外讲师是个糟糕的老师,这对于他来说往往是学术上的死刑判决,尽管他可能是世界上的一流学者。他是好老师还是坏老师,这个问题要由学生先生们用来向他表示敬意的听讲人次来回答。但事实上,学生们之所以涌向某位老师,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例如秉性,甚至声音的抑扬顿挫,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常人难以想象。根据我个人算得上相当丰富的经验,加上冷静的思考,我对那些大众教师深表怀疑,不管他们如何必不可少。民主,存在于适合它的地方。科学训练,例如我们按照德国大学的传统推行的科学训练,是精神贵族的事,这一点,我们无需掩饰。但是,另一方面,对科学问题进行阐释,使没有受过训练、但是有接受能力的头脑理解它,并使他——这对我们恰恰是至关重要的——能够独立思考,大概是教育学里最艰巨的任务,这也是事实。毫无疑问,这项任务是否完成了,并不能由听课人数来决定。再回来谈本题,这种艺术是一种个人天赋,与一个学者的科学素质完全是两码事。与法国相反,咱们没有一批科学上的“不死之士”,按照德国的传统,咱们的大学应当兼顾科研与教学两种要求。一个人是否兼有这两种本事,纯粹靠机遇。<br>学术生涯是一场疯狂的赌博。要是年轻学者为了取得进大学授课的资格来取经,我几乎负不起劝进之责。如果他是犹太人,人家当然可以告诉他:Lasciate ogni speranza。但是,对任何别的人,都必须问一问良心:您当真相信,您能忍受年复一年地让一批又一批的平庸之辈迈过您去,而既不抑郁,也不沉沦吗?答案自然每次都是:当然没问题!我只为我的“天职”而活——不过,我只看到极少数人能够忍受这些,而不受精神上的损失。<br>看来,关于学者职业的外部条件,说这些就够了。<br>不过,我想,诸位实际上希望我谈一些别的东西,希望听一听内在的学术使命是什么。今天,决定作为使命的学术内在状态的是:科学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闻的专业化阶段,并且未来也将是这样。事情不仅在外表上,而且恰恰实际上是:只有在严格的专业化条件下,一个人才能有可靠的意识,在科学领域中做出某种真正完美的贡献。一切与邻近学科交叉的研究工作,例如我们偶尔要做的工作,又如社会学家们必须经常进行的工作,都有一种听天由命的压力:充其量只能给专家提供他从本学科的角度不容易发现的有用的问题,本职工作却难免极不完美。只有通过严格的专业化,科学工作者有朝一日才能满怀自信地说:“在这里,我做出了传世的贡献。”这种清醒的意识,人一生或许只有一次。在今天,一项真正已成定局的优异成就只能是专门的成就。谁要是没有本事,打个比方,带上眼罩,死心塌地地认定:他的灵魂的命运就系于,他是否能把这篇手稿的这个地方揣摩透,那他还是离科学远点好。他永远也不会体验常说的科学“经历”。不用这种被局外人嘲笑的奇特的如醉如痴,这种热情,这种“你来之前悠悠千载已逝,在你身后千载悠悠默待”的气魄——去揣摩,就受不到科学召唤,那就去干别的事吧!因为,如果一个人不能用热情去做一件事,这件事对于作为一个人的他来说就毫无价值。<br>然而,纵有如此之多的热情,不管它是多么真挚,多么深切,还是远远不能保证一定会取得成果。这也是事实。当然,热情是决心,亦即“灵感”的前提。今天,年轻人中问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科学已经变成了计算检验,可以在实验室或者统计档案里制造出来,就像在工厂里一样,只需要冷静的理解力,用不着全部“心灵”。首先要指出,这种论调对于工厂里和实验室里的情况一无所知。不管在哪里,人都必须思考出什么,而且是正确的,才能创造出有价值的东西。这种“思考”,却是强迫不得的。它和任何冷冰冰的计算无关。当然,计算也是必不可少的前提。举例说,任何社会学家,即使年事已高,也不会不屑于在脑袋里成千上万次地作琐碎的计算检验,有时,也许要算上几个月呢!要想获得点什么,绝对不能放心大胆地全推给机械性辅助力量,否则要受惩罚——最后得到的,只能微乎其微。然而,如果对于计算的方向,对于计算过程中产生的单项结果的影响,没有一定的“想法”,那么,就连这“微乎其微”也不可得。在正常的情况下,只有坚毅的劳动才能孕育出“想法”,或者叫“灵感”。当然,也并不总是这样。业余爱好者的想法有时也能产生与专家的想法一样的甚至更大的影响。我们有许多一流的假说和见解,它们恰恰应当归功于业余爱好者。正如赫尔姆霍茨在谈到罗伯特?迈尔时所说的,业余爱好者与专家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的研究方法缺乏可靠性,因而往往不能从事后产生的影响来复查他的想法,做出评价,加以贯彻。灵感不能代替工作,工作本身也不能代替灵感,或者迫使灵感冒出来;热情也无济于事。两者都能激发灵感,可重要的是,必须结合起来。但是,灵感这东西,只有在它自己愿意来的时候才来,而不是我们想叫它什么时候来它就来。最精彩的念头,用伊埃灵(Ihering)的话说,是坐在沙发上抽雪茄的时候迸发出来的,依照赫尔姆霍茨的自然科学的精确勾画,是顺着街道的缓坡散步时,或在类似的情形中,突然想出来的,反正总是在没有期待它的时候降临的,而不是在一个人坐在书桌前苦思冥想、搜索枯肠的时候出现的。<br>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