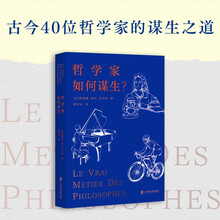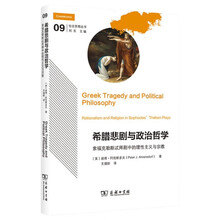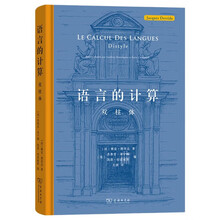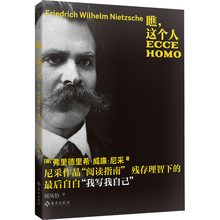无疑地,哲学是附属于神学之下,但是,就其为哲学而言,哲学除了自己固有的方法以外,并无其他凭借,哲学既然奠基于人类理性,其全部的真实性都有赖于原理的自明和演绎的精确,以获致与信仰之间的自然和谐,而无须歧离自己固有的途径。哲学如果这样做,也是为了真理,而真理不会彼此矛盾。
这样的新士林派与纯理性派当然仍有一个基本上的差异。对于前者,信仰永在,而他的哲学若与信仰冲突,那一定是表示哲学错误的记号;若有这种冲突出现,他便必须重新检讨原则,核验结论,直到发现败坏这些原则的错误为止。如果这时候他仍然无法与理性主义者达到共同的了解,那并非由于缺乏共同语言。他绝不会触犯圣奥古斯定或圣安瑟莫所不会原谅的错误,而会在人家问及天主存在的证明时,先要人相信天主。假如他的哲学是真的,那只是由于它合理的显明性,假如他无法劝服其对手,那只是由于他没有率直地诉诸信仰作为证明,这并不只因为对手不分享他的信仰,而是因为他的哲学的真理丝毫没有依靠他的信仰的真理。
一旦我们从这个观点来看圣多玛斯的哲学,就会出现一些多少令人惊讶,但同样无可避免的结果。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奥古斯定派学者在每一个时代中都激烈抗议多玛斯思想把基督教义外教化。假如某些现代多玛斯派学者否认奥古斯定思想是一种哲学,中古的奥古斯定派学者早在他们之前,便否认多玛斯思想忠实于天主教传统。无论何时,若他们认为多玛斯派某一个论题有问题,要加以驳斥,他们便会用抨击学说精神这一类较一般性的驳词,来支持其纯粹论理上的攻击。如果多玛斯派在光照的问题(theproblemofillumination)、理性种子(rationesseminales)或是世界的永恒性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岂不正是因为多玛斯派首先在基本上对于理性和信仰的关系就弄错了吗?因为圣奥古斯定本人曾宣布接受信仰的指导,如果我们拒绝跟随他,而宁愿跟随某位外教哲学家或是他的阿拉伯注释家们,那么理性就再也不能分辨真伪了;理性既然被强迫依靠本身的光明,那就很容易被实际错误的学说所蒙蔽,而不见其错误。
但是,随之而来的更是奇怪。就像有些奥古斯定派学者认为多玛斯主义错误,因为它并非一种天主教哲学;同样有些多玛斯派学者会回答说:奥古斯定思想确然不错,但根本不是哲学,因为它纯属天主教。事实上,他们不得不采取这种立场;因为,一旦理性的运作脱离了信仰,一切天主教义和哲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就变成矛盾了。假如一种哲学是真实的,那是因为它合理;但如果哲学合理,根本不是因为天主教而合理。因此,我们必须做一抉择。绝不会有一位多玛斯派学者承认多玛斯的学说之中有任何东西相反理性或相反信仰的精神,因为多玛斯明白主张:启示与理性的谐和正是真理与真理本身的谐和。但是,假如他们中有些人毫无畏缩地接受奥古斯定派的指责:“你们的哲学丝毫没有任何天主教的内在特征!”这点丝毫不足为奇。它怎么可能会具有这样的特征,同时又不会不再是一种哲学呢?圣多玛斯的哲学原则正是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原则,也就是说,一个对于启示(无论天主教或犹太教的启示)毫无所知的哲学原则。假如多玛斯主义采用了亚里斯多德的学说,同时又把它净化,完整化,并且使它精确,那并非诉诸信仰,而只是把已经隐含在亚里斯多德的前提中的结论,作出比亚里斯多德所能做到的更正确、更完整的演绎而已。简言之,多玛斯哲学,从哲学思辨的观点看来,只是合理地修正、补充了亚里斯多德哲学而已,别无其他。多玛斯无须为了使亚里斯多德哲学成为真理而予以洗礼,正如同他无须为了与亚里斯多德谈哲学而予以洗礼一般。哲学的讨论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的,而不是在人与天主教徒之间进行的。
这种态度的逻辑后果,正是干脆否定了整个“天主教哲学”的观念;而且,似乎很奇怪,就有些人会这样做。不单有些历史学家否认天主教义对于哲学思辨的进展有重要的影响,甚至有些新士林学者主张“天主教哲学”这类概念显然没有意义。我们诚然可以运用哲学来促进宗教信理的可接受性,但这样做就是把哲学纳入护教学中了;或者,我们也可以接受合理的结论,但应按照它们是否合乎信理来予以判断,这样我们立刻就掉进神学里面;或者,为了克服某些困难,我们决意表明“天主教哲学”只意指“真正的哲学”,那样,我们就再也没有理由说:此一哲学必须由天主教徒,而不由非教徒或反天主教徒来发现、来宣讲。或者,最后,我们称某一种哲学为“天主教哲学”只因为它可与天主教义合得来,那么,假如此时的相合性只是一种事实,不因为别的,只因它是从纯粹理性根据第一原理而推展而得,那么,这种哲学与天主教的关系仍然和前面的例子一般,都是外在的。而且,假如在另一方面,此种相合性只是削足适履的结果,那么我们又再度回到神学或护教学中去了。这样我们等于是在绕圈子,似乎是在企图用明显的语词来定义一个矛盾的概念:“一个哲学,也就是一种理性的科学,但它同时又是宗教,无论在本质上或实践上,都有赖于非理性的条件。”为什么不把这种谁都不满意的概念放弃呢?奥古斯定派愿意接受“天主教哲学”,条件是这种哲学等于抛弃哲学,唯存天主教;而新的多玛斯派也愿意接受“天主教哲学”,条件是这个哲学愿意放弃以天主教义为依据,而只作为一种哲学。这样,只要把这两个观念完全分开,把哲学交给理性,把天主教义还给宗教,岂不更为单纯?
迄今,无论事实的观察或观念的分析都十分相符,要不是我们及时想起来把观念与事实连系在一起的复杂线索,否则任何进一步的探问似乎都属徒劳无益。历史就其纯为事实的搜罗而言,丝毫不能决定任何法理的问题,后者是由观念来仲裁,这点所言非虚。但是观念是由事实推论而出,事实则是借概念来判断,这点亦同样真实。事实上,关于“天主教哲学”的定义,我们曾经有大量的演绎推论,但较少归纳推论——尤其我们可以加上“在天主教界,更少归纳”——以上这也是一个事实。到底哲学思想和天主教信仰曾经如何理解彼此的相互关系呢?双方曾经意识到从对方所接受和自己所给予的是什么呢?这些都是大问题,也不缺乏决定性的答案。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