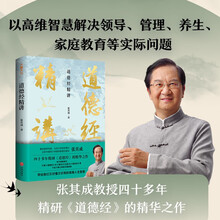论为人与为学
陈聚英初见师,请示看何书。师语之日:且勿遽说看何书。汝欲堂堂巍巍作一个人,须早自定终身趋向,将为事业家乎?将为学问家乎?如为学问家,则将专治科学乎?抑将专治哲学或文学等乎?如为事业家,则将为政治家乎?或为农工等实业家乎?此类趋向决定,然后萃全力以赴吾所欲达之的,决不中道而废。又趋向既定,则求学亦自有专精。如趋向实业,则所学者,即某种实业之专门知识也。趋向政治,则所学者,即政治之专门知识也。大凡事业家者所学必其所用,所用即其所学,此不可不审也。如趋向哲学,则终身在学问思索中,不顾所学之切于实用与否,荒山敝榻,终岁孜孜。人或见为无用,而不知其精力之绵延于无极,其思想之探赜索远,致广大,尽精微,灼然洞然于万物之理,吾生之真,而体之践之,充实以不疑者,真大宇之明星也。故宁静致远者,哲学家之事也。虽然,凡人之趋向,必顺其天才发展。大鹏翔乎九万里,斥莺抢于榆枋间,各适其性,各当其分,不齐而齐矣。榆枋之间,其近不必羡乎远也,九万里,其远不必骄于近也。天付之羽翼而莫之飞,斯乃不尽其性,不如分,此之谓弃物。吾向者欲以此意为诸生言之,又惧失言而遂止也。汝来请益,吾故不惮烦而言之。然吾所可与汝言者止此矣。汝能听与否,吾则以汝此后作何工夫而卜之也。若犹是昏昏懂懂,漫无定向,徘徊复徘徊,蹉跎复蹉跎,岁月不居,汝其虚度此生矣。
先生曰: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
事不可意,人不可意,只有当下除遣。若稍令留滞,便藏怒蓄怨,而成为嗔痴习气,即为后念种下恶根,永不可拔。人只是自己对于自己作造化主。可不惧哉?可不惧哉!
偶见师于案头书纸云,说话到不自已时,须猛省而立收敛住。纵是于人有益之话,但说到多时,则人必不能领受,而自己耗气已甚。又恐养成好说话之习惯,将不必说不应说不可说之话,一切纵谈无忌,虽日直率,终非涵养天和之道。而以此取轻取侮取忌取厌取疑于人,犹其末也。吾中此弊甚深,悔而不改,何力量薄弱一至是哉!
漱师阅同学日记,见有记时人行为不堪者,则批云含蓄为是。先生日:“梁先生宅心固厚。然吾侪于人不堪之行为,虽宜存矜怜之意,但为之太含蓄,似不必也。吾生平不喜小说,六年赴沪,舟中无聊,友人以《儒林外史》进,吾读之汗下。觉彼书之穷神尽态,如将一切人及我身之千丑百怪,一一绘出,令我藏身无地矣。准此,何须含蓄,正唯恐不能抉发痛快耳。太史公日:不读《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亦以《春秋》于谗贼之事,无所不言,言无不尽,足资借鉴也。吾恶恶如《春秋》,不能为行为不堪者含蓄。……”
一友读李恕谷书,师过之。某因问先生对恕谷有无批评。先生日,吾看船山、亭林诸先生书,总觉其悖大笃实,与天地相似,无可非议。他有时自承其短,而吾并不觉他之短。看李恕谷书,令我大起不快之感。说他坏,不好说得。说他不坏,亦不好说得。其人驰骛声气,自以为念念在宏学,不得不如此。然船山正为欲宏学而与世绝缘。百余年后,船山精神毕竟流注人间,而恕谷之所以传,乃附其师习斋以行耳。若其书,则不见得有可传处。然则恕谷以广声气为宏学者,毋亦计之左欤?那般虏廷官僚、胡尘名士结纳虽多,恶足宏此学。以恕谷之聪明,若如船山绝迹人间,其所造当未可量。其遗留于后人者,当甚深远。恕谷忍不住寂寞,往来京邑,扬誉公卿名流间,自荒所业。外托于宏学,其中实伏有驰骛声气之邪欲而不自觉。日记虽作许多恳切修省语,只是在枝节处留神,其大本未清,慧眼人不难于其全书中照察之也。恕谷只是太小,所以不能如船山之孤往。吾于其书,觉其一呻一吟、一言一语,无不感觉他小。习斋先生便有悖大笃实气象,差可比肩衡阳、昆山。凡有志根本学术者,当有孤往精神。
师语云颂天曰:学者最忌悬空妄想,故必在周围接触之事物上用其耳目心思之力。然复须知,宇宙无穷,恃一己五官之用,则其所经验者已有限。至妄想所之,又恒离实际经验而不觉。船山先生诗有云:如鸟画虚空,漫尔惊文章。此足为空想之戒。故吾侪必多读古今书籍,以补一已经验之不及。而又必将书籍所发明者,反之自家经验,而辨其当否。若不尔者,又将为其所欺。
颂天可谓载道之器,惜其把知识看轻了。他也自责不立志,却没理会志非徒立,必见诸事。少年就学时,则穷理致知是一件大事。此却靠读书补助。于此得着门径,则志气日以发舒。否则空怀立志,无知能以充之,毕竟是一个虚馁的汉子。吾观汝侪平日喜谈修养话头,而思想方面全未受训练,全未得方法,并于无形中有不重视之意。此吾所深忧也。观颂天昨日所书,仍是空说不立志,而于自己知识太欠缺,毫不感觉。充汝辈之量,只是做个从前那般道学家,一面规行矩步,一面关于人生道理也能说几句恳切语、颖悟语。谈及世道人心,亦似恻隐满怀。实则自己空疏迂陋,毫无一技之长。尤可惜者,没有一点活气。从前道学之末流只是如此。吾不愿汝侪效之也。
先生诫某君日:吾一向少与汝说直说,今日宜披露之。汝只是无真志,有真志者不浮慕,脚踏实地,任而直前。反是,则昏乱人也,庸愚人也。汝于自家身心,一任其虚浮散乱,而不肯作鞭辟近里工夫。颂天知为己之学,而汝漠然不求也。尝见汝开口便称罗素哲学,实则,汝于数学、物理等知识,毫无基础,而浮慕罗素,亦复何为?汝真欲治罗素哲学,则须在学校切实用功。基本略具,始冀专精。尔时近于数理哲学,则慕罗素可也。或觅得比罗素更可慕者亦可也。尔时不近于数理哲学,则治他派哲学或某种科学亦可也。此时浮慕罗素何为耶?汝何所深知于罗素而慕之耶?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至其所笃信,则必其所真知者矣。不知而信之,惊于其声誉,震于其权威,炫于社会上千百无知之徒之展转传说,遂从而醉心焉。此愚贱污鄙之尤。少年志学,宁当尔哉!天下唯浮慕之人,最无力量,决不肯求真知。吾不愿汝为此也。汝好名好胜,贪高骛远,不务按部就班着工夫。一日不再晨,一生不再少。行将以浮慕而毕其浮生,可哀也哉!
先生一日立于河梁,语同学云:吾侪生于今日,所有之感触,诚有较古人为甚者。古之所谓国家兴亡,实不过个人争夺之事耳。今则已有人民垂毙之忧,可胜痛乎!又吾人之生也,必有感触,而后可以为人。感触大者则为大人,感触小者则为小人,绝无感触者则一禽兽而已。旷观千古,感触最大者,其唯释迦乎!以其悲愿,摄尽未来际无量众生而不合,感则无涯矣。孔子亦犹是也。“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何其言之沉切也!“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程子谓其量与天地相似,是知孔子者也。
为学,苦事也,亦乐事也。唯真志于学者,乃能忘其苦而知其乐。盖欲有造于学也,则凡世间一切之富贵荣誉皆不能顾。甘贫贱,忍澹泊,是非至苦之事欤。虽然,所谓功名富贵者,世人以之为乐也。世人之乐,志学者不以为乐也。不以为乐,则其不得之也,固不以之为苦矣。且世人之所谓乐,则心有所逐而生者也。既有所逐,则苦必随之。乐利者逐于利,则疲精敝神于营谋之中,而患得患失之心生。虽得利,而无片刻之安矣。乐名者逐于名,则徘徊周旋于人心风会迎合之中,而毁誉之情俱。虽得名,亦无自得之意矣。又且所逐之物,必不能久。不能久,则失之而苦益甚。故世人所谓乐,恒与苦对。斯岂有志者愿图之乎?唯夫有志者不贪世人之乐,故亦不有世人之苦。孜孜于所学,而不顾其他。迨夫学而有得,则悠然油然,尝有包络天地之概。斯宾塞氏所谓自揣而重,正学人之大乐也。既非有所逐,则此乐乃为真乐,而毫无苦之相随。是岂无志者所可语者乎?
人生在社会上呼吸于贪染、残酷、愚痴、污秽、卑屑、悠忽、杂乱种种坏习气中,他的生命,纯为这些坏习气所缠绕、所盖覆。人若稍软弱一点,不能发展自家底生命,这些坏习气便把他底生命侵蚀了。浸假而这些坏习气简直成了他底生命,做他底主人翁。其人纵形偶存,而神已久死。
凡人当自家生命被侵蚀之候,总有一个创痕。利根人特别感觉得。一经感觉,自然奋起而与侵蚀我之巨贼相困斗,必奏廓清摧陷之功。若是钝根人,他便麻木,虽有创痕而感觉不分明,只有宛转就死于敌人之前而已。
为学最忌有贱心与轻心。此而不除,不足为学。举古今知名之士而崇拜之,不知其价值何如也,人崇而己亦崇之耳。‘此贱心也。轻心者,己实无所知,而好以一己之意见衡量古今人短长。譬之阅一书,本不足以窥其蕴,而妄日吾既了之矣。此轻心也。贱心则盲其目,轻心且盲其心。有此二者,欲其有成于学也,不可得矣。
先生尝自言,当其为学未有得力时,亦会盲目倾仰许多小大名流言已而微笑。予因问日:“先生对昔日所盲目倾仰者,今得毋贱之恶之耶?”先生日,只合怜他,贱恶都不是。
世俗所谓智者,大抵涉猎书册,得些肤泛知识,历练世途,学了许多机巧。此辈原来无真底蕴,无真知见。遇事只合计较一己利害。其神既困于猥琐之地,则不能通天下之故,类万物之情,只是无识之徒。凡人胆从识生。今既无识,便无胆,如何做得大事?
赖典丽云,尝闻诸先生日:吾人做学问,是变化的,创造的,不是拉杂的,堆积的。此如吾人食物,非是拉杂堆积一些物质而已。食后必消化之,成为精液,而自创新生机焉。若拉杂堆积之物,则是粪渣而已。学问亦然。若不能变化创新,则其所谓学问,亦不过粪渣的学问而已。
〔与赖生〕子笃实人也。忠信可以习礼,笃实可以为学。尽力所至,莫问收获,只问耕耘。著书是不得已。如蚕吐丝,如蜂酿蜜,非有所为而为之也。陈白沙诗云:“莫笑老佣无著述,真儒不是郑康成。”得此见地,方许通过要津。
论读书
之一
凡读书者,须有主观方面之采获,有客观方面之探求。先言主观。读者胸中预有规模,有计划,则任读何书,随在有足供吾之触类而融通者。若无规模,无计划,而茫然读古人书。读一书,即死守一书之文义。读两书,即死守两书之文义。是谓书蠹,何关学问?次论客观。某一学派之大著,必自有其独到之精神,必自有其独立之系统。读者既有主观之采获,遂谓得彼之真,窥彼之全也,于是,必以主蔽客也。故必摒除一已所触类融通者,而对彼之宏纲众目,为纯客观之探求,方见吾与彼之异,及吾与彼,并其他诸家之异。益徵理道无穷,宇宙无量,而免入混乱或管窥之诮矣。吾任读何书,只是如此。
之二
吾尝言,今日治哲学者,于中国、印度、西洋三方面,必不可偏废,《十力语要》卷一,《答薛生书》已言及此。此意容当别论。佛于内心之照察,与人生之体验,宇宙之解析,真理之证会,此云真理,即谓实体。皆有其特殊独到处。即其注重逻辑之精神,于中土所偏,尤堪匡救。中国学问,何故不尚逻辑?《语要》卷一,时有所明。但言简意赅,恐读者忽而不察。自大法东来,什、肇、奘、基,既尽吸收之能,后详。华、台宗门,皆成创造之业。华严、天台、禅家,各立宗派,虽义本大乘,而实皆中土创造。魏、晋融佛于三玄,虽失则纵,非佛之过,曹魏流荡之余毒也。光武惩新莽之变,以名教束士人。其后,士相党附而饰节义,固已外强中干。曹氏父子怀篡夺之志,务反名教。操求不仁不孝而有术略者,丕、植兄弟以文学宏奖风流,士薄防检,而中无实质,以空文相煽,而中夏始为胡。又自此而有所谓名士一流,其风迄今未已,华宵之不竞,有以也哉!宋、明融佛于四子,虽失则迂,非佛之过,东汉名教之流弊也。宋承五代之错乱,故孙、石、程、张、司马、文、范诸公,复兴东汉名教,南渡诸儒继之,明儒尚守其风。若陆子静兄弟,及邓牧、王船山、黄黎洲诸儒,皆有民治思想,则其说亦不足行于世。揆之往事,中人融会印度佛家思想,常因缘会多违,而未善其用。今自西洋文化东来,而我科学未兴,物质未启,顾乃猖狂从欲,自取覆亡。使吾果怀自存,而且为全人类幸福计者,则导欲从理,而情莫不畅,人皆发展其占有冲动,终古黑暗,而无合理的生活,如何勿悲!本心宰物,而用无不利,现代人之生活,只努力物质的追求,而忽略自心之修养,贪嗔痴发展,占有冲动发展,心为物役,而成人相食之局。直不知有自心,不曾于自心作过照察的工夫。异生皆适于性海,异生,犹言众生,性者,万物之一源,故喻如海,见《华严》。人皆见性,即皆相得于一体,而各泯为己之私,世乃大同。人类各足于分愿,大同之世,人人以善道相与,而无相攘夺,故分愿各足也。其必有待中、印、西洋三方思想之调和,而为未来世界新文化植其根,然则佛学顾可废而不讲欤?此意,容当别为专论。
印度佛学,亡绝已久,今欲求佛学之真,必于中国。东土多大乘根器,佛有悬记,征验不爽。奈何今之人,一切自鄙夷其所固有,辄疑中土佛书,犹不足据。不知吾国佛书,虽浩如烟海,但从大体言之,仍以性相两宗典籍为主要,其数量亦最多。性宗典籍,则由什师主译;相宗典籍,则由奘师主译。奘师留印年久,又值佛法正盛,而乃博访师资,遍治群学,精通三藏,印度人尊之为大乘天,史实具在,岂堪诬蔑。不信奘师,而将谁信?奘师译书,选择甚精,不唯大乘也,小宗谈有者,其巨典已备译,即胜论之《十句论》亦译出。唯小空传译较少,然小空最胜者,莫如《成实论》,什师已译,故奘师于此方面可省也。什师产于天竺,博学多通,深穷大乘,神智幽远,靡得而称。弘化东来,于皇汉语文,无不精谙深造。本传云:“自大法东来,始汉历晋,经论渐多。而支、竺所出,多滞文格义。什既至止,姚兴请译众经。什既率多谙诵,无不究尽,转能汉言,音译流便。既览旧经,义多纰缪,皆由先译失旨,不与梵本相应。姚兴使僧肇等八百余人,谘受什旨,凡所出经论,三百余卷。临终,自云:‘今于众前,发诚实誓,若所传无谬者,当使焚身之后,舌不焦烂。’及焚尸已,薪灭形碎,唯舌不灰。”详此所云,什师既能汉语,又于译事,备极忠实,观其临终之词,可谓信誓旦旦。又《远法师传》,称什师见所著《法性论》叹曰:“边国人未有经,什以印度为中,故称中夏为边。便暗与理合,岂不妙哉。”又《肇法师传》云,著《般若无知论》,什览之曰:“吾解不谢子,文当相揖耳!”夫远、肇二师之文,古今能读者无几,而什师能欣赏焉,其于汉文深造可知。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