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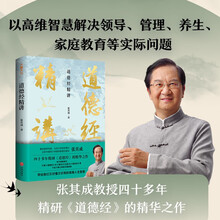




第一章 心性内涵
性善之说与生之谓性
所谓“性”,专就天地万物的个体说,而不就其整体说。任一个体,都有其存在的特质,因而能表现各种样貌;个体存在的特质,或是其“存有”,便以“性”称之。广泛地说,物类莫不有其性,生物有之,无生物也有之。就哲学上对“性”的探索言,重点不放在植物以下之所谓“无情”者,而放在动物以上之所谓“有情”者,尤其是放在“人”这里。人和其他动物有相似处,也有不同处。人固然有特殊的躯体结构和心智能力,而有别于其他动物;然而跟其他动物一样,他也有饮食好色等生理的欲求及趋利避害等生物的本能。从同具动物性的欲求与本能上看,人和动物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不过人往往表现得更为精致而已。那么人与其他动物最大的区别在哪里呢?就在人有道德意识,能从事道德实践,这是其他动物所欠缺的。所以人存在的本质可以包括两方面:一是形气自然的存有,一是形上道德的存有。前者为人的动物性,这是人的“物性”;后者为人的道德性,这是人的“神性”。唯有从道德性看人,
才能真正把人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
在孔子以前的古代文献中,“性”字大抵指向自然存在的本质;自然存在的本质包括较低层次的本能、欲求及较高层次的气质、天分。如《尚书?召诰》所谓“节性,惟日其迈”,是说要节制骄淫的欲求,才能使道德天天进步。《诗经?大雅?卷阿》所谓“岂弟君子,俾尔弥尔性”,是说和乐平易的君子,让你能满足欲求,称心如意。但这并不表示古人没有道德意识,只是不从这里说“性”而已。
《论语》中提到“性”字的只有两个地方。其中之一见于《阳货》2章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历来对“性相近”一语有不同的理解。程伊川说:“孔子言‘性相近’,若论其本,岂可言相近?只论其所禀也。”(《二程遗书》第十八)他以为若从本原之义理上说性,每一个人都是相同的,不可说“相近”。因为说“相近”,内涵有所不同;这有所不同的“性”,只能从气禀上说,不能从义理上说。王阳明说:“夫子说‘性相近’,即孟子说‘陛善’,不可专在气质上说。
质,如刚与柔对,如何相近得?”(《传习录?下》)他以为若从气质上说性,则每一个人的性或刚或柔、或清或浊,差别很大,不能说彼此“相近”。所以孔子这里所说的“性”,只能从义理上说,跟孟子所说“性善”的性同一指涉。从义理上说的性,每一个人都相同;阳明在这里,是把“相近”解释为“相同”。孟子说一个放失其良心的人,“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气,其好恶与人相近也者几希”(《告子上》8章)。在这里,“相近”是“相同”的意思,所以阳明对“性相近”的理解,并非无据。《论语》中“性”字另见于子贡所说的“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13章)在这里,“性”与“天道”并称,“天道”是形而上的,则“性”或许也是指形而上的义理之性,但不必然如此。不管孔子有言或无言,“天道”与从义理上说的“性”总是深奥难解,所以子贡说在这两方面“不可得而闻”于孔子。然而从气禀上说的“性”相当复杂,要通盘把握,也很不容易,则子贡“不可得而闻”之“性”,未尝不可从这方面说。因为相关的章句太少,难以确定孔子言性的内涵。放宽来看,可以说孔子言性是义理、气禀两头通的。
孔子所说的仁、义、礼等道德法则,都是从人内在真诚的道德心发出来的,可见道德心也是人的特质。孟子于是进一步说这能自发仁、义、礼等道德法则的道德心就是人的“性”。道德心是纯善无恶的,所以说“性善”。孟子“道性善”,并不在否定人自然存在的本质,而是在通透人生价值的根源,使道德实践有一形上的根据。孟子对于人有感官方面的生理欲求当然很清楚,但要人正视此一天生具备的道德本质,并将它体现出来,以表现人格的尊严。孟子说: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24章)
人的耳目对于美好声色的喜爱,鼻口对于爽口香味的满足,手足对于安乐舒适的需要,这些都是属于其生理上的欲求,所以孟子首先承认这是性中所有之事。然而我们虽然有这些感官方面的需求,却不一定能获得相对的满足,而会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在这里有命存焉;命是人生的限制原则。因此讲究修德的君子并不一味追求它,强调在这当中“有命焉”,而不说它是性。反之,仁在父子之间相互亲爱,义在君臣之间的各尽其道,礼在宾主之间的往来恭敬,智对于贤者的深人了解,以及圣人对于天道的印证体会,这其中或有不能尽分处,或有不能透彻处,总难做得十全十美,也是有所限制的,所以孟子首先承认在这当中有命存焉。然而有德的君子体认到实践这些德行是人的天职,唯有努力奉行天职,才能使心灵获得快意满足。也就是说仁义礼智等道德的实践有其生命中内在的根源,所以说在这里“有性焉”,而不说它是命。
与孟子同时的告子对性持传统所谓自然存在之本质的看法,无法体会孟子“道性善”的真正用心及此一慧解在道德实践上的价值,乃有与孟子对于人性观点的论辩。在《孟子-告子上》前几章孟子与告子的论辩中,虽然从纯粹推理上看,孟子未必占上风,而告子也未必居下风;但是孟子对人性的洞见却是告子觉察不到的。虽然如此,我们却可以经由告子论性之言看出其对人性的观点。告子说:
性,犹杞柳也;义,犹杯椿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椿。(《告子上》1章)
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告子上》2章)
生之谓性。(《告子上》3章)
食、色,性也。(《告子上》4章)
性无善无不善也。(《告子上》6章)
在以上诸义中,“生之谓性”可以说是告子立说的总纲领,其他的论点,只是这一说法的辗转引申。牟宗三先生说:“‘性’即是出生之生,是指一个体之有其存在而言。……‘生之谓性’意即:一个体存在时所本具之种种特性即被名日性。”
(《圆善论》,页5~6)这里所说的“个体存在”,乃是从生物学上看的自然生命之个体存在。告子所谓“生”,是就个体生命的存在说;?而其存在所本具的种种特质就是其性,所以说“生之谓性”。董仲舒说:“性之名非生与?如其生之自然之资谓之性。”(《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这是告子“生之谓性”一语之详说。所谓“如其生之自然之资”是说相应于那个体存在的自然资质;这自然资质就是个体存在的种种特质。从这个地方说性,不但异类之间不同,就是同类的不同个体之间也有所差别。然而自然生命有共同的生理需求,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食欲和色欲,所以告子言“食、色,性也”。食、色等欲求固然无善可言,也唯有在过甚其求而对己或对人造成伤害时才可说恶,所以纯粹就食欲和色欲等生理需求本身来看,是道德地中性的,所以告子说“性无善无不善”。既然只是以个体存在的自然资质看人性,则其中并无道德的成分,所以会把仁义等道德律则看成只是外在的行为规范,而可以被人认知。人们不能顺其自然的资质,必须扭曲之,以符应外在的道德律则,才能表现道德的行为;犹如不能顺着杞柳的枝条,必须加以人为的斫削,才能造成盛物的屈木容器。再者,人性固然可经由人为的造作表现善,当然也可以经由人为的造作表现恶;就好像潆洄的流水一般,其向东流或向西流,初无定然,全看被引导向东方或被引导向西方而已。因此,若只从个体存在的自然资质看人性,则人性是中性的,而告子所说也是对的。
孟子经由亲切的体证,确信仁义等道德法则是直接由人的真诚侧怛之心发出来的,这真诚恻怛之心是人先天本来具备的特质;他就着这种特质以言性,所以说性善。孟子认为告子对人性的理解有所偏颇,想要扭转之,于是对告子说: 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杯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杯椿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杯椿,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乎!(《告子上》1章)
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上》2章)
孟子认为依照告子以杞柳之造成杯椿以喻人性之造成仁义之说,将使天下人误认为仁义不直接出乎人性而不看重它,甚至排斥它,这会造成对仁义莫大的伤害。再者,以湍水本来不一定要流向东或流向西,以喻人性本来不一定要表现善或表现恶,这样作类比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顺着水性而不加干预,水是向下流去的;同样,如果顺着人性而不去搅乱,人是向善而趋的。对于原本低处地面的水如果拍击它让它溅起,可以高过人的额头;对于原本低处山下的水,如果逼着它让它逆流,也可以高居山上。这是情势使然,不是水性原本如此。同样的,顺着人的天性,人的行为原本可以表现善;如果去搅乱他的天性,就会表现不善。告子与孟子都借水性以喻人性,两人所说的好像都有道理,这是因为对人性采取不同的观点。然而孟子心目中所认定之人性的道德性,却是告子看不透的。
由此可知,在一个人生命的存在中,“自然之资”固然是其所本有,“仁义之心”也是其所本有,二者都是人天生而有的本质。告子说性,只是看到前者,未能肯定后者,因而有所偏颇;孟子说性,不但承认前者,更能肯定后者,所以完备周到。孟子已经看出人性的这两个层面,不过尚未明显地用不同的名称标示出来而已。首先用不同的名称将这两种性明白标示出来的是张横渠,他说:
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故气质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正蒙·诚明篇》)
以上所说,显然本于孟子。“气质之性”是就人的自然之资说,“天地之性”则就人的仁义之心说。“气质之性”是随着人的形躯而有的,“天地之性”则是先天本有的。“气质之性”是说气质本身这种性,或是从气质方面所说的性。“天地之性”不是说天地本身之性,而是说与天地之精神同一之性,或是说从天地生化的源头那儿来的性,这就是后来程子所说的“义理之性”。如是,以气言的性与以理言的性便可作一显明之对较。要让天地之性存而不放,必须“善反”,也就是善于自我省察,以化去气质的偏蔽。气质的偏蔽既然是吾人所要对治的,所以“君子有弗性”。“弗性”就是孟子所说的“不谓之性”,不把它看做性;也就是说君子必以“天地之性”为人的真性。
君子对气质之性“弗性”,只把天地之性或义理之性看做性;义理之性乃是就吾人纯粹的道德心而说的,所以说“性善”。孟子所谓“性善”,是从价值判断的源头处言其善,这样所说的善不与恶相对,乃是绝对的善,所以胡五峰说:“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言之,况恶乎哉?”又引其父胡安国的话说:“孟子道性善云者,叹美之辞,不与恶对也。”(《宋元学案?五峰学案》)性是成就天地鬼神的奥体,也是兴发吾人德行的根源,最是纯粹美好。这样的纯粹美好,固然不可说是恶,但也不是相对的善,所以说性善的善是“叹美之辞”。牟宗三先生说:“孟子说性善,是就此道德心说吾人之性,那就是说,是以每人皆有的那能自发仁义之理的道德本心为吾人之本性,此本性亦可以说就是人所本有的‘内在的道德性’。”(《圆善论》,页217)“道德心”是人的“本心”,本心“能自发仁义之理”,这就是人的“本性”。所以孟子所说“性善”的“性”,就是人之“内在的道德性”。牟宗三先生又说:“孔子论仁,孟子论性,都是讲道德的创造性。……德行之所以能纯亦不已,是因为有一个超越的根据;这个超越的根据便是孟子所谓‘陛善’的‘性’。”(《中国哲学十九讲》,页431)“性善”之“性”是使德行纯亦不已之“超越的根据”,所以说它是“道德的创造性”。“道德的创造性”不属于“自然因果性”,而是属于康德所说的“特种因果性”,也就是“意志的因果性”。孔子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29章),就是从“意志的因果性”说的。
由此可知,孟子“性善”之说,本于孔子言仁,是就人的道德心以言性的;而告子“生之谓性”之说,只是顺着古来“性”字的用法,纯就个体存在的自然资质而说性。二人言性所涉及的层面及其在人的道德实践中之功能,迥然不同。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孟子以后的学者言性也有很多人采取告子的路线。荀子说:“性者,本始材朴也。”(《礼论》)性是个体原初的朴实材质,也就是个体的“自然之资”,它有好利、疾恶与耳目之欲、声色之好等特质,人往往不加节制而流于恶,所以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善是人为的造作,这与告子以扭曲人性来造成仁义的见解略同。董仲舒说:“性者,天质之朴也。”(《春秋繁露?实性》)性是人天生朴实的资质,也就是人的“自然之资”。他又说:“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