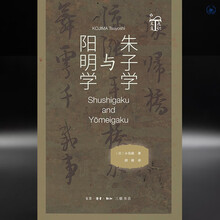关联的协同性
如果我们从经验的整体性与由此生发的关联性的构成本性出发,我们就会承认所有的行为是语境式的,因此就必定是协同的。没有什么事物可以独立自生,没有什么事物单独孤立地产生。呼吸是空气与肺的合作,看是眼睛和太阳的,走是双腿与地面的。毫不奇怪,我们看到所有定义气宇宙论的字眼都是协同的,交易的,合作的:天人、体用、变通、太极/无极、阴阳、道德、理气、无有,等等。在这宇宙论中没有高阶的或独立的“一”,没有奠基式的、初始原则,没有独控式的特权秩序,就像马赛尔·加拉奈特和其他东西方杰出的汉学家们所言:“中国智慧毋需上帝观念。”①
正如我们指“礼”的时候,必然假定同步地以“乐”作为情境,所以当我们指涉那个独一无二的初始的“性”的时候,我们必须认为“情”有其多样性。“性情”这两个词汇是看待同一事情的两种具体的、情境化的非分析方式。正是这种被唐君毅称为“一多不分观”(theinseparabmtyofoneandmany)的彻底协同性排除了自然种类的存在,它需要我们从情境化且独一无二的个体开始。我们从特殊事例而非从本质形式开始归纳。事物所处的特定情境之外,不存在离散的、本质性的、初始的、重复的本性。
承认了宇宙论的词汇如“性情”等是协同、互通的,我们就承认了事物的情境必须整合到其意义中去。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在关系中了解人,并且“呼其别名”,如兄弟、姑婶、老师。只有知道他们的角色以及他们跟别人的关系,我们才真正认识了他们。这种始终是条件式的、同源关联(parono-mastic)的认识论认为意义的源泉是富于生发性的关系,而这些变化的关系本身就必然是知识的组成部分和对象。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