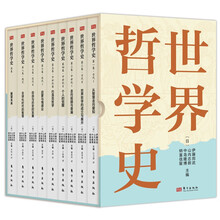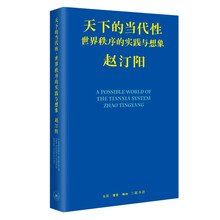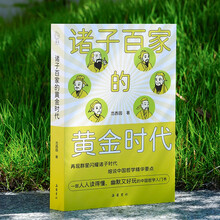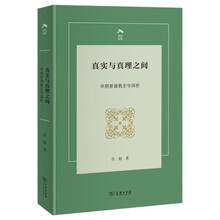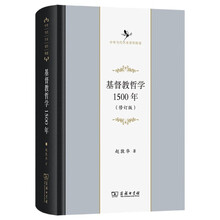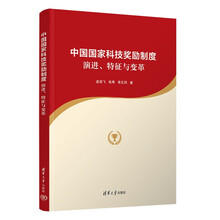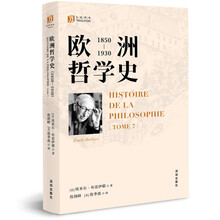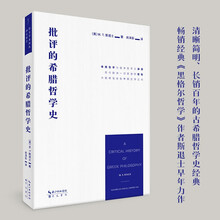葛兆光以“寻找位置的努力”评《中国哲学史》:“随着20世纪初大学教育制度的转型和文史哲三分的学科建立,谢无量、钟泰、胡适、冯友兰写出自己的哲学史,于是中国哲学史开始成立,因此我很同意并且同情中国哲学史成立背后的‘历史’,这个历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在‘民族本位’与‘世界大同’之间重新为中国的‘传统’与‘思想’寻找位置的努力。”(《为什么是思想史》)
陈卫平以“拒绝西方哲学范型”评《中国哲学史》:“然而,中国哲学显然是有其民族特点的,如果对此不注意,那么中国哲学史又会成为西方哲学在中国的翻版。分别在1923年和1929年出版的《周秦哲学史》(陆懋德著)和《中国哲学史》(钟泰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有鉴于此,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提出了挑战。……后者则强调,中西哲学各自成系统的,用西方哲学术语来叙述中国哲学,就会扭曲后者的真实面目,是极不合理的,……于是沿用传统术语而摈弃西方哲学用语。总之,他们试图去除中国哲学史研究当中西方哲学的一切印迹,以拒绝西方哲学范型,来净化、维护中国哲学史的独立性。”(《“金岳霖问题”与中国哲学史学科独立性的探求》)
曹树明以“中国化研究模式”评《中国哲学史》:“与胡、冯相反,钟泰倡导中国化研究模式。该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不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系统,而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身特点确定研究方法,采用中国特有的话语方式和问题领域整理中国哲学的内容。……该书发行后,长期以来被学界忽视,原因大致有二:一是西方化研究模式的主导地位使然;二是该书被误认为是对传统学术史的简单回归。”(《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模式述论》)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