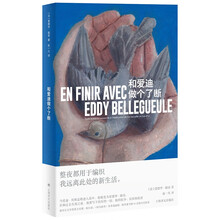“你错看了我了,淑!我压根儿就不知道你对我有心--一直到最近才知道;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个没有关系;难道你对我真有心吗,淑?你明白我这个话的意思吧?--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你说什么‘可怜我’那种话!”
那个问题是淑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愿意答复的。
“不过,说到究竟,这也并没有什么关系呀。你要明白,即便你没有这件事,咱们也应该各自东西。”
“不对,咱们不应该各自东西!这件事是唯一的障碍!”
“你忘了,即便没有障碍,那也得我爱你,也得我愿意作你的太太才成啊,”淑说,说的时候,带着一种温和的严肃态度,来掩饰她的真意。“再说,咱们又是表兄妹,表兄妹结婚,就不会有好结果。并且--我又是跟别人订过婚的人了。”“我有好几种理由不能冒冒失失地就把话对你说出来。这里面有一种我已经对你说过了;第二种理由是,我老觉得,我不应该结婚--因为我属于一个奇怪而特殊的家庭--属于一个结婚就犯别扭的家庭。”
“啊--这个话是谁对你说的?”
“我老姑太太。她说,咱们范立家的人,就没一个婚姻美满的。”
“这太怪啦。我父亲以往的时候,也常对我说这一类的话!”
他们两个站在那儿,心里让同样的想法所盘踞,这种想法--他们两个的结合,如果是可能的话,就要意味着一种可怕的阴错阳差,就要意味着盛在一个盘子里的两样苦菜--这种想法,即便把它当作一种假设,都够丑恶的。
“哦,这种话不会有任何意义!”她说,说的时候故作轻松,而实在却是沉不住气。“这只是咱们家的人,这些年以来,选择配偶的时候,老运气不好就是了--没有别的!”
于是他们就自己劝自己,说所有从前发生过的事情,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仍旧可以是表兄妹,仍旧可以作朋友,仍旧可以亲热地互相通信,仍旧可以见了面快乐如意地在一块儿待着,固然也许见面的机会要比以前少了。他们分手的时候,彼此很亲热;然而裘一德最后着她那一眼,却含着探询的意味,因为即便顶到那个时候,他还没完全了解她的真正心意呢……
我亲爱的裘德--我现在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你听了以后,也许并不至于觉得是突如其来:不过你确乎可以认为是加快了速度(像铁路公司说它们的火车那样)。费劳孙先生和我不久就要结婚了,在三个或者四个礼拜以内就要结婚了。我们原先的打算,本来要等我在师范学校毕业,得到证书,能够帮助他教书(如果需要的话),然后再结婚;这你已经知道了。但是他却优悠大度地说,现在我既然不上师范学校了,就不必再等了,再等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他这是为顾全我。因为我要是没闹到让学校开除了,我就不会有现在这种别扭的情况了。这完全是我自己的错儿。
你得给我道喜。你记住了,这是我告诉你的,不许你不听。--你亲爱的表妹,
淑珊纳·芙洛伦·玛丽·布莱德赫
裘德看到这个消息,身子都站不住了;早饭也吃不下了:一个劲儿地喝茶,因为他的嘴老发干。待了一会儿,他就上了工地,自己苦笑起来:这是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普通的常情。好像一切的情况,没有不跟他开玩笑似的。然而,那个可怜的女孩子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他只好这样自己问自己。但是他却又觉得,心里的滋味,比痛哭还难受。
“哦,淑珊纳·芙洛伦·玛丽呀!”他一面工作一面说。“你并不明白结婚是怎么回事啊!”
上一次由于他喝醉了跑去看她,所以她受了刺激,才订了婚约。是不是这一次又和那一次一样,因为他把他的婚事对她说了,又刺激了她,才促成了她这一步的行动呢?固然不错,使她作这种决定的,还有其他充分的理由--还有实际方面和社会方面的理由;但是淑这个人却并不是顾实际、工心计的啊;所以他就不能不想:这大概是费劳孙跟她讲过,说要证明学校当局对她的疑心完全没有根据,最好就是按照平常履行婚约那样,马上和他结婚。费劳孙跟她这样说了,同时她又突然听到了他的秘密,心里一不受用,自然就听了费劳孙的话了。事实上,淑是处在一种非常别扭、走投无路的地位上的。、可怜的淑!
他对淑的爱,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在她结婚后的第二天和第二天以后那几天里,更明白地显了出来。梅勒寨的灯光,不是他再能忍受的了;梅勒寨的阳光,只是一片颜色沉滞的油漆了;梅勒寨的青天,只是一张锌板了。跟着他收到了一封信,说他老姑太太正在玛丽格伦病得很危险。和这封信差不多同时来的是基督寺他的旧雇主给他的另一封信,信上说,如果裘德愿意回基督寺,他可以给他属于高级的长期工作。这两封信使他觉得轻松了一些。他先起身往他老姑太太那儿去,同时决定由那儿再到基督寺,去看一看,他的旧雇主给他的这种工作,究竟怎么样。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