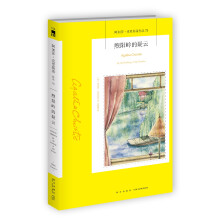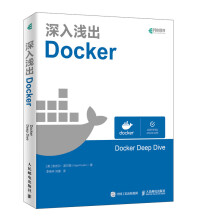冥王星为什么重要?
“冥王星万岁!”
“别再搞行星歧视!”
“冥王星是被陷害的!”
“亲爱的地球:你这浑球。冥王星敬上。”
“冥王星仍然是颗行星啊混蛋。”
2006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IAU)在布拉格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与会者表决,将冥王星逐出了太阳系。消息传出,街上的T恤衫和汽车保险杠上就出现了大量反对标语,以上就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突然之间,IAU决议就将冥王星在科学上除了名;它在文化上、历史上、乃至神话上的地位也被一并剥夺了。
在天文学家看来,要将冥王星称作“行星”已经越来越难了;如果要继续这么称呼,就得给几颗晚近发现的天体同样赋予“行星”的称号――其中有块名叫“Eris”(以前叫“Xena”)的冰冻岩体,其体积甚至比冥王星还大。但光凭这一点,还不足以让专家剥夺冥王星在苍穹中的地位。“行星”的定义更多地涉及语意,而非科学1。与其将冥王星逐出太阳系,还是新发展几颗行星比较容易――有些科学家、历史学家和记者的确就是这么建议的2。但IAU拒绝妥协3,他们搬出了好几条专业理由:冥王星比另外八大行星小得多啦;冥王星围绕太阳转动的轨道更接近椭圆啦;冥王星的引力太小,无法“清理轨道周边的大型物体和碎片”啦;等等等等。
听到这个,美国人惊呆了:“冥王星是行星”是他们从小就学到的,是他们记忆中重要的天文学知识。要改可没那么容易。再往深了一层看,他们觉得这么做不公平;IAU决议激发了他们对弱者的同情――为什么突然就把冥王星踢出了行星联盟呢?自1930年发现以来,它已经在里面待了近一个世纪了。一位卡通画家写道:“不准反悔。”4
很快,相关网站纷纷成立,它们呼吁网民投票,推翻专家的决议,让冥王星保留原有的地位。有人在Facebook上成立了个小组,组名叫“我在你这年纪,冥王星还是颗行星”,组员达到了150万人。新墨西哥州人民对的反对声尤其强烈――当年,冥王星的发现者克莱德·汤博(Clyde Tombaugh)曾在这里发起过一个天文学项目。墨州众议院经过投票,一致决定保留冥王星的行星地位,还将2007年3月13定为“行星冥王星日”。美国方言学会也把“被冥王星”(plutoed)选为了2006年的年度单词。学会还给它下了个定义:“使某人或某物降级或贬值,例如: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在全体大会上判定,冥王星已不符合其行星标准,此举致使这颗前行星被冥王星了。”
甚至许多科学家都感到了不安。天文学家艾伦·斯特恩(Alan Stern)就说天文学界让他“觉得丢脸。” 5斯特恩是美国国家宇航局“新地平线”项目的首席科学家,项目宗旨是飞往冥王星及以外的天体。斯特恩质疑了将冥王星降级的程序,称“只有不到5%的全球天文学家参与了表决。”别的专家也表达了不同意见;还有人打趣说,IAU就是“无关紧要的天文学联合会”(Irrelevant Astronomical Union)。喜剧演员也开足马力。笑星比尔·马赫(Bill Maher)就讥讽道科学家是在“割肉”。史蒂芬·高博特(Stephen Colbert)打趣说,这颗前行星被迫与太阳系外的“同类”会合,已被“平等隔离”。类似的笑话层出不穷,拜它们所赐,理应是冷静理性的科学界现在换上了一幅喜怒无常的嘴脸。
总之,对这个决议满意的人几乎没有;下一次IAU会议(定于2009年8月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甚至有可能重启辩论。那么,这场星际冲突是怎么闹起来的呢?参与的科学家难道没有预见到公众的反应?还是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从科学上说,冥王星决议真的必要吗?
这些问题涉及很广,远不止是太阳系有几颗行星的问题,也不止是未来的婴儿摇篮上会有什么挂件的问题(婴儿摇篮上常挂有行星模样的挂件――译注)。因冥王星而起的喧哗是个生动的例子,它展现了科学和其他社会部门间的鸿沟。在美国,这道鸿沟尤其醒目;而美国又是个特殊的国家:它的科研在世界上居于领先(至少目前如此),但它也孕育了一股强大的反智文化,让民众对科学不管不顾(只要科学家别折腾冥王星就行)。
仔细想想,这个反差真是惊人。美国有规模庞大的科研设施,每年支持科研的联邦经费超过1,000亿美元6。巨大的硬件投入在全国织起一张大网,其中有政府实验室,有各类研究机构,有世界一流大学,也有开展广泛研究的创新企业;这些机构在网中各得其所,共同撑起美国的科学事业。正是因为巨额投入,美国才造出了原子弹,登上了月球,破解了基因组,发明了互联网。然而,就是这样的美国,孕育出了一批对科学无知的国民。他们不是彻底无视科学的进展,就是干脆拒绝科学的原理,决绝的程度令人触目惊心。比如,许多美国人拒绝接受生物演化的理论和事实,数量之多令人沮丧。他们不相信我们这个物种、还有地球上形态各异的其他物种,都是由演化产生的,尽管这一点在科学上已经确凿无疑。再来看疫苗:疫苗是医学史上一项伟大、成功的发明,到二十世纪末为止,它们每年都挽救一百万人的生命7。而现在,在反科学的美国人中,却有一些富有影响的个人走上了危险的道路,不让自己的孩子接种疫苗。这个国家已经被政治一分为二,两边的阵营对现实有着不同的理解。同样是受过大学教育的民众,在民主党员中,相信“全球变暖是事实,而且是由人类活动引起”8的比例,比共和党员高出两倍还多。不仅是这样,美国还在丧失二十一世纪的科研竞赛中的领导地位,逐渐被印度和中国等取代。
如果美国真的失去了先机,那么公众对科学的隔膜肯定会是一个原因。在美国,科学或许是费解的、可怕的、甚至拒人于千里之外;公众与科学的接触也往往浅尝辄止。调查显示,只有18%的美国人认识一位科学家9。能叫出全国最高科研机构的人就更少了(国家卫生研究所NIH,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SF)。2007年底的一项调查要求受访者说出一名科学界的典范人物,结果44%的人交了白卷10――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在收到的答案中,“盖茨”、“戈尔”和“爱因斯坦”出现得最多;而这几位,有的根本不是科学家,有的已经不在人世了。
现状如此,在科学家每天起床接着改造世界时,美国的普罗大众就难免跟不上了。正是两者的疏远,让冥王星式的冲突反复爆发:民众突然闹明白了科学家在干什么,随即报以愤怒或警觉,甚至更糟。
冷落冥王星不会在地球上引发什么大不了的后果;但科学和社会的脱节却会产生严重的破坏。我们生活在变革的时代: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生态饱受掠夺,生物医药研究争议频频。世界上有许多值得恐惧的事物,比如全球疫病、核扩散、高科技恐怖袭击等等。在遗传学和神经科学领域,我们都站到了突破的关口上(其他领域也是)。这些突破会重新界定我们的身份,甚至让我们的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时代,科学理应在政治生活、经济前景、甚至人民的生活方式、日常习惯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然而,令人担忧的分歧却一次次出现在我们眼前:一边是我们对科学的理解;另一边是我们生活、参政、求知、娱乐、以及界定自我的方式。
科学家和美国大众之间存在文化隔阂。更严重的是,这种隔阂持续存在,愈演愈烈,已经体现在了决定我们如何思维的社会部门中。在政治、新媒体、娱乐、宗教等领域中,科学都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实际上它没有。
2001到2008年,一届广受批评的政府主宰了美国政坛,它对科学极其蔑视,在美国近代史上尚无先例11。和这个反面教材相比,巴拉克·奥巴马的政府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希望。但无论如何,科学在政界仍受冷落。它理应在决策和治理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但获选上台的官员对此少有体会。无论是民主党,共和党,许多政客都没能在自己关注的问题中看到科学,尽管科学在这类问题中几乎无处不在。实际上,凡是政客都有意让自己显得对科学不太精通,因为他们不想让人觉得自己是书呆子。
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在1962年写了本经典著作,题为《美国人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12。书中记载了对智力活动的蔑视如何成为了美国文化的痼疾。作者提出的问题现到还在困扰着我们。在对待科学家的态度上,这个问题显得尤其迫切,而且,它从美国诞生以来就忽隐忽现,始终存在。比如,我们为倍受尊崇的国父富兰克林重写了传记,把他塑造成了喜欢修修补补的的凡夫俗子,而实际上,他却是位深谋远虑的一流科学家13。法国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4曾在1830年代访问美国。在他看来,这里的人民对成品的兴趣超过了成品制造过程中的智力挑战和问题。他这么总结道:比起理论来,美国人较关注科学的实际应用。长久以来,美国科学家都要和两股力量竞赛:一股是我们务实进取的态度,另一股是我们的宗教虔诚。当迈凯恩和佩琳在2008年的竞选中嘲讽对果蝇和灰熊的研究时,他们想讨好的正是美国的这股反智风气。他们满以为这样就是给自己加了分;不过这大概也是事实。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