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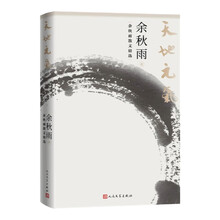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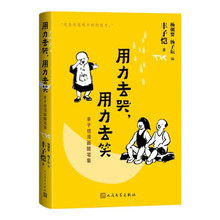



《印象阅读:翻阅时光》将在书评与印象记之间,寻找一种妥协、一种融合。入选作者,则老少成宜。愿望,是借这样一本书,为不同读者提供较为丰富的知识、趣味与见解,为当今书评类写作状况,留下一幅色彩斑斓的景象。
地坛与合欢树的记忆 2010年最后一天,我去季风书店慰劳一下疲惫的心灵,偶遇在报社工作的石君,他轻声对我说:史铁生去世了,在今天凌晨。书店里很安静,但我还是瞪大了眼睛急忙追问缘由。我不应当这么惊奇才对,因为我见识过病魔带给他的痛苦。他三天就需要透析一次,透析后的第一天,人很精神;第二天精神大减;第三天,差不多委靡不振了。而且,我想象不到,做完透析后他十分饥饿,饿到必须立即吃东西的地步。2004年春天,在上海,在王安忆老师的指挥下,我所做的事情就是推着他的轮椅飞奔到宾馆去吃东西…… 为了方便透析,他在胳膊深处直通血管埋了一根管子。他曾让我伏在上面听一听,我被震撼了,血流涌动的声音完全就是长江大河奔腾而下的声音!人的细小血管中竟然蕴藏着这么大力量,生命的激情太令人震撼了!难道……它就突然停息了?那訇訇的奔突声就消失了?对于生死,背负着苦难已经走了很久的史铁生曾有无数次的叩问,在《我与地坛》中,他说:“死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 我欣赏这种面对苦难的态度,我欣慰他的苦难总算得到解脱,但我还是自私地不希望这个节日这么早就降临到他的身上。
作为一个读者,送别自己喜爱的作家最好的方式就是默默地读他的书。翻动着冰冷的书页,我想起了许多他的文字伴着我们走过的时光,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我觉得那才是20世纪文学的又一个黄金时代:从王蒙到王朔,从张承志到余秋雨,从新写实浪潮到陕军东征,仿佛积蓄了多少年的能量在此找到了井喷的出口。一部部作品在所谓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之后,终于为它的真正读者所阅读:《九月寓言》、《废都》、《长恨歌》、《活着》、《坚硬如水》、《丰乳肥臀》、《马桥词典》,还有苏童的那些中短篇、于坚等人的诗、李辉打捞历史的“沧桑看云”系列……每一部作品都曾留下不同的阅读记忆,有赞赏,有感叹,也有争论;社会正在日益世俗化,人们都在奋不顾身地“下海”、“走穴”、倒卖,然而此时毕竟还有这样一批作家和这些作品丰富着我们的精神空间。外界环境如此喧嚣,而他们却又如此执著于精神的探索和表达,这中间有多大的反差啊,然而正是这种反差才凸显出这批人的可敬。那是一些在人生最迷乱的岁月中伴着我精神成长,在内心最为孤独的时刻给了我生命营养的作家和作品,虽然现在我早已过了追星的年龄,但我对他们始终保持着特殊的敬意,这是后来的一些作家用再多再轰动的作品也永远无法取代的尊敬。
为此,我很久前曾发愿有朝一日一定要写一部《九十年代文学史》,将别人以为文学已经边缘化,但它却蓬勃生长的景象描述出来;同时也是在梳理自己的精神史。毫无疑问,史铁生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章节。
《我与地坛》,发表于1991年第1期的《上海文学》;1992年秋天,我进入了大学,至今我仍十分感谢一位姓耿的教我们写作的老师,她以对当代文学的热爱、敏锐的感觉、不俗的审美鉴赏力引导着我们的阅读,也不断地为我心中高涨的文学火焰拾柴加薪,她向我们推荐《我与地坛》,给我们讲《命如琴弦》。“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总之,只好认为这是缘分。……仿佛这古园就是为了等我,而历尽沧桑在那儿等待了四百多年。”这样的句子立即就把年轻人俘虏了,大家传抄着,甚至在手记中不断地模仿着写下很多类似的句子。对文中用四季来对应地坛的时节和人生的时序也佩服得不得了,常恨心中没有他那么多的比喻。至于一个人“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废了双腿”的心态,我们也试图去理解,对于苦难、命运、欲望、救赎这样的话题,也是我们所喜欢的“深刻”。反正,这篇文章当时大家是争相传诵着,不过对于文字中的禅机,甚至对于苦难与命运的追问,又哪里是我们这帮初出茅庐、什么风雨也没有经历过的人所能领会的呢?近二十年过去了,当年一起读《我与地坛》的同学哪里去了?我只知道耿老师也离开了那小小的校园,她还会记得那些为文学沉醉的日子吗?如今谁还会以一颗白心静静地重读《我与地坛》吗?如今还在传抄这样作品的人是不是都是不正常的人呢?史铁生对当代文学的另一杰出贡献是他的长篇小说《务虚笔记》,在务实的时代中能有这么漫长的写作之夜、这么大篇幅的“务虚”,是史铁生向命运挑战的结果,这部书集中了他的写作才艺和对人生的思考。不过,我得承认,当年我并没有读懂它,以后几次想认真读读它,都因心境浮躁没有气力来完成,特别是他用英文字母来命名人物的写法更是让我眼花缭乱。
有段时间,我发现缺少阅读史铁生的耐心了,觉得他越来越玄,到2006年《我的丁一之旅》,我从大连背回上海,又几番从上海背到别的城市,始终没有读完它。我心中很歉疚,觉得背叛了对这位作家的敬意。渐渐我发现跟我谈论史铁生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偶尔一次有人说起《病隙随笔》,我激动了老半天,不久大家谈论的只是史铁生的病了。这两天我总是在检讨:远离史铁生究竟意味着什么?是不是我的心越来越虚浮?——也可能越来越实际进而远离了“虚”和“玄”。我忘不了同样在上世纪90年代,《收获》杂志的一句宣传语:“在世间所有虚妄的追求都过去以后,文学依旧是一片灵魂的净土。”史铁生之于当代文学的意义,除了他所贡献的那些作品之外,还有一种精神和品质,他的文章是干净的、宁静的,他的存在显示着文学“灵魂的净土”的价值和意义。
文学在当今是百无一用之物,但一个作家也有他的幸福之处,比如由于文字,许多读者与作家自然而然有了亲近感,作家也沟通了人们的心灵,让疏离的世界中的人们彼此靠近了许多。正因为这样,见到史铁生我一点也不觉得陌生。那是2004年5月,王安忆老师刚到复旦大学任教,有了一笔经费,她想到了请多年未曾到沪的老友出来看一看。我当年的日记中曾有两次记到这件事情。5月25日:“史铁生上午9时半来校演讲,有王安忆和马原陪同。史人很平和,但面色乌黑,着毛衣。中午饭后,谈关于美国、梦想、信仰,没想到竟然争论起来,我觉得他太单纯、书生气了。”与复旦学生的对谈是在复旦叶耀珍楼多功能厅进行的,暗暗的,环境不很好;可能是上午,那天来的学生似乎不多,与贾平凹来时学生把逸夫楼挤个水泄不通无法相比,即便这样,史铁生说他已经够紧张了,“在飞机上紧张,在地上也紧张”,“今天见了这个架势,还是让我紧张”。这不是矫情,是真实的状态,所以他开头就说要申请抽支烟,消除紧张。更多的时间留给了同学提问,有人提到了《我与地坛》,表达了对作家的敬意。
这个对谈后来曾以“我们活着的可能性有多少”为题发表在当年《上海文学》第7期,我找到当年整理稿的电子文档,没有想到这是史铁生当年修改的回传稿,上面是醒目的一行:“周立民老师:文中改动部分,红字为准,蓝字删去。史铁生04,6,11。”如今对着它,我良久无语。那天的“争吵 ” 发生在午饭后,上海某作家的日记中还曾记过一笔,说复旦一青年还是学生的,那就是我。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客套,主要是我觉得他们这代人太崇拜美国及其一切了,我觉得我们没有那种心态;而史铁生则认为如果没有信仰和梦想怎么能行呢?我的反驳又是:美国就是我们的梦想吗……那天饭后,虽然不是剑拔弩张,但也算你来我往谁都不相让,安忆老师甚至也来浇水熄火。不过讨论问题是讨论问题,不伤和气。或者正是史铁生的和气,不摆大名人的架子,才有了我的放肆。现在想来,我的很多较真儿实在很愚蠢,我们东北人也太直性子了,他讲了一个上午我为什么就不能让他休息休息呢?两天后,我又见到了他,5月27日,“下午4时半,到宾馆见史铁生,后王安忆来,推史到附近医院去透析,史一再说王安忆太热情,心甚不安。我见王半跪在地上替史系鞋带,十分感动……”系鞋带的细节我终生难忘,那一代作家彼此温暖着携手前行的友情是浇灌我灵魂的净水。记得那一天在宾馆闲谈中,他说过:不能要求作家的下一部作品就比上一部好,这做不到(大意)。我理解他的意思,更佩服他看得开,写作不是争胜,一个作家只有剥除了这份心态才会更自由地写作,也才会越写越好。
此后,有一年在北京,是一个文学奖的颁奖,我见到过他,那天风很大,他有些感冒,还是抱病出席…… 多少年前,史铁生的母亲不经意中种下一棵合欢树,一度以为它死了,没有想到竟然活了过来。她呵护着它,也常常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苦难让他们忘记了这棵独自承受风雨的树,儿子腿残了,经常抱怨命运的不公,更为不公的是母亲年仅四十六岁竟猝然逝去,儿子痛苦中只有这样安慰自己:“她心里太苦了。上帝看她受不住了,就召她回去。”母亲去世后,史铁生的小说接连发表了,得奖了,但她看不到了;这棵合欢树长高了,也开花了,但她也看不到了……老房子新换了人家,那有一个孩子,史铁生感慨:“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起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儿,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