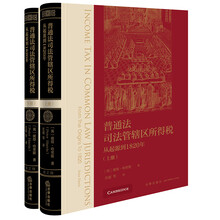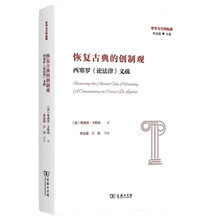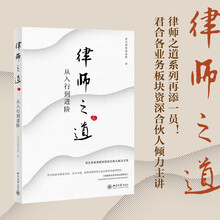萨维尼之后,很多法学者亦对系统的思考深感认同,但此时萨氏的整体性观察法进一步变迁为,如何将众多概念加以合秩序安排的概念建构。沿着这种思考就形成了概念法理学,它为德国法哲学从此获得全球性声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鲁道夫·耶林,19世纪同萨维尼比肩的伟大法学家,使得概念法学“成也于斯人,败也于斯人”。在他的首版于1877年的《法之目的》一书中,耶林试图将法之目的安插人此前概念所居的位置。耶林的实用主义获得了世界范围的成功,原因就在于他触到了关键点:法之目的论结构。此一思想延续时间很久,耶林自然也有些夸大其词。其实,问题并不在于,究竟是目的还是概念具有决定性,而是在于,如何将二者摆放到正确的关系位置当中。
在对这一问题的漫长讨论中,20世纪的法哲学逐渐浮出水面。那些曾经属于康德、黑格尔、萨维尼以及耶林的风骚,如今又花落至凯尔森和拉德布鲁赫。凯尔森分别写就的两版《纯粹法学》,首版于1934年,二版于1960年面世,可谓是最有意义的实证主义法学作品。
被我们的方法论当作严肃的教义学方法来反复折腾——是这样一种程序,它以逻辑的方式将法条适用于它们所没有涵盖、但与它们所涵盖的案件相似的案件。仿佛就是如此简单:任何一个案件都不会与别的案件有任何共同之处,哪怕在最低限度上与它们有一点相似之处!因而人们是要为几乎每个案件都寻找到一个可适用的法条(这样做无疑是舍近求远),而不是每次都去通过逻辑划定所容许(类比)的界线,这种逻辑完全随意地来划定量与质的分界线。同样,因为扩张解释(extensive Interpretation)所借助的不外乎是与案件的相似性同样的动机和手段,它就应受到与类比同样的批评;当类比被禁止时(刑法典第2条),人们会让它充分发挥作用!并且它也很好地扮演了这一角色。人们会一直将解释推进到语词(Wortlaut)最宽广的界线,并且还要超出一些。我们的法院档案陈列室都知道,在“危险工具”(gefahrliches Werkzeug)这一标记之下可以将哪些东西没收充公!相反,没有人会认为,“制造者”——依据民法典第950条他通过加工取得新物的所有权——这一表述同样可以被理解为产业工人和工匠,因为那样一来就属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了。
法与意志——意志一会儿要求我们得出它所愿意看到的结果,一会儿要求我们避开那些它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我们并不采纳某种能得出所有结论的建构方式(因为它是最没有强制、最合乎逻辑、最自然、最好的);而采纳这样一种建构方式,即它的结论恰恰是我们所意图的。
与当今的类比相同,应被放弃的还有法律拟制(juristischeFiktion),因为它不外乎是类比的一个亚类型。只有当它被一个民族在保守的意义上用于一种制度的历史性发展时(如同罗马人一样),它才是可以被容许的;相反,当它被用于将一个具体的法条体系性地延展至它没有涵盖的案件时——只因人们惰于构想出一般性的普遍规定,或者担心暴露出他们的表述矛盾,因为在拟制的外袍下.矛盾的结果可以悄悄潜入法律而不被觉察到——它就是不被容许的。此外,拟制的其他功能也没有学术价值,它不外乎是一种服务于错误的方法或实践利益的用以隐蔽谎言的主要策略。法律拟制决不能与其他学科中的那些单个的抽象化方法(如真空环境、经济意义上的专制)相比,它们是完全合法的,但有时是危险的,它们有时也恰好被称为拟制。因为这些方法上的“拟制”(methodischeFiktionen)不外乎是一种辅助性研究手段,它将结论视为只是有条件的正确的;但法学上的实质性拟制(materieUeFiktionen)却是认知的障碍,因为它被理论看作是永恒不变的组成部分,或许人们对此还感到特别自豪。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