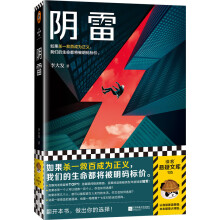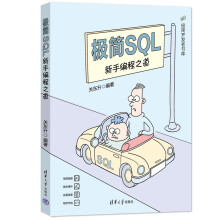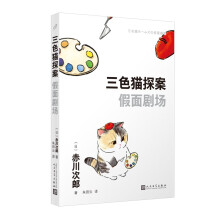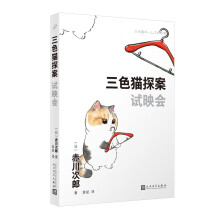尽管人们正面遭遇着形而上危机并表现出恐惧、感叹或某种程度的束手无策,但这丝毫阻挡不了其在形而下层面对解决现实文化问题的自信和进取,阻挡不了各国政府的公共文化政策立场及其文化制度设计中为求取文化利益极大值而衍生出来的系列化文化治理与文化服务技术支持方案,即使那些经济发展状况极端弱势的国家,也都会顽强地坚守其政府文化治理的政策选择努力,就仿佛几内亚政府的文化行政部门在财政支付困难背景下的笃信“无论如何,任何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生活之中的真实文化,都能够形成对试图淹没它的抵抗,并能够确保其自我维系和人民创造精神永存,仿佛一粒富有生殖力的进步种子。这就是几内亚人民的道德与文化价值”,或者文化遗产保护中玻利维亚式的“致力于构建制度化的登记,对所有玻利维亚考古的、艺术的和历史的财富进行造册,严格其法律强制性并禁止其出口”。虽然这样的笃信、责任和努力较之克莱德·克拉克洪那种“十一层次定义法”中诸如“通过‘文化’,人类学家旨在说明人们的整体性生活方式、个体从其群体中所获得的社会遗存,或者说,文化可以被看作是人所创造的环境部分”的意义边界切分要表层化而且笼统得多,但是这丝毫不表明关于文化问题的形而上处置方式就一定比形而下处置方式更有价值优先性,只不过处置方式的差异,导源于将其设定为不同的处置对象而已。在形而下处置方式中,尽管文化的意义本体深刻而且纠缠性存在于具在的文化事态中,但人们处置的不是那些意义本体而是文化事态,单从学科分析的知识范式而言,这实际上也是公共文化政策学家完全不同于文化人类学家知识身份之所在,尽管文化人类学知识谱系从来都会给文化政策学家以背景性支撑。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