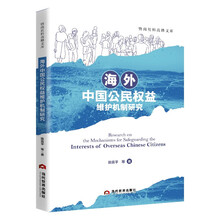我们需要详细阐述一个更复杂、更合理、更符合现实的而不是自然主义或理想主义的社会善恶模型。从符号意义上来说,恶不是一个剩余范畴,尽管那些属于恶的范畴之内的事物在社会上是边缘化的。从只是让人觉得讨厌、恶心的东西到真正邪恶的东西,恶深深地体现在对善的符号表述和制度化维持中。因此,恶在制度上和文化上的生命力必然要持续下去。圣俗之间的分隔线必须一次又一次地重画;这条分隔线必须保持生命力,不然所有的一切都会丧失。人们不仅在认知上对恶进行符号
化,同时也以一种生动的、感性的方式体验着恶--正如我在本书几乎每一章节都提到的那样。通过丑闻、道德恐慌、公开惩罚和战争等现象,社会给出了对善的敌对面进行再体验和再明确的机会。恐惧、排斥和害怕等令人揪心的经历创造了净化的机会,维持着柏拉图称作“公正的记忆”的生命。只有通过这种直接体验--由互动或符号性交流提供的一一社会成员才能逐渐认识到恶,并开始对其感到害怕。这种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悲剧性经历和知识基础的情感道德宣泄同样也是这种认识并害怕恶的体验的核心。这种认识和恐惧激发着人们对他人的恶进行谴责、对自己的恶意图进行忏悔,并举行集体层面的惩罚与净化仪式。这样.神圣、道德和善得以复兴。换言之,恶不是像福柯和马克思所说的那样简单地通过维持支配地位和权力而生产出来的,而是为了维持把某事物评估为积极的可能性而生产出来的。恶必须在每一个社会领域进行编码、叙述和体现--在私密的家庭领域、科学世界、宗教、经济、政府、初级共同体等领域中。在每一个领域和每一个作为整体的国家社会中都存在着精心雕琢的关于恶如何发展、可能在哪里出现、历史上善恶之间的斗争以及善如何能够再次战
胜恶的叙事。
这种视角对于我们审视现代社会的文化过程和制度过程的眼光都有很深的启示。在本书的各篇文章中,我将以“二元表征”的术语来讨论前者。在这里我想使用“惩罚”这个词,先来讨论后者一一恶的制度过程。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