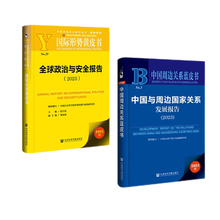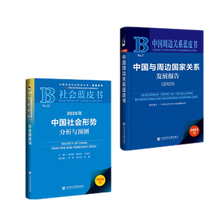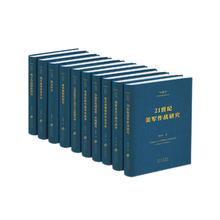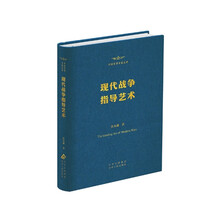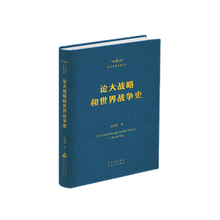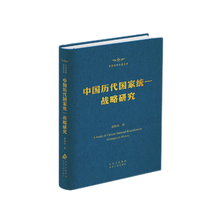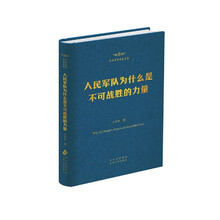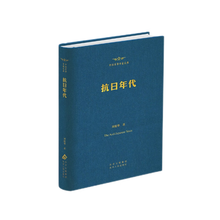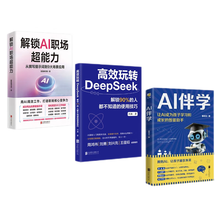章清: 谢谢桑兵教授。我想除了陈寅恪先生所阐述的“了解之同情”,我们还可以比较多地接触到的是另外两个“情”,一个是“移情”,柯文在《中国中心观》里面表达过这方面的意思,而钱穆先生也讲过“温情”。我想不管哪个“情”,其实都涉及到历史学这门学问比较关键的一些东西。因为做历史研究的从时间来说总是存在一个天然的隔断,那么用什么方法能够尽可能地感受到古人所说的东西,这就成了对做这门学问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 今天桑兵教授是讲陈寅恪先生治史的方法。他实际上是从一个很小的角度人手的,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更重要的是示范了自己对于治史的一些体会,我们也可以透过他所分出来的不同的段落大致感受到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要了解陈寅恪先生所讲的“了解之同情”,最基本的是从文本进入,这个文本本身要读通读透,不要选出一段就任意进行发挥,那样做未必理想,尤其是涉及到像陈先生这样的一些高人,随便抽出一句话大概未必合适。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呢,我想他也特别举证了关于整理国故和古史辨这段历史。其实这也是提示我们,不管怎么说,陈寅恪先生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说的话一定是和那个特定时代的信息有关的,所以我们也需要透过当时的学术环境去进行把握。其实这方面的例证,在研究别的历史的时候也有一些学者强调过,比如说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我们都是把它当成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较量的第一个回合。我想关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胡适本人也是这么说的,如果结合当时的文献就很清楚,以这种方式来解读那是太离谱了。胡适发表问题主义的演讲,他所针对的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即便马克思主义能够是批评的对象,那也是十数个批评的对象之一,这里面可能涉及对无政府主义等诸如此类现象的批评,但我们都不去涉及。我想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要了解陈先生针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所做出的一些评述,牵涉到的就是当时的整理国故、古史辨这样一些学术思想背景。第三个层面,我想就是他从正面来回答陈先生的治史方法究竟是什么。涉及到这样一个正面讨论的时候,背景就更为宏大了,就涉及到要在学术思想的传统里面去感受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究竟是什么。 这是我所理解的今天桑兵教授给我们讲的陈寅恪的治学方法,他不但是在讲这个方法,也是在示范他对治史的一些理解。我们还有一些时间,下面就开放给大家。请提问。 学生: 我非常认同打破时空框架是历史研究的一大门路,所以我们回到“了解之同情”,就要返回到那个时空去。我一直有个疑问就是,“了解之同情”这个词最早是德国启蒙运动时期赫尔德的一个概念,或者叫“同情之理解”,或者叫“了解之同情”。但是我的感觉是,陈先生在用这个词的时候,要表述的意思和原来的意思有所不同,而且我感觉是完全相反,其实它最早的含义应该说是尊重当时的历史语境,探讨问题的时候要回到当时的知识背景中去,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来探讨这个历史问题。但是陈先生批评的比如格义附会之类的做法,好像这并不是原来那个“了解之同情”或者“同情之理解”的含义。我感觉是不是陈先生的“了解之同情”并不是原来的意思,是陈先生自己个人的理解呢?就是说他确实受了当时西方的影响,有的学者说他在哈佛大学受过白璧德的影响,当然我也是很存疑的,但是不是有这个方面的意味?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