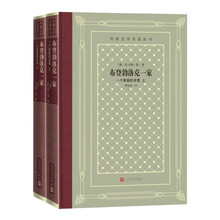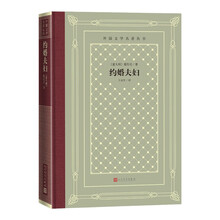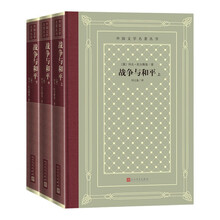我那时以为这一生大概只会做一件事:离开村庄。
我并非在村庄里过得不愉快,那里的水土很适合我,只不过村里人都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认为离开村庄才有出息。我只能让自己有出息点儿。
我选择在一个夏天离开,那是一个炎热的晌午,人们都在打瞌睡,我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为了不让他们以为我有什么留恋,以为我带走了村庄的什么东西,我要走得有出息,能留给他们的全留给他们。
后来我发现我是自欺欺人,路上累了歇脚的时候,把行囊打开,里面装的是一整个村庄。我很羞愧,我曾想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把它们抖掉,但在人生这段漫长的路上,想要的东西还未得到时,拥有的东西就无法舍弃。
在县城读书,我不能舍弃我的贫穷。在寄宿的同学中,我的伙食比许多人都要差,一般我只买个小菜,另外吃自己带的家乡菜:咸鱼、坛坛菜、鲊辣椒。这几道菜都是干的,耐放,很下饭。肚子饿了,就用炒米茶充饥。炒米茶是母亲亲手做的,先炒米,炒黄豆,炒芝麻,炒熟后,用石磨磨成粉。用开水一冲,加点儿红糖,很香。在我陶醉于母亲说的营养时,喝着麦乳精的同学都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
在省城读书,我以为离村庄越来越远了,却又无法摆脱家乡话的困扰。我既说不好普通话,也说不好省城的方言。说普通话,边音和鼻音、卷舌音和翘舌音分不清;说省城话,走在大街小巷,别人一听,都嗤之以鼻。我为企图抬高自己而装腔作势感到难受。我开始很少说话,我怀疑自己是否能够上品位地交谈,只有上厕所时,会冷不丁骂出一句家乡的脏话。
在机关里办公,我摆脱不了家乡老土的做派。走路还没学会挺胸亮脖子,说话还没学会慢条斯理,办事还没学会大刀阔斧,我常常怀疑同事是不是私下里议论我是个乡巴佬。老乡来时,我打肿脸充胖子招待他们,我怕他们说我小气,说我忘恩负义,我瞧不惯他们的心眼儿,同时看到他们就像看到自己,我为此感到忧戚:难道真的就抛不开村庄了吗?
在我尽力掩藏村庄时,村庄却如影子一样照看着我,照看着像我一样从村庄出来的许多人。
我毕业后被安排到这座城市,得感谢利叔。利叔和我是同村人,出来许多年了,混出了一点儿名堂,他常常为帮不了村庄而揪心。给我办事使他找到了寄托,他说他不是在帮我,只是在帮村庄。
在城里我单身了许久,和乡下女子相处惯了,和城里的姑娘总有点儿格格不入。后来我遇到一个叫莲的女子,她的一切都具有村庄的风韵。她不在乎我的家底,却看上了我身上农家孩子的勤劳和朴实。接受她的爱情,我知道又等于接受了村庄的一笔恩惠。
后来,父亲母亲跟着我进了城,开了一家土菜馆,贴补我的家用,曾经令我害羞的家乡菜,全部端在了大桌上。家乡菜全部来自家乡,别有一番滋味。母亲喜上眉梢地来回奔忙,有时为了应急,母亲会拿假土鸡冒充,算账时偷偷打点儿折。借助土菜馆,我发了一点儿小财,我真的离不开村庄了。我开始懂得,我们这些出门在外的人,永远都是村庄的骄傲,也永远都是村庄的累赘。我们把她的善良播撒,也把她的丑陋翻新。 不知从何时起,我开始把村庄像糖一样含在嘴里,稍不留神,香甜就脱口而出。我走到哪里,村庄都扑面而来。村庄的竹器、村庄的粮食、村庄的花卉,全都进了城,我感到这一切似乎都是跟着我进城的,这种感觉很亲切、很贴心、也很自得。我们这些从村庄出来的人,常常在一起聚会,在街道、在集市、在公园旁若无人地侃起村庄,就好像是在村庄的某个田亩说话,高昂铿锵。当人微言轻时,我们害怕提到村庄,怕由此引起人们的歧视;当功名趋盛时,又总期待他人提到村庄,让人知道我们付出的努力;当我们贫穷时,总为村庄感到羞涩;当我们富有时,又拿村庄来调味。我们永远在把村庄当做铺垫,当做背景。
总感觉对村庄有所亏欠,总是不想爽爽快快地承认。终于有一天,我的灵魂在不断地拷问中,把名利修炼成淡、成轻,这时,我的村庄才真实地凸现出来。走吧,回吧,从村庄出来的人,常常希望回一趟村庄,回一趟家,干点儿什么,或者什么也不干。
村庄最初不认识我们,但等我们一开口,就知道我们是谁了。在这块土地上,我们毕竟曾赤身裸体地摸爬过,村庄还残留着我们的呼吸。然而,正当我们想再次缩短和村庄的距离时,村庄似乎却又在一点点远去。村庄的风物,村人的思维,常让我们寡言少语,我们走近亲近,又走近了陌生。我们对村庄难以有什么回报,在那里久久徘徊,似乎还是在寻找什么东西。是因为过去我们带走太多,所以总认为取之不尽,我们走的时候,不是带走了一把铁锹、一把斧子,那些东西对我们没有用,我们带走的是别的东西,尽管两手空空,带的东西已经很多了,这似乎只有我才知道,而我又只有独自在夜晚书写文字时才真正知道。
而我那时疏忽了的是,我的文字又把村庄打扰了。我这后半生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要实现,那就是什么时候,要让村庄打个盹儿,我要带着它上路。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