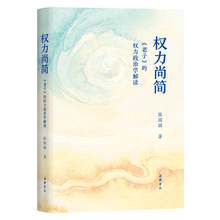我对此质疑的回答是,我对某个地区的理解并非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进行界分的,而恰恰是以学派的流动性所自然形成的状态作为讨论的前提。比如谈到湖湘学派的生成地域使用的是相对模糊的“湖湘地域”这个概念而相对较少使用“湖南”这个地区称呼,就是考虑到湖湘学派的形成是不同地区的学人交流互动的结果,如四川人张械和安徽人朱熹的身份均非行政区划下的所谓“湖南人”所能认定,但却通过在湖湘地区的活动赋予了其独特的人文气质。对区域的观察恰恰是以某个知识群体活动讲学的覆盖范围为依托,而这种活动的边界是不确定的,模糊到很难在行政地理区划的意义上锁定其活动的精确幅员轮廓。
但我亦认为,这种人文知识群体流动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派别尽管难以完全在地理上加以界定,却并不能成为我认同“区域文化建构说”的一个理由。因为某个区域学派一旦经过长期对话切磋,就有可能在某个地点沉淀下来,具有传承其自身思想传统的力量,并最终影响某个区域知识群体的思维和行动方式。这种影响可能具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并非某个时代特殊构造的“历史现象”所能加以说明。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