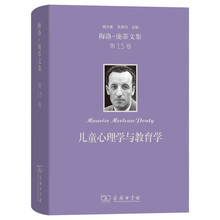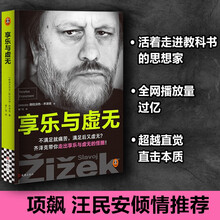我就是先说一下,所谓谈论普遍性问题就是连同数学、道德、政治这些较为具体的问题来谈的。如果你从来不关心普遍性这个问题,我也会觉得很奇怪,因为谈论民主制度的适用范围问题、谈论数学真理问题,不可能不涉及普遍性问题。
我们刚才简单地谈了一点,就已经涉及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汉语的论理传统,即今天汉语讲的“哲学的”,它已经注定跟西方的传统接上了——我们今天的论理词基本上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我们讲的“普遍性”就有可能是“uni-versa”或“universality”,这本来是个拉丁词,它大致的意思是“一对多”,或者说是“联系多之一”,或者就说“多之联系”,大概就是诸如此类的说法。刚才一讲到普遍性,周濂就马上提到“一与多”的问题,从西方文字面上就是同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来讨论普遍性问题,还不是只从字面上与西方哲学联系,它还跟另外一些西方概念连在一起,比如柏拉图的“理念”,康德的“绝对命令”,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
当然,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精通哲学史,但这个参照系是在那儿的。比如“普遍”这个词,我们今天可能在很多不同的场合使用,如在报纸上会常用,如“群众普遍存在不满情绪”,或者“贪污很普遍”,这时候这个“普遍”我们就不会把它翻译成“universal”,我们会把它翻译成“general”,或者“widespread”等。而在哲学传统里边考虑这个“普遍”的时候,我们多半是在谈“universal”。这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区别是在这儿:我们讲到“general”或者“widespread”,它不是百分之百的,我们说“贪污现象普遍”,它也许就是百分之七十,甚至就是百分之四十,我们都可以说它“贪污现象普遍”。但是在哲学里面谈到“普遍”,通常是指“无例外的”,如“二加二等于四”,没有地方二加二等于别的数。就此而言,我们就接触到哲学里面一个非常常见的区分:所谓“经验的”和“理性的”。
有人说人权是普适的,那我们说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人权。有人就说民主制都合适,民主制国家发展得还都行;有人说这东西可能不坏,但是中国的国情就不合适。到底普适不普适?
讲起制度,我们都知道“多样性”这个词已经流行很多年了,多样性也有这个问题,当然你可以提倡多样性,可是你提倡到什么程度?比如说中国人的观念,关于人权、民主,跟美国人不一样,中国是有其独特的文化的。但中国本身也是挺大的一个地方,对外是多样性中的一样,那对内呢?有普遍性吗?说我们中国人跟其他人不一样,好像是在反对普遍性,但是这不是明显也在主张一种普遍性吗?就是在中国内部的普遍性。但是,如果有一个少数民族说你不对,说你代表不了我们,可就是这个民族中当然也不是一种人,那你说多样性是多样到什么地方,最后多样到每一个个体?当然我们也知道,一个个体,此一时彼一时,那我们就不知道多样性多样到什么地方。
讲这些问题,不是说我要来解决它们,我不能说它们是日常问题,但的确是,平常如果你思考的话,就会联想到这么一个叫做“普遍性”的问题。换句话说,“普遍性”在我的理解中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它是一个题域,这个题域连着很多我们平常会思考的事情。最简单的说法,可以说“普遍性”这个词有若干重意思,都汇集到“普遍性”这样一个“论理词”的名下。我们说它们都汇集到“普遍性”这样一个词名下,是不是因为这些问题、这些意思有一个共同点?我们知道,至少维特根斯坦提出过一个叫做“家族相似”的说法,它们不一定有共同性,它们可能就是这个和那个有点像,那个和第三个有点像,然后就连到一个“家族”里面了。那么,共同点也好,家族相似也好,或者还有其他的……家族相似我觉得也不是咱们要说的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者结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