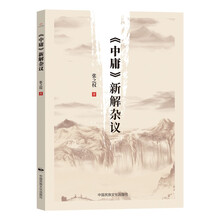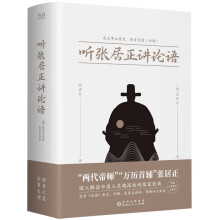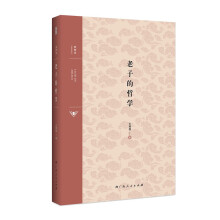思维对存在的反映,因了实践(“习”)的检证,气日充,量日丰,所以认识的对象是可以变革的,人类的认识也是可以发展的。“型范”,即今哲学术语的类概念,他不认为有“成型”的不变的人性类概念,人性反而可以由于实践的善养,与由于实践的不善养,而变化其“质”。所谓“气为质之充”是说通过实践而使人性更加丰富,通过这种过程就显示人类实践(“习”)所发生的功效,便可以改变人类认识的“质”(器官)。气是日生的,量是日生的,性也是日生的,故“质”也是日变的,好像寒因气之充而变为暑那样。由量到质的变化,不但表现向上的发展,而且也表现向下的变化。故“气以理纪质”是有多方面的意义。由量之充而发展,就得“理”之正,而由量之不充,也可以得“理”之反。不论是走了哪一方面,求“理”的过程都是由型范得出来的,型范虽有正与反。但却都是理的“节文”过程,得理与失理,都是理。这一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哲学,可与黑格尔的认识论(当然是颠倒的)对照研究。夫之的人性论超过了前人,后面还要详细研究。他释“性者日生者也”,在语源上亦合于历史。按两周金文,“性”之原字即“生”字,已有明证,如金文的“厥生”,即“诗”言“尔性”。因此,他把宋明儒以来所高谈的性命,重新规定了活生生的发展内容,并据此进而说明“理在日成”中,“未成可成,已成可革”,天下不可能有一成不变的“理”存在。他的认识论是和人性论直接结合的,关于人性的论点如下:
“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则夫天命者,岂但初生之顷命之哉?……天之生物,其化不息,初生之顷,非无所命也……
幼而少,少而壮,壮而老,亦非无所命也。……不更有所命,则年逝而性亦日忘也。……形日以养,气日以滋,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一日受之,受之者有所自授,岂非天哉。故天日命于人,而人日受命于天,故日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惟命之不穷也而靡常,故性屡移而易,抑惟理之本正也,而无固有之疵,故‘善,来复而无难,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性也者,岂一受成侀不受损益也哉?……形气者,亦受于天者也,非人之能自有也,而新故相推、日生不滞如斯矣。”(《尚书引义》卷三《太甲》二)
夫之从很笨重的经典形式(如《尚书》)中解放出来,使这种形式来服从他的理论内容。他把古代的天命观,拉到日降而富的新命观,否定了绝对的天命。他把古代的人性论,拉到日生而新的生化论(《思问录内篇》说“命日新而性富有也”),否定了绝对的人性类概念。因此,他说的“气与性为体”,也即把超乎现实的“理”,拉到实践之中日新而富有的理,否定了绝对的理的概念。“理”,不但是以客观存在的内容的发展而也发展,而且是以主观的认识官能(质)日生日新而也日富日善。“未成可成,已成可革”之性理说,是他的自然生化论的合理的发展。宋明以来的性理观在夫之的批判之下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
夫之既然肯定实在的气,日生的气,又肯定由气日日充实的质,即因实践改变了人类官能而生化的质,则性在气质之中也就日新而富有,并不是一降生就命定了的。性的体是能动的日受其生,性的用是能动的日至其善,从名实关系上说来如下:
“言性者,皆日吾知性也。折之日,性弗然也。犹将日,性胡不然也?故必正告之日,尔所言性者,非性也。今吾勿问其性,且问其知。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言性者于此而必穷。目击而遇之,有其成象,而不能为之名,如是者,于体非芒然也,而不给于用,无以名之,斯无以用之也;习闻而识之,谓有名之必有实,而究不能得其实,如是者,执名以起用,而芒然于其体,虽有用,固异体之用,非其用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