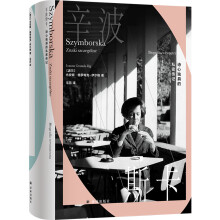2.民间艺术的感染
现在回到孙犁与书的关系上来。
孙犁与书的关系,开始于听人讲说评书(也叫平话)《三侠五义》和人鼓书《呼家将》等故事。幼年听说书时的情形,在他的义章《童年漫忆·听说书》中,有过具体的描述。
孙犁家所在的那条街上,有好几户人家,是长年去山西做小生意的。这些外出的人,春节也不回家,因为那时正是生意兴隆的季节。他们大多在春秋农忙时回来,为的是帮助家中收割和播种。其中有一个孙犁叫他德胜大伯的,当时有四十上下的年纪,他能说书。遇上夏秋之间农活稍闲的时候,人们在吃过晚饭之后,就会聚集到碾盘旁边纳凉休闲。一家大梢门两旁,有两个柳木门墩,德胜大伯常常被大家推请坐在一个门墩上面,给大家讲说《三侠五义》等故事。而另一个门墩,照例是留给年纪大、辈分高的人坐的,轮不到年青人和年幼如孙犁似的小孩子们去占领的。在孙犁的印象中,德胜大伯的评书,讲得很好,像专业艺人一样,不只故事记得很清楚完整,说得也很熟练。他是做小生意的,不会有时间,也舍不得专门花钱到娱乐场所去拜师学艺。按照孙犁的推想,德胜大伯的评书可能是这样学来的:他长年住在小旅馆里,同住的,干什么的人都有,夜晚没事,也许会请能说书的人,免费说上一两段,为远离家乡、长年在外的人消愁解闷。日子长了,德胜大伯也就记住了全书的人物、故事情节和各个细节,也学会了讲说的技艺。
在《童年漫忆。听说书》中,孙犁还生动地记述了他幼年时,听专业或半专业半业余的民间艺人说书的情形。较为常见的是,麦秋过后,这些艺人推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以车后架做鼓架。他们大多在街头说唱快书,只用鼓板,不用弦子。只说小段,不说整本。有的自己专事说书,说完之后,由热心的经管人,代他们敛些新打下的粮食,作为报酬。有的兼做小买卖,在说唱中间,则由经管人代他们在人群中,主要是在妇女中,为他们兜售一些针头线脑等小物件。等售完了预先准备的那些东西,他们就骑着车子赶往别的村子,说唱卖货去了。
最令孙犁难忘的,是在一年秋后,村里来了推着一车羊毛的兄弟三人,以说书招徕顾客,做擀毡条的生意。第一个晚上,就在街头说了起来。老大弹弦,老二说《呼家将》。村中的一些老书迷们,对兄弟俩的说唱技艺,赞赏不已,说是真正的西河人鼓,言调韵味纯正极了。既然能有这样的艺术享受,书迷们便自告奋勇地去各家各户做动员,为他们招揽生意。就这样,兄弟三人在村子里连续说唱了三四个月。眼看天气越来越冷了,村里要擀毡条的,都已经擀完了。但直到这时,书中呼延庆的擂,硬是没有打成。孙犁绘声绘色地写道:“每天晚上预告,明天就可以打擂了,第二天晚上,书中又出了岔子,还是打不成。人们盼呀,盼呀,大人孩子都在盼。村里娶儿聘妇要擀毡条的主,也差不多都擀了。几个老书迷,还在四处动员:‘擀一条吧,冬天铺在炕上多暖和呀!再说,你不擀毡条,呼延庆也打不了擂呀!’直到腊月二十老几,弟兄三个看着这村里实在也没有生意可做了,才结束了《呼家将》。”孙犁风趣地说:“他们这部长篇,如果整理出版,我想一定也有两块大砖头那么厚吧。”
在旧中国,像孙犁家乡那样的农村,文化生活是很贫乏的,与书有关的文化就更少了。要说与书有些关系的,除了说评书《三侠五义》,说唱大鼓书《呼家将》等一类活动,就是“吊挂”了。所谓“吊挂”,是一种用彩色绘制在粉底白布上的连环画,有人物,有山水车马,有故事情节。故事多取自《三国演义》、《封神演义》、《五代残唐》、《杨家将》等通俗小说。画法与庙宇中的壁画相似,形式则和年画上的连环画一样。每幅一尺多宽,二尺多长,下面作牙旗状。每四幅为一组,用绳子串挂排列于长街。看了“吊挂”上的连环画,可以增长一些历史文化知识。只是“吊挂”只在春节期间挂出,平常收藏在家庙里面,不能随便拿出来观赏。还有,能阅读《三国演义》等古书的人,才能看懂“吊挂”上的故事。如此看来,孙犁也是在上了小学之后,才仔细地看过与书籍内容相关的“吊挂”吧。
3.第一次借读《红楼梦》
1919年,孙犁6岁时进入本村小学读书。农村小学校的设备是很简陋的,不过是借。家闲院,两间泥房做教室。实行的又是复式教学,一个先生要教从一年级到四年级四个班学生。孙犁除了上小学,冬季时,还要上夜学。父亲为他买了一盏煤油灯。孙犁后来回忆说:“放学路上,提灯甚乐。”(《自编纪年》)孙犁家每年请先生两次。席间,他叔叔总是嘱咐老师,不要打他的侄子,因为他有病。有病,就是指前面提到过的孙犁患有惊风疾。他这种病,直到7岁以后,每年清明节这一天,由他叔叔带着,到三十里外的伍仁桥一户人家,用针刺手腕,连续三年,才治愈。
孙犁上的是国民小学,学的是新学制的课本,不再读“四书”“五经”和文言了。但当时在农村中所接触的,例如政府文告、春节门联、婚丧应酬等文字,还都是文言,很少白话文。就是说,在“五四”以后,在一定的场合,还需要学会应用文言文。孙犁接触的第一篇古文,是他家的私乘。他的父亲,在经营了多年商业、家境有所好转以后,决心要为祖父立块碑。他请一位进士写了一篇碑文,并把这篇碑文交给小学的先生,要他教会孙犁阅读,以准备在立碑仪式上,叫他在碑前朗诵。孙犁父亲把这件事看得很重。在他心目中,这“不只有光宗耀祖的虔诚,还有教子成材的希望”。70多年后,孙犁在《与友人论学习古文》一文中回忆彼时彼地的情景时说:“我记得先生每天在课后教我念,完全是生吞活剥,我也背得很熟,在我们家庭的那次大典上,据反映我读得还不错。那时我只有十岁,这篇碑文的内容,已经完全不记得……但是,那些之乎者也,那些抑扬顿挫,那些起承转合,那些空洞的颂扬之词,好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犁从识字开始,就有逛书摊的喜好。他晚年梦境中常常出现的一种景象是:“在小镇的长街上,有很多卖农具的,卖吃食的,其中偶尔有卖旧书的摊贩。或者,在杂乱放在地下的旧货中间,有几本书,它们对我最富有诱惑的力量。”在《书的梦》中孙犁说:“这是因为,在童年时代,常常在集市或庙会上,去光顾那些出售小书的摊贩。他们出卖各种石印的小说、唱本。”有时,在戏台附近的地摊上,还会遇到可以白白拿走的宣传耶稣教义的各种圣徒小传。对于这类书,孙犁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其中也有对他最具诱惑力的书,像小说《封神演义》、《红楼梦》等,但买这样一本即便是最普及的本子,也要花一两天的饭食之需。而孙犁当时的家境,虽已富裕了一些,也还是不能轻易购买的。那时他上学的课本,有的还是他母亲求人抄写的呢。
在孙犁幼年的那个时代,在他的家乡东辽城村,有书的人家几乎没有,能读书的农民也很少。他们不愿意,也没有条件去买去读那些“闲书”。在村子里,存有几本书的,是东、西头刘姓人家。他先是向西头刘家借了一部《封神演义》,读完了,又向东头刘家借了一部《金玉缘》,也就是《红楼梦》。
东头刘家有兄弟四人,三个因生活所迫在少年时就下了关东,只有老大留下来,娶了一房童养媳,算是成了一个家。老二老三最终没能回来。老四叫四喜,论乡亲辈,孙犁叫他四喜叔。四喜叔高高的个子,穿着黑布长衫,走起路来有些“蛇摇担晃”。这种走路姿势,常常成为大人们告诫孩子的教材,说是像四喜那种没有根柢的走法,将来是吃不上饭的。但孙犁对四喜叔的印象很好,曾这样描写过他:四喜叔性格开朗,行为洒脱。他从东头到西头,扬长地走在大街上,说句笑话,往往惹得那些嫂子辈的人,骂他“贼兔子”,他就越发高兴起来。他对孩子们尤其和气。有时坐在他家旷荡的院子里,拉着板胡,唱一段清扬悦耳的梆子,孩子们听起来很是入迷。四喜叔知道年近10岁的孙犁爱看书,就把一部《金玉缘》借给了他。
四喜叔的刀功非凡。每逢集市,用他那把锋利明快的切肉刀,帮人家卖肉。孙犁见过四喜叔彼时彼地的神采,令他赞叹不已:四喜叔站在卖肉的车子旁边,那把刀,在他手中熟练而敏捷地摇动着,那煮熟的牛肉、马肉或驴肉,切出来是那样地薄,就像木匠手下的刨花一样,飞起来,并有规律地落在又厚又大的圆形肉案子的边缘。这样,他给顾客们装进烧饼的时候,既出色,又非常方便。他是远近闻名的“飞刀刘四”。他在工作的当儿,那高大的身材,在顾客的层层包围下,顾盼自若,意气洋洋,虽说是英雄落魄,但暂时有了用武之地,“飞刀刘四”不乏庖丁解牛般的神色气度,确实令人向往。所以孙犁说,如果一个人能永远像“飞刀刘四”,在那样一种工作状态中存在,“岂不是很有意义,也很光荣?”但“飞刀刘四”的结局是很令人痛惜的。一次,他在帮人卖肉之后,喝醉了酒,在回家的路上,用刀逼着一个相识的人把自行车给他,不然,说要砍了人家。那人留下车子后去报了案。县长不分青红皂白,把他抓去就枪毙了。孙犁对第一个借给他《红楼梦》的四喜叔,始终不能忘怀,对他的人生悲剧,充满了沉痛之感。当他在息影二十多年后复出文坛时,在最初写作的几篇散文中,《童年漫忆。第一个借给我的人》写的就是以上所介绍的内容。在文章末了,他由四喜叔借给他《红楼梦》,引出了对书与人生命运关系的思考:“他那部《金玉缘》,当然也就没有了下落。看起来,是生活决定着他的命运,而不是书。而在我的童年时代,是和小小的书本同时,痛苦地看到了严酷的生活本身。”
读书总是和写字或者写文章连在一起的。在孙犁的幼年时代,写字还得用毛笔,用毛笔就得用砚台,或者用墨盒。用墨盒,里面最好铺上一层丝绵。要有丝绵,就得养蚕。不少孩子是喜欢养蚕的。但孙犁家乡桑树很少,只是在两家田地中间,有时种上一棵野桑,叫做桑坡,作为地界。尽管这种野桑很难生长,因为它的根,往往被犁铧铲断。但只要它不死,到了春天,就会发出一些铜钱大小的桑叶。这些桑叶,成了孩子们争夺的对象。桑坡上的枝条剥光了,只好用榆叶去喂蚕。但蚕不爱吃榆叶,能活下来的,到末了,也只能有气无力地吐出一点点丝来。和孙犁一起养蚕的,是一个和他很合得来的远房妹妹。他俩养的蚕,都只能吐出一点薄薄的丝绵。堂妹答应他,她的蚕吐的丝绵,也铺在他的墨盒里。堂妹不读书不识字,但她知道,墨多一些,可以多写字,而写好了字,写好了文章,就会有锦绣前程。孙犁在《蚕桑之事》中说,他们的丝绵总装不满盒,而他在12岁时,就离开了家乡。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