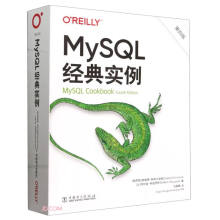这里还要解决一个疑问:有没有可能是在高宗朝画的画,在宁宗朝补的字?从文献记载看,在南宋画院组织的书配画类型创作中,比较普遍的做法是先书写文字,预留空绢,在一段不长的时间之后补图;如果有先画后书的情况,也应当在不久之后完工。作为表达朝廷一定政治意图的历史故事画,长期文图分离,对于宣扬政教,可谓事倍功半。而宁宗时实为南宋画院发展的最高峰,人才济济,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能够真正代表南宋绘画的时代风貌,这时把几十年前的旧画拿出来补题文字,似乎没有必要。因此我倾向于把台北李唐本的书法与绘画看成同时期的产品。
当认为李唐册确实源出于李唐时,其创稿时间就是Rorex所主张的高宗时期,并具体到绍兴和议之后的12世纪40年代,多少与韦太后的回归有关。但当绘画与书法的风格都提示了更晚的绘制时间,创稿的时间也不得不向更晚的历史时机中去寻求。创稿需要的历史条件,确为战争之后缔结和约,但不见得是南宋初年战争之后绍兴和议,却更可能是l 3世纪初的开禧北伐(1206——1207)和嘉定和议(1208),这是与台北李唐册和波士顿本的绘画风格、与台北李唐册的书法风格都比较吻合的一次“战争与和平”时机,也是南宋最后一次经历大规模战争之后还有机会享受较长时期和平,从而有余力进行大型绘画创作的时机。至于这种叙事画母题想表达什么思想主题,也只能从当时的历史形势中去寻找。
宁宗后期政治方面最大的事件,是嘉定元年(1208)史弥远上台后,推行“嘉定更化”,理学在南宋朝廷获得合法地位,并在随后的三十多年中逐渐增强势力,终于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从南宋后期开始,上层统治阶级的思想“转而趋向稳定、内向甚至是沉滞僵化,并逐渐渗透到整个国家的思想和制度之中”,理学正统化既是思想沉滞的主要表现,也是其促进动因之一。这时创制的《胡笳十八拍图》,也不可避免地与这项思想文化的重大转型联系起来。传为蔡琰所作的《胡笳十八拍》诗,首见于南宋初年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同书也收入了刘商的同名诗。到南宋,朱熹编的《楚辞后语》又同时收入了这两首诗。在创制《胡笳十八拍图》时,这两首诗都可供选择。《胡笳十八拍图》作为画院画家的“职务创作”,当然要仰承朝廷意志。他们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刘商诗,而没有选择名气更大的传蔡琰诗,或者说没有选择当时人都相信是蔡琰本人所作的诗呢?用传蔡琰诗传播不广来解释,显然不足采信,因为北宋王安石的集句体《胡笳十八拍》诗中已经集有传蔡琰诗的句子。这一选择之中,就蕴含着创稿的意图之所在。
刘商诗和传蔡琰诗在文学意象和思想取向上有明显的区别。传蔡琰诗的风格,确实像郭沐若所说的那样:“多么深切动人的作品啊!那像滚滚不尽的海涛,那像喷发着熔岩的活火山,那是用整个的灵魂吐诉出来的绝叫”,“那种不羁而雄浑的气魄,滚滚怒涛一样不可遏抑的悲愤,绞肠滴血般的痛苦”,“思想大有无神论的倾向,形式是民间歌谣的体裁,既有伤乎‘温柔敦厚’的诗教,而又杂以外来影响的胡声,因而不足以登大雅之堂”;而刘商诗“呆板得更不能相比”。这些话虽然是站在现代诗人的角度上来说的,该诗的文字组织、岂术水准是否完美也受到了清人徐世溥、今人胡国瑞等人质疑,但郭沫若指出了一个事实:传蔡琰诗的感情是强烈、甚至是激越的,而决不是后期封建社会的儒家所倡导的温柔敦厚。它塑造的蔡琰形象虽然也有别于蔡琰的历史原型,但它传达了、甚至强调了蔡琰性格中刚强坚韧的一面,这不是南宋道学家们所认同的。朱熹在《楚辞后语》中对传蔡琰诗所作的评语说:
琰失身胡虏,不能死义,固无可言,然犹能知其可耻,则与扬雄《反骚》之意又有间矣。今录此词,非恕琰也,亦以其雄之恶云尔。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