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基础教育阶段所大力提倡的“个性化自主阅读”,有多大程度是符合中学生阅读的真实状态,值得调查研究。一篇课文真有那么多的“意义”,学生真有可能产生那么多的“个性化”见解吗?它们都是有价值的吗?都值得肯定吗?现在的语文课让人忧虑的是“意义”太少,还是“意义”模糊?是“个性解读”太缺乏,还是“共性解读”太肤浅?
许多教条的做法,令他痛心疾首。他说:连一个哈姆雷特还没有弄清,就弄什么一千个!他的这个说法,不仅有经验的意义,而且有理论的意义。一千个哈姆雷特,既是一种跨国界的、跨历史的概括,也是对众多“理想读者”的提示。但,不管是什么时代、什么国度、什么样的读者,其首要任务,就是读懂哈姆雷特,歪曲的哈姆雷特就不是哈姆雷特了。在阅读理论上,读者主体不是绝对的,作者主体也不是绝对的,它们都要受到文本主体(共同视域)的制约。读者的多元对话,是相对于一元霸权而言的。一元尚未弄通,何来形成霸权?妄求多元,其结果是一元不元。在这方面的混淆,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风靡全国的语文课堂上的空对空的无效对话。说到痛切处,他甚至有点疾言厉色了:
任何教学方法的选择,都不能脱离具体施教的环境条件。如果今天请孔夫子来上语文课,他能够像“侍坐章”那样的上法吗?他老先生恐怕非得煞费苦心考虑组织教学不可。也就是说,举国皆然的班级授课制,天然地要受到时、地、人的条件限制,这几乎是一个铁定的“框子”。无论你教什么和怎样教,都不能不顾及——四十五分钟的一节课,五六十平方米的一间教室,五六十个的学生群体,你只能在这被框定的舞台上活动,你不能成为“飞天”。四十五分钟能进行多少“自主探究”的活动?五六十平方米能组织多少像模像样的合作式的学习讨论?五六十个,甚至多至六七十个学生,能够个个都加入“对话”的行列吗?在国外,班生数在三十个之内才适合语言教学,在小学,人数就还要减半,这才能进行对话,教师也自然会乐意选择对话教学。专家们可以坐在交椅上,指导说“你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可是站在讲台上的教师呢?他们总是不得不考虑“只能做什么,怎么做”。非不为也,乃不能也,我们不是常听见语文教师这样抱怨吗?什么是“对话”?非得你一言我一语,才叫做对话吗?无论是开口说话,还是闭口倾听,只要有交流存在,有声无声都应该是对话。如果认可这一点,那么一节课从头到尾,只由教师用启发式主讲,讲的内容合适,听得学生受用,理所当然应该视为成功的“对话”。我甚至认为语文能力的养成如果主要靠的是课外的“习得”,那么实际每周仅有三五个钟头的课内“学得”,就以接受性学习为主,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这个“接受”当然不是灌输式的,而是在学生自习的基础上的指导和传授。不考虑目的和需要,为“对话”而“对话”,满堂问答,热热闹闹,甚至连教师只能讲十分钟都规定了下来,这种教法与其说是贯彻新课标,不如说是对“教学相长”、“师生互动”的歪曲和糟践。
陈日亮这样的义无反顾,应该是中国语文界和北欧模式教学理论和方法的真正的对话。低水平的假对话,之所以能风行一时,还与某些形式的豪华包装,如多媒体,如学生表演等等有关。如此等等的形式花样,就把不称职教师的主体掩盖了。对此,陈日亮曾经不止一次发出呼喊:不少教师离开了这些花样,就不知道怎么教书了。他曾经把能不能将文本一堂课讲到底,作为考核年青教师的一个准则。可惜的是,这样最低的要求,却并不是很多年青教师都过得了关的。他的这个说法和做法,不仅有实践意义而且有理论意义。因为对话,是一种学术话语,和日常用语的直接问答有不尽相同的内涵。在学术上的对话具有隐喻意义,并不限于直接问答。我们常说,阅读就是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就是在隐喻的思想交流意义上说的。按美国演讲学,演说是一种交流,这里包含有声语言,也包括无声的躯体语言(表情、动作、笑声、鼓掌、沉思)。课堂教学当然是师生的平等交流,既有直接简短问答之意,又有无声的心领神会。就像读书一样,在这个时间段,你就是读,一言不发,读的过程中评价,质疑,虽然是无声的,但和日后在某一场合发表高见一样都是学术意义上的对话。一个教师,在一堂课上,从头到尾讲到底,讲得很有启发性,表情、身体和其他暗示,学生明白了,有感应了,也就是精彩的对话。
表面上看来,这是由于对学术话语的误解,是知识水平的局限,实际上,弄清这样的误解,有时并不需要学术语言,只要凭着经验就能纠正许多谬误。反对满堂灌,反到老师讲不了一堂完整的课,荒谬至于此,还要举着改革的神圣大旗,实在是许多不会教书的人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其结果是吓唬了自己。
陈日亮先生的这本书,是他四十多年教育生命的结晶,内容十分丰厚,我才概述了他的一个方面的观念,已经花了这么多的篇幅。活到这份为人写序的年纪,所患者乃唠叨,实在不好意思写下去了。为了不致太片面,在此简略地声明一下,陈先生丰富的教学思想,至少还有好几个方面,如他的作文教学,他的亲自“下水”等等方面,都是我们福建语文界乃至全国语文界应该认真研究、推广,加以普及的;值得拿出来作为本钱,用来和西方,尤其是北欧的母语教学对话的。
我这里用了一个比较俗气的词语:本钱。但是,我想只有这个词语对目前的许多误解才有冲击力。我们讲了这么多年的教学改革,改来改去,只是在方法上,观念上。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挟着行政的强制性的浩大声势,作倾盆大雨式的宣教,以为这就是教改的全部内涵。这里隐藏着一种危险的误解:以为解决了方法和观念问题教师就有了水准,教师就有了改革的本钱。其实,方法和观念的改变,只是教学改革的启蒙,教师水准的提高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改革以前的弊端不仅仅是方法和观念问题。具体来说,并不仅仅是满堂灌问题。满堂灌之所以要不得,原因在于其所灌的内容僵化,如果内容深邃,就是灌一下又有何妨?我们这些人,就是被有水平的大师灌出来的。大师们并没有为我们搞什么对话,我们不是一样也成才了吗?当然,他们如果采取对话的方式,可能会好一点。但是,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反而差一点。因为,为了等待一些比较弱的同学跟上来,不得不放慢速度。我在高中英文课堂上,就碰到这样的痛苦。一些从北方来的同学对英文一窍不通,教师非常好心,耐心地等待他们的理解。提问,答不出;启发,还是答不出。冷场,冷场,冷场。从南方学校升上来的,就白白地在浪费青春。如果当时他不等,因为他们既然连英语字母都记不全,而我们却已经在读小说《最后一课》、《项链》了,在这种情况下,等也是白等。如果就一往无前,老师就对我们这些人快速灌输,效率不知要提高多少倍。对话是一种教学方式,像一切优良的方式一样,必然蕴藏着局限。对话的局限,就是没有质量,空对空,没有深度,从平面到平面的滑行。当在对话苦于平面滑行的时候,灌输一下,是打破僵局,在层次上深化的一种必要措施。在某种比较深奥的地方,不能指望学生能从有限的经验自发地上升为系统的理论。绝对地胆怯于灌,就可能成为学生自发性,甚至是无理取闹,胡搅蛮缠的尾巴。不管是帮助学生从经验上升为理性,还是作理论的演绎,教师都是要有本钱的。这个本钱就是高于学生的素养。盲目迷信所谓平等对话,就会产生一种可怕的风气,把教师降低到学生的水平,让教师做无本钱的生意。
许多所谓示范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教师并没有拿出多少比学生更高明的见解来。这就造成了一种普遍的感觉,语文课,上和不上一个样。
这种多年的弊端,可谓积重难返,许多有识之士,为之痛心疾首。对于这一点,我和陈日亮都从理论上进行过思考。我在《名作细读》的序言中提出了一个观念,那就是语文教学与数理化英语课程根本不同。在数理化英语课堂上,学生对于课本和教材,不可能充分理解,其中有许多不懂需要教师作阐释。学生的认知过程是,从不懂到懂,从未知到已知。而语文课则不然。到了初中,课本上即使有少量生字,学生也可以从注解、从字典上得到解答。学生的感觉是全都懂了,没有什么不理解的。此时,教师上课的任务是什么呢?一般教师往往把学生已经理解了的,已经明白了的,或者理解起来没有难度的,用少慢差费的方式讲述一番,这就不能不引起学生的厌烦。我提出教师应该从文字上已经没有问题的地方提出深层次的问题来,作出相当警策的、开放性的阐释,因而,我在许多文章中,反复强调教师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不仅仅是个性自觉的愿望,而且是建立在个体素养和修养的深厚基础上的。
教师水平不高,不能适应改革的要求,这是当前无可回避的现状。我不赞成一味责难中学教师,这是因为,中学教师文本分析能力不足,是大学文本分析水准普遍低下造成的。首先应该遭到责难的是大学教师,当然也包括我在内。为此我才花了几年的工夫写了《名作细读》,目前出版的还只是第一本。第二本,已经写成,第三本正在完成之中。总共一百万字。但是,这也不等于说中学教师就没有可以责备的地方。我以为,最令人无奈的是,不少中学教师缺乏阅读、研究、写作的兴趣。说得粗暴一点,就是不求上进。而陈日亮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数十年地坚持阅读、研究、写作。不少中学教师,连各种各样的文本分析的文章都懒得翻阅,一味依赖网络上的教案。我问他们为什么,有一个正在修读教育硕士学位的女教师告诉我,那样太花时间了。阅读文本分析的文章,常常要花去四个多小时,而照搬教案,只要半个小时,最多一个小时。我不免大为惊讶。四个多小时,这算什么多呀,我们备课,一堂课往往要准备两三天。她说,你们课时少呀。我说你每周多少课时?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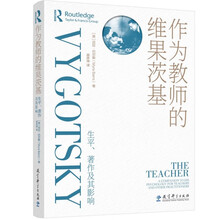



当前的任务是不能满足于喊喊观念方法等等口号,而应该多做陈日亮这样的草根的工作。
——孙绍振
陈老师是语文教育默默坚守者与探索者的一个代表,一个典型。他的最大特点,也是最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保守”,又绝不“趋时”。跳出了语文教育观念的“两极对立”的模式,他对语文教育和教育改革的思考,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和价值,特别是当人们冷静下来,面对语文教育的真实问题时,就会更感到他的清醒之可贵。
——钱理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