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处于耕猎时代的人类恐怕并不知道鱼是可以由雄性变为雌性或者由雌性变为雄性的,也不知道蚯蚓和其他生物一样拥有雌雄两套生殖器管。但是人类肯定知道,像人一样,野兽和家畜也是由雌雄两性组成的。对于我们人类而言,分化为两种性别(源于拉丁文secare,意为切开或分开)是一个终极真理。两性之间的差异一直被主伙比两性之间的相似更重要、更显著,这一认识几乎是不证自明的,这也贯穿到了世界各地各民族的有关人的起源的神话之中。
但是,神造人的神话也许在暗示着雌雄同体或者介于雌雄两性之间的另一咱性别的存在。在创世纪中,有隐讳的描写认为上帝是根据他自己的形象来创造男女的,这也就是说这个上帝是雌雄同体的。
在古希腊和罗马,雕塑家和陶匠塑造了一个雌雄同体(hermaphroditus)的形象(图1),他代表介于雌雄两性之间的性别,他是一个年轻男性,但双乳高耸。在医学术语中,这样一个人
也许只是年轻男性具有女性的乳房罢了,而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雌雄同体。只有当某个人的性别不能由其性器官的外观来判断时,这个人才被称为雌雄同体。
在新生儿的病例中有时很难确定性别,因为有的新生儿其外生殖器畸形或者在外形卜既不全表现为男性又不全表现为女性。
几个世纪以来,农夫就知道在牛类中的一种雌雄同体的牛,即被叫做“自由马丁”的牛。患病的小牛总是双胞胎,其中一个是正常的雄性,而另一个则是略微雄性化的雌形,而且总是不育的。
对于“自由马丁”的诊断和愈后都很明确,因为农夫们很早以前就知道这种病了,而且没有类似的其他病症存在,所以不会误诊。
人类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因为只有在非常孤立和近亲繁殖的人群中,才町能出现类似牛类中“自由马丁”的情况,即每一个雌雄问体的新生儿都有一样的诊断和愈后,而且都有一样的遗传原因。当在儿代之中都遇到这种病例之后,人们才知道婴儿成长到青春期以后会发生什么。在多米尼加共和国孤立的山地人群中就出现过这样的例子。当雌雄同体(两性人)首次出现在近亲结婚的几个家庭中时,最初他们被定为女孩,因为婴儿的性器官外观上像女性。但是,当到青春期时,他们的外形看起来更像男孩或“阉人”。他们没有高耸的乳房,也没有其他女性化的外部特征。这些人不能出嫁,常成为父母的负担。于是,这里的人们便吸取了教训,当再有相同症状的新生儿出生时,就会被当做男孩来抚养,尽管孩子的外阴并不是男性的。从婴儿期开始,这些孩子就被取笑为 “12岁的卵蛋”(guevodoces),或者“假小子”(machihembra)。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东部高地上,生活着山姆比亚(Sambia)部落,这也是一个极端孤立和近亲繁殖(imbred)的群落,类似的阴阳人(又称两性人)的家系也发生在这里。这里的阴阳人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同类有相同的遗传起源、相同的诊断结果(男性染色体5—甲还原酶缺失),以及相同的发育过程。当婴儿出生时,对其性别的确定传统上是依赖于接生婆是否见多识广,且仔细检查具有女性外形的婴儿的生殖器官。哪怕婴儿只有轻微的畸形存在,接生婆就把该婴儿叫做阴阳人(kwolu aatmwol),在皮金(Pidgin)语中则把阴阳人叫做图里姆男人(Tumim-man),两种叫法都旨在强调在青春期时,这种孩子会越来越像男人而不是女人。于是,这种婴儿就会被当做男孩来抚养。如果婴儿没有被仔细检查生殖器官,这类婴儿就会被当做女孩。
作为女孩,阴阳人的反常之处一直都没有人注意,直到青春期她也没有女性的第二性征发育(而表现为雌雄化)。这种发育畸形也许继续被隐藏着,直到结婚后被丈夫发现,于是,丈夫便会不承认这桩婚姻。
作为男孩,尽管他没有明显的阴茎且经常被嘲弄,部落长老会允许阴阳人加入培养武士的初期训练,但不允许他们毕业。在村落里他们只能做护卫(shaman)或者巫师,另一种选择就是逃到海滨城市去过现代都市生活。
以上这些孤立的近亲繁殖的群落是例外而不是常例。在地球上的大多数地方,基因库是如此芜杂,以至于当有阴阳人婴儿出生时,不可能用肉眼观察来确立和诊断而加以治疗,尽管其发病机理可能是遗传的。而男性阴阳人和女性阴阳人的性器官从外部上看也许难以区分。
在16世纪,著名法官科克(Lord Coke)勋爵宣称根据英格兰习惯法:“一个阴阳人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其性别应根据最终取胜的性别来决定。”并以此来决定遗产和爵位的继承权。所谓“最终取胜的性别”是指成年以后的性别,而并不一定是指出生时的性别。但是,科克勋爵并没有详细列出确定获胜性别的标准。
什么是确定阴阳人新生儿性别的标准?这个恼人的问题一直没有结论,直到1876年德国病理学家爱德温·克勒布斯(Edwin Klebs)依据性腺结构建立了区分阴阳人的分类系统。按照这一分类系统,一共有三种阴阳人。第一种是真正意义上的阴阳人(true her-maphroditism),这种人具有卵巢和睾丸两套性组织。另外两种则是伪刚刚人(pseudohermaphrodite),男性伪阴阳人只有睾丸组织,而女性伪阴阳人只有卵巢组织。这种三分法直到现在还在使用。实际上,克勒布斯认为只有睾丸和卵巢才是决定性别的标准。当然,在他那个时代,人类并不知道激素、染色体(chromosome)或者基因(gene)的存在。因此,他没有激素性别和染色体什别的概念,而这些概念乃是对阴阳人的现代理解的基石。
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
相对于上述动物试验,人类中类似的异常被称为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androgen insensitivity syndrome),之前被称为睾丸雌化综合征(简称AIS)。正如斯维尔综合征,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一样可证明,如果亚当定律不能在胎儿早期起作用,夏娃定律就会取而代之,引导胎儿向女性发育。
正常情况下,一个46XY染色体核型的受精卵应该发育成男性。在产前及产后期间,在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的患者身上,X染色体带有的有变异的基因导致体内需要雄性激素的细胞不能吸收和使用所需的雄性激素。来自精子的Y染色体没有上述变异的基因的替代基因,但来自精子的X染色休却有。所以,46XX染色休核型的受精卵可以掩盖有变异的基因,而不会发育成有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的女孩。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只出现在有着46XY染色体核型的女孩中。
在患有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的胚胎的亚当定律停止作用之前,性腺的的体(precursor)细胞形成睾九组织。这些睾丸组织分泌出睾丸酮和抗苗勒激素。后者防止苗勒氏管(副中肾管)发育成女性器官(子宫和输卵管)。但是睾丸雄激素(睾丸酮)却不能克服应该发育形成男性器官的细胞上的雄激素不敏感性。因而亚当定律不能作用而被夏娃定律取代。女性外部器官最终形成,但是由于没有内部器官可供连接,所以,阴道浅并以盲端结束。
在从男性变为女性的手术中,阴茎的皮肤并不剥去,而是可能与阴囊的皮肤一道被用来为人造阴道组成新开管道的内衬。阴茎皮肤的性敏感,加上其他阴茎周围区域的敏感组织可以保证性愉悦的继续,当然,这种性愉悦在一定程度上要依靠雌激素和孕激素的替补治疗。一些人把这种感觉比喻为使人愉悦的光,其强度不断增加并辐射到整个身体。另外有的人则把这种感觉比为高峰,有点像以前所经历但唾弃的男性性高潮。很多接受了有关女性性欲的陈规陋见,她们认为为男性性伙伴带来性快感比自我满足更重要。
从男性变为女性,女性激素替补治疗只能增大乳房,而不能使其声音女性化,也不能消除其体毛和胡须,因此,使用电针疗法剔除男性毛发是必要的。女性激素替补治疗会增加皮下脂肪,减少肌肉,降低皮肤尤其是面部的油性,这些都与女性的特征是一致的。
在从女性变为男性的性别重新判定中,乳房以及内部女性性器官都被切除。阴蒂则保留下来,包埋于再造阴茎的底部。阴茎是用腹部移植的皮肤做成的。整个变性手术相当繁琐复杂,需要几次手术才能把皮肤管道移植到阴茎的正常位置,并最终建成尿道。这样制作的阴茎不能勃起,需要借助某种形式的帮助才能插入性伴侣的阴道。性高潮町以通过刺激保留阴蒂的那个区域来达到,性高潮的实现还得部分地依赖持续的男性激素替补治疗。
男性激素替补治疗可以扩大声带并使声音男性化,使体毛和胡须长粗长多,但是如果秃顶是家族遗传,则它会使人秃顶。皮肤会变得多油脂,可能出现粉刺。阴蒂会增大,但不能大到可以改造成阴茎的地步。
综合起来看,女变男的手术结果多不尽如人意,更无须说繁多的手术所花费的时间和金钱。然而,大多数从女变男的人会因为有了一个假阴茎而带来一份拥有阳器的满足。
易性癖这个术语既是一种诊断,也表示一种康复(借助性改变)的方法。性的重判涉及社会,也涉及激素治疗和手术。社会康复既涉及家庭咨询,也涉及法律和职业咨询,此外,社会康复可能还涉及公众教育。
变性后的变性人的性伙伴一般都知道变性人的病史。这些性伙伴也许并没有接触过同性恋。其中许多人自己也没有感觉到自己是同性恋。他们对其变性人伙伴做出评价多是看其人品和行为,而并不涉及解剖学或生育能力。相反,一些人被易性癖者所吸引,不管其是否接受了变性手术。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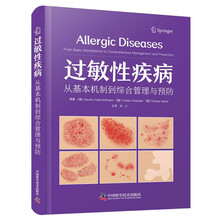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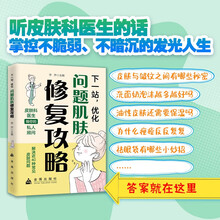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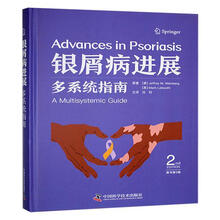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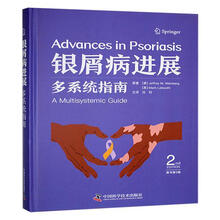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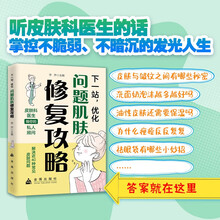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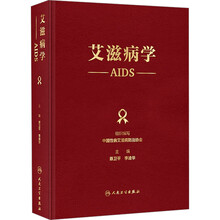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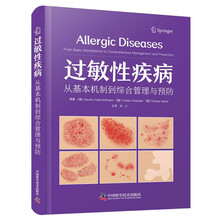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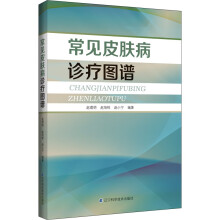

《人体的性缺陷》(或直译为《性的生理缺陷及相关症状——在咨询中帮助青少年及他们的家庭》)于1974年在北京度过了它的第六个生日。那么,它是怎样度过它的那个生日的呢?读
者也许要问,难道一本1968年用英语出版的书在1974年才得以在北京发行?事实是这样,本书在我的行李包里随我一起到达了北京。那年,我去访问我的一个童年时期的朋友——布瑞斯·哈尔兰德(Bryce Harland),他那时已是新西兰驻中国大使馆的大使了。我们是一起在新西兰首都威灵顿的郊区楼尔哈特的同一个社区里长大的。
那年到北京之前,我拟定了我的访问计划,我想知道中国是怎样治疗性器官先天缺陷的。我对两性人尤其感兴趣。那就是我为什么把我的这本书放到我的中国之旅的行李中的原因。
1974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像我这样的外国人在北京是很罕见的,因而要获得去儿童医院访问的许可是相当困难的。但在我的大使朋友的鼎力相助下,我最终得到了许可,并且受到了热情的接待。
在医院里,我参观了一个儿科手术的最后一部分。那个手术是对青春期前的小姑娘施行的子宫囊肿切除。根据我的观察,那个姑娘当时是处于清醒状态,有反应,但没有痛苦的表现。医生对她使用了镇静剂,但却没有使用麻醉剂,整个手术是用针灸来止痛的。我离开医院之前,在恢复室看到了那个姑娘,她和另外几个术后的孩子正在安静、平和地休息。我被告知,这些孩子会比使用麻醉剂做手术的孩子康复得更快。
我还参观了专门治疗有智力障碍的儿童的诊所。在那里,我见到了一位老医生,他是在美国受的教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在那个诊所已经工作了很多年。当时他正在用针灸治疗一个从小就有严重智力障碍的男孩。我问他效果怎样,他压着嗓门对我说,“就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吧,反正除此之外,也看不到任何希望。”我想再问他更多的问题,他却不愿别人看到他与一个外国人在一起且交谈那么久而终止了交谈。我意识到是该跟他道别的时候了。我当时想,也许我正被人跟踪着呢。
在访问儿童医院时,那个负责接待我的儿科女医生为不能用中国的儿科理论和临床实践来回答我有关两性人的问题而感到窘迫,她所能说的只是这种病例太稀少。不知道她是因为缺少先天生殖器官缺陷的知识而难堪呢,还是羞于在大庭广众之下谈论性。那时,也许我应该对她的接待表示我诚挚的感谢,然后马上离开。或者,我应该像我打算的那样,为了表示我的礼貌,请她转赠一本书给医院图书馆。我当时把一本书从我的包里拿了出来,递给了她。我似乎觉得做错了什么事,仿佛我在向公众展示两性人的两性性器官。他们会不会因为我而受到什么政治上的迫害呢?我别无选择,我的书也无处可藏。
转眼间,过去已将近30年了,我没有想到,本书在1994年经过修订和充实后出了第二版,而到了2003年,它居然有了中文版,并毫无限制地到达中国人的手中。本书中文版的面世其实正逢其时,因为艾滋病及艾滋病毒传播得越来越快。艾滋病是致命的病症,通过体液包括血液和性器官分泌的液体而传播,而且传染过程常常就是几分钟时间。艾滋病彻底改变了“性解放”的面目,将“性解放”与死亡纳入了一个方程式,而这个方程式还远没有被这个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国家包括中国所完全“消化”,从而采取相关的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