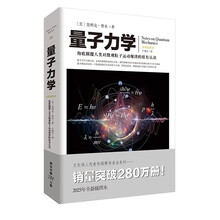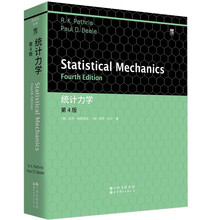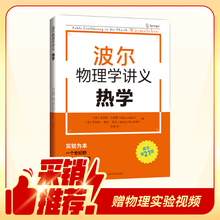因为在生成事物中那个持久不变的是与形式结合着的伴随因,它就像一位母亲;但是,对立的另一部分,如若人们集中注意力于坏的方面,就会觉得它仿佛不存在。因为,如若认为有些东西是神圣的、善良的和令人向往的,那么,我们就断言还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与它相反的,另一个是按照其本性它自然要欲求和渴望的。但按照他们的 观点,其结果就是,相反者渴望自己的消灭。然而,形式不能渴望它自身(因为它并不缺少),形式的反面也不能渴望它,因为相反的双方是彼此消灭的。真实的说法是质料渴望形式——似乎就像阴性渴望阳性,丑陋欲求漂亮一样。区别只在于,丑陋以及阴性的这种渴求不是由于本性,而是由于偶性。
因为一切感觉物体在本性上都处于何处,它们也各有自己特定的地点,而且,各物的整体和部分的地点是同一的,例如,整个大地与一块土、火与一星火的地点同一。所以,假如无限的感觉事物是同类的,那么,它就或者会不能运动,或者总是运动。但这都不可能。因为,为什么更要朝下而不是向上或往其他什么方向呢?我的意思是,假如以一块土为例,那么,它会在何处运动,或在何处静止呢?因为根据假定,与它同类的物体的地点是无限的。那么,它是否会占有整个地点呢?又如何占有呢?它的静止和运动到底是什么?或者,到底在何处进行?要么它就会在一切地方都静止(因此就不会运动),要么它就会在 一切地方的运动(因此就不会静止).但是,如若宇宙万物不是同类的,那么,各物的特有地点也就不同;而且首先,除了通过接触外,宇宙的物体就不会是统一体;其次,各部分物体在属上就或者是有限的,或者是无限的。但是,它们的属不会是有限的;因为假如宇宙是无限的,要么,其中的一些就会是无限的,另一些则不是无限的,例如火或水,但这样一来,就像前面所说过的,无限的那种元素就会消灭与它相反的那些东西了。(正是由于这个道理,自然哲学家们都不把火或土,而是把水或气或它们的中间物当作无限的统—体,因为火或土的地点显然是确定的,而水或气朝上或向下运动都可以。)但是,如果各个部分是为数无限的和单一的,那么,它们的地点和元素也就会是为数无限的。如果不能够这样,地点是有限的,整体也就必然会是有限的;因为地点和物体不能不相互对应。整个地点不可能会比物体占有的地点更大(所以,物体就不会是无限的),物体也不会比地点更大。因为不然的话,就会或者有某个空的地点存在,或者有其本性不占据任何地点的物体了。
但是,如若无变化,也不会有时间。因为当我们的思想没有发生变化,或者虽然变化了但却没有觉察时,我们就不会认为时间已经发生了,犹如神话中萨丁岛上那些睡在英雄身边的人们醒来时所发现的那样。因为他们把前一个现在和后一个现在重合在一起,当成了一个,由于无所觉察而漏掉了居间的时间。所以,就像把这个现在与另一个现在视为同一个就不会有时间一样,如果觉察不到两个现在之间的不同,也就会同样地认识不到那个居间时间的存在。因此,当我们还没有辨明任何变化,灵魂还显得是停留在单一而未分化的状态中时,我们就会不知道时间的存在,相反,当我们感觉到并且辨明了变化时,我们就会说时间已经过去了。因此显然,如若没有运动和变化,也就不会有时间。
所以显然,时间既不是运动,又不能没有运动。
既然我们的企图是要探索时间是什么,那么,我们就必须从这里出发来把握时间是运动的什么。因为我们是同时感觉到运动和时间的。尽管时间是模糊的,我们不能通过身体感受到,但是,如若某种运动在灵魂中发生,我们就会立即得知同时有某个时间已经过去了。反之,当得知有某个时间过去了时,也总是发现同时有某种运动已经发生了。所以可见,时间要么是运动,要么是运动的什么;既然它不是运动,就必然是运动的什么。
既然被运动的东西是从某处被运动到另一处,并且所有的积量都是连续的,那么,运动就与积量相一致;而且,由于积量是连续的,所以运动也是连续的;而如果运动是连续的,时间也就是连续的了。因为运动有多少,时间也总是被认为已经过去了多少。先于与后于的首要含义是在地点方面;在那里,它们表现为位置。此外,既然积量中有先于和后于,那么,运动中也必然有和积量相类似的先于和后于。但是,由于时间总是和运动相互一致的,所以,时间中也就有了先于和后于。先于和后于在运动中,它们作为存在时是运动,不过,在与存在相异时又不是运动。但是,当用先于和后于作规定时,我们规定了运动当然也就知晓了时间;换言之,只有在我们把握了运动之中的先于和后于的感觉时,我们才说时间已经过去了。通过判明先与后这两者的互不相同以及它们之间的某个居间者,我们才确定了它们。因为只有在我们想到两端与中点有区别时,并且在灵魂告之现在是两个时——一个在先,另一个在后——,我们才可以说,这就是时间。因为能被现在规定的东西才可被认为是时间。让我们把这个作为前提。
当我们感觉到现在只是作为一个,并且,既不作为运动中的先与后,也不作为时间的先与后的同一,我们就不会认为有什么时间已经过去了,因为没有任何运动。当我们感觉到先与后时,我们就说有时间,因为时间乃是就先后而言的运动的数目。
因此,时间不是运动,而是运动得以计量的数目。这就表明:我们依据数目来判定多和寡,又依据时间来判定运动的多和寡;因此,时间就是某种数目。既然数目有两层含义(因为我们是说,有被计数的或能被计数的数目以及我们用以计数的数目),那么,时间显然是被计数的数目,而不是我们用以计数的数目。我们用以计数的数目与被计数的数目是不同的。
就像运动一样,时间也总是彼此相随的。一切同时的时间都自我同一;因为现在在存在时是同一的;作为先与后来规定时间,它就不同于自身了。而且,现在自身既作为同一,又不作为同一:作为处于彼此相随的现在,它不同一(现在之为现在正是这个意思),但现在作为存在而存在时,它又是同一的。因为正如我们所说过的,运动和积量相一致,时间则要和运动相一致。同样,正如被移动凭借着点一样,我们也凭借着一个东西来认识运动以及运动中的先与后。这东西在存在上是同一的(因为它或者是一个点,一块石头,或者是诸如此类的其他什么东西),但在原理上则不相同。就像智者们所主张在吕克昂中的科里斯考斯与在市场上的科里斯考斯是不同的科里斯考斯一样,这东西从这里被移动到那里当然也是不同的。正如时间和运动相一致,现在也和被移动的东西相一致。因为正是凭借着这被移动了的东西,我们才认识了运动中的先与后;而作为能被计数的先与后,就是现在。所以,不论是在先于中还是在后于中,现在作为存在时都是同一的(因为先与后都是在运动中);但又不相同,因为现在是作为能被计数的先与后。这是最容易认知的道理:运动是通过被运动物,移动是通过被移动物;而被移动物是某一“这个”,但运动则不是。所以,现在在一方面总是作为自身同一的,但在另一方面则不是作为自身同一;因为被移动物也是这样。
很明显,如若没有时间,就不会有现在,反之,如若没有现在,也不会有时间。因为正像被移动与移动同时并存一样,被移动的数目与移动的数目也是同时并存的。因为时间就是移动的数目,“现在”对应于被移动物恰似数目的单位。
可见,时间既依靠现在而得以连续,又通过现在而得以划分。因为在这里,也有类似于移动与被移动物之间的那种关系:由于被移动物是单一体,运动和移动才据此成为单一的;它之所以是单一,并不由于处在存在中(因为这可能中断),而在于原理。这个被移动也规定了运动的先与后;就这方面而言,它与点有某种类似之处。因为点既连续长度又规定长度:它既是这一长度的起点,又是另一长度的终点。但是,如若有人要这样地把一个东西当作两个来使用,即如若把同一个点既作为起点又作为终点,那就必然有个停顿。然而,由于被移动物处在被运动中,所以,现在总是不相同的。所以,时间是数目,不是作为既是起点又是终点的那种点,它更像是线段的两端,而不是作为线段的部分。前者的理由已如上述(因为把线段的中间点作双重使用,就会出现停顿的结局),后者的理由很清楚:现在不是时间的部分,段落也不是运动的部分,就像点不是线段的部分一样;一条线的部分是两个线段。所以,现在作为限界,它不是时间,而是时间的偶性;它作为计数的东西,因而也就是数目。因为限界,只是有限界的东西的限界,而数目,例如10,则是这10匹马以及其他可数东西的数目。
由此,显而易见:时间乃是就先与后而言的运动的数目,并且是连续的(因为运动是属于连续性的东西)。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