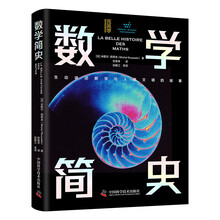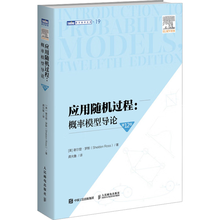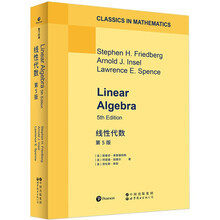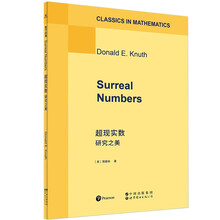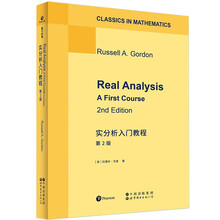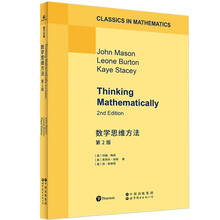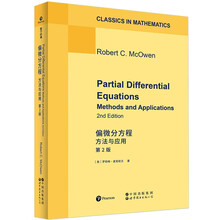概率在预测中的作用
那情景真是令人毛骨悚然。一具具肿胀不堪、发紫发乌、散发着腐臭味的尸体由弩炮大力掷向空中,沿着抛物线的轨迹飞落到被围困的城池内。该城即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卡法城(今乌克兰境内的费罗多西亚)。在14世纪,它是热那亚商旅的大本营。那时它正遭受蒙古军队的围攻,一如此前的数次被袭。在1344年的围攻中,这座城市还近乎坚不可摧,然而仅仅两年之后情势就发生逆转,这次伴随着中亚铁骑而来的还有黑死病。大批的鞑靼侵略军死于此病,堆积如山的尸体同时又造成严重的卫生问题。于是有军事天才提出了解围妙计。这些蒙古人随军带有一种被称为“投石机”的强大弩机,通常用其投掷沉重的石块来摧毁城墙和塔楼等石砌的防御工事。而今,“人体导弹”取代石块雨点般落到坚守在城墙内的人的身上。一个名叫加布里埃尔·穆斯的目击者在一份拉丁文手稿中描述道:很快地,如山的死人堆里增 加了大批誓死守城的基督徒们的尸体,只有那些侥幸得以逃生的人躲过了恶臭与疾病。
卡法城的故事并不只是人类细菌战的一个早期案例。一些历史学家和流行病学家相信这次战役标志着鼠疫开始由中亚传人欧洲。那些逃回欧洲的热那亚人很可能经由所乘船只上的老鼠及老鼠身上的跳蚤(这些跳蚤在咬人的同时将耶尔森氏鼠疫杆菌传人人体血管)将病菌带回了家乡。无论起源如何,1348年的欧洲大鼠疫的确是从地中海沿岸港口城市爆发并传播开来的。从当时僧侣的著述及教区死亡记录可以得知:被鼠疫夺走生命的人的总数占欧洲人口的25%-50%。但是,我们永远也无从确定黑死病传人欧洲的实际路径。
虽然黑死病爆发于数个世纪以前,但它所提出的问题至今仍为我们关注。为什么会“爆发”流行病?为什么科学家无法预测出某种“旧”型流行病(比如流感或麻疹)下一次爆发的时间、地点和规模?为什么他们更难预测出诸如艾滋病之类的“新”型流行病的发生?天气预报必须依赖于大气环流及海洋的恰当模型,而流行病预报的困难就在于很难建立起精确而科学的感染模型。只有当特定的一系列事件发生后流行病才爆发;由于每一事件都有一定的发生概率,因此疾病的爆发也就具有一个平均或预期的发生频率。为了预测流行病,我们需要建立准确的流行病发展的数学模型。要建立数学模型,就需要了解整个链条中的每一环节及其各自的发生概率,然后将所有环节的发生概率与特定区域所有相关人员的总数相乘,即可测算出整个事态发展的预期结果。举个简单的例子,让我们设想某一疾病在人际间传播的途径,比如说通过打喷嚏感染流感病毒。如果人群中每一感染者都平均接触并传染一个健康人(流行病学家称之为“易感者”),一场流行病就会爆发。要是每个感染者平均接触并传染一个以上的易感者,每一个新的感染者随后又接触并传染数个易感者,如此循环往复,则流行病将会大规模蔓延开来。倘若每个被感染者平均下来不能“成功”传染一个新个体,则流行病会渐渐衰亡。一个简单的链状概率模型便能反映上述情况。
另一个密切相关的例子源于生活中的幽默。假设你编了个笑话讲给几个好友听,要是这笑话一点儿也不好笑,它就不会传开。但如果你的朋友们听后捧腹大笑,而且其中每个人在24小时内转述给其他两个人听,则24小时后在此单链状模型中听到该笑话的人数就增加到2;依此类推,48小时后听到的人数又会增加到4,3天后增加到8,7天后就会有128个新人听过你的笑话了。听起来很惊人不是吗?别忙,让我们再看看--到第二周结束时,听过这笑话的人数将超过16 000人,到月底时这个数字将达到2.5亿人(大致相当于美国总人口数)。真的会有这么多人听到吗?有多少次你刚刚兴冲冲开个头,就会有人说“我早听过了”或“这笑话一点不好笑”?事实上,人口数量是有限的,同时,一些人会对某一疾病具有免疫力或是对某一笑话无动于衷,这些因素极大地影响了我们所建立的试图用来解释某个笑话或疾病如何得以传播的数学模型的计算结果。情况若非如此,对人类而言则既有好消息又有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大家都可以靠连锁信发家致富,坏消息如同1348年的黑死病也许会将整个欧洲人口灭绝殆尽。
这种连锁反应机制的另一有趣例子是闲话在工作场合的传播。不过,流言蜚语从本质上与传染病有更多共同之处。你听到了一条绘声绘色的小道消息,于是告诉了几个密友,他们随后又会讲给别人听。一传十、十传百,传到最后这个消息会与最初时大相径庭。譬如,你听到有关克瑞格和莫琳的某桩趣事并讲给其他人听,一个月之后你听到的却是一段添油加醋的有关格里格和诺琳的故事。你能听出这是个被传得走了样的版本吗,或是会把它当作新闻大热门立即通过电子邮件转告你的朋友?用生物遗传学的语言来描述,闲话已经发生了变异,然后如同发生变异的病毒,它可以再感染那些感染过初始病毒的人。流感发生的情形就是这样,因此疫苗每年都必须更新以有效预防新出现的病毒变种。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