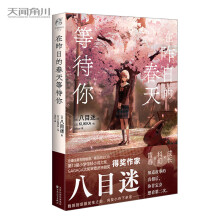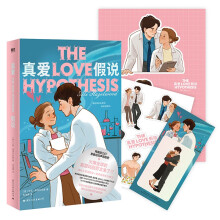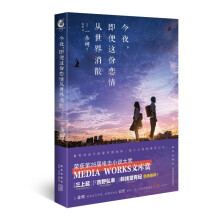扶养我长大成人的外婆,是个性急的人。
明明今年公园的樱花还没开,她却已经等不及这短短的半个月,满心期待地要我带着便当和她一起去赏花,即使我百般不愿意。
一直到最后,她都是个急性子的人。
丧礼那晚,打开电视,只听见记者以极度兴奋的语调说道:今年第一朵樱花已经在西边某处绽放了。
关掉才打开的电视,我喃喃说了声:“太迟了。”坐在身边的夏姬听到后,一脸困惑地把手伸过来,轻轻摸着我的头。那动作不如平常成熟,反而像是小女孩安慰弟弟似的生硬,却用尽她所有的温柔,害得我几乎落泪。我急忙拿起遥控器,关了桌灯。
即便关了所有灯,透过大片落地窗映入的月光,还是照得客厅一室明亮。
这里是夏姬的房间。我和她并肩坐在沙发上,并把脚翘在眼前的玻璃茶几上。白天,太阳明明大得害我汗湿了丧服的整个后背,随着夜愈深,凉意也愈发袭人。我穿着圆领衫,她则在T恤上罩了件稍长的开襟毛衣。那件毛衣,白底上织了玫瑰和蜂鸟图案,令人印象深刻。
“你知道吗?”
“嗯?”
“听说那个世界就在西方尽头。”
“喔。”
过了一会儿之后,我才反问:“所以?”
“所以……一定不会太迟的。”
“什么意思?”
“你外婆一定会在途中顺便看看西边刚开的樱花再上路的。”
我勉强挤出一丝笑容给她看。
“是啊……也许吧。我家那个外婆啊,这方面看起来挺精明的。不过到了那个世界之后,就不用专程带便当出门了,听说身边随处都是花田。”
再度伸过来的手,这次温柔地将我的头按向她的肩头。我乖乖任她摆布,虽然靠在女人的肩膀上,实在有点儿难为情,不过这么做了之后,我才发现这好像是我现在最希望她为我做的事。
这是夏姬第一次让我在这个房间过夜,或许今夜的我看起来真的相当无助。事实上,我的确全身无力,一想到明天是星期六,又没有什么非去不可的地方,就教人松一口气。她不用上班,大学也还没开学,打工的地方也已经联络好了。反正,往后不管我再怎样彻夜不归,也不会有人哕嗦了。想到这里,竟突然怀念起过去曾感到厌烦的低沉嗓音。
“嗯,小慎,”夏姬带点儿迟疑地开口说。“如果有什么事是我可以分担的,尽管跟我说。”
“什么事?”
“没有啦,如果没有就算了。只不过想说,你或许有什么话想要一吐为快。”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你从守灵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好像很痛苦的样子。如果只是伤心,我还可以理解,可是,你看起来好像真的很痛苦。”
“喔……你就那么注意我啊?”
心想她会一如往常四两拨千斤地避开话题,所以我故意带点儿戏谑的反问,谁知她一言不语,只是温柔地“咚、咚”拍了拍我的头。顿时,情感的波动再度排山倒海而来,但我紧闭双唇强压了下来……可恶!怎么偏偏碰上满月呢?灯都关了还这么亮!偏偏月亮又关不掉!
没办法,只好靠在她肩头闭上眼睛,但这么一来,眼前却清楚浮现出外婆几天前的身影,甚至比真人还要鲜明。
打烊前,外婆说要顺便帮我剪头发的声音;相对于此,我粗暴回嘴的措辞。之后第二天早上晚起,我发现外婆倒在洗头台下,已然冰冷……
夏姬沉默着,继续抚摸我的头。梳过头发的指尖,时而碰触到耳朵或脸颊。手指冰凉的触感,舒服得让我想起小时候外婆帮我量体温的手,鼻子不自觉地酸涩起来,弄得我原本无心,声音却哽咽了起来。
“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嗯?”
“要死好歹也先跟我说一声啊!”
夏姬的手颤动一下,停了下来。
“我有话想在那之前说啊!”
彼此间的呼吸在往返第四趟的时候,她又开始慢慢移动手指。
“吓我一跳,”夏姬小声地说,“曾经有个人也说过同样的话。”
“谁?”
“嗯……一个老朋友。”
“那个人的……谁过世了?”
夏姬不知为何没回答,只是深深地、静静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才慢慢说:“可是啊,唯有这件事,不管多后悔都没用。过世的人,我们怎么都追不到的。”
声音跟叹息一样静谧。
“对了,小慎,你听过死神与蜡烛的故事吗?”
“没有……应该没听过。”
“你小时候没读过吗?如果我记得没错,应该是格林童话。”
我摇摇头。“不记得了。”
“我小时候好怕那个故事。明明很怕,却不知为什么一看再看。死神把违背自己诺言的男人带到地底下类似地窖的地方,那里的墙上点着数也数不清的蜡烛。有的烛火旺盛,有的即将烧尽、烛火也相当微弱;再不然,就是这里点燃了一根新蜡烛,那里就熄灭了一根。换句话说,这些蜡烛代表人类的寿命。男人问自己的烛火是哪一根,死神就指了一根眼看就要熄灭、即将燃尽的蜡烛。”
我听见夏姬喉头发出小小的吞咽声。
“男人一慌,就拜托死神把自己的烛火移到隔壁又新又粗的蜡烛上去。死神先接受他的请求,倾斜着短蜡烛作势要将火移到新蜡烛上,却故意让烛火掉落在地上——瞬间,男人就砰地倒在了死神脚下。”
“……那是,死了吗?”
“对。”
“死了,故事就结束了吗?”
“对,结束了!”
“……”。
眼前浮现出地窖里无数的蜡烛,并试着想象其中外婆的蜡烛最后熄灭的瞬间。不知道是因为烧了很久,所以蜡烛变得很短,然后静静地只留下一缕轻烟就熄灭了?或者是明明还很长,却叫死神那家伙不小心弄倒了呢?
突然,一种说不清是愤怒或悲伤的情感在心中迸发,有如被泼西而出的冷水溅满全身般,我不禁颤抖起来。
“冷吗?”夏姬搂住我的肩膀,轻轻摩擦着。
“要不要开暖气?”
我摇头。
摇曳的烛光忽明忽暗地映在眼帘。那火光,跟守灵至今、点在灵堂上的许许多多的蜡烛重叠,并盘旋在我脑海里。
“总觉得,”我靠着夏姬不动地说,“丧礼根本就是活着的人在自我满足。每个人都在为跟死者毫不相干的事而四处奔走——只知道在意形式,讲究排场。”
忽然之间,我感觉到夏姬微微一笑。
“是啊。我也觉得丧礼是为了活着的人而办……”她语调缓慢,认真地说,“不过,为了转换心情,那是绝对必要的。毕竟,活着的人明天还要继续生活下去啊!而且,虽说是形式,但正因为有既定形式,才能安心地照做,不是吗?要是没有任何形式,不晓得有多少人会感到无所适从了。”
“可是,不管多隆重的丧礼,不都看不到本人高兴的样子吗?要花那么多钱办丧事,还不如在活着的时候多尽点儿心。”
“这我也可以理解,只是不管在世时尽了多少心,人死了,还是会后悔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吧?”
“……喔,难不成你有这种经验?”
夏姬露出一丝苦笑。
“只是就常理来说罢了。”
面对阳台的窗户外头,感觉稍稍暗了些。我起身从沙发站起来,走到窗边。
起了一点儿云。风吹得几朵流云聚在一起,遮住了月亮,并从缝隙间透出几道有如聚光灯般苍白的光束,照着坡道下的石神井池和对面扩散成一片黑压压的森林一隅。
夏姬静悄悄地走过来,站在我身边。
随着遮盖月光的云朵分分合合,光束的强度与粗细也时时不断变化。映照在水面上的椭圆形光束,乍看之下闪耀着炫目的白色光芒,却在下一瞬间,有如旧铝箔纸般模糊阴暗。
“可以问你一件事吗?”我试着问。
“什么?”
“你刚说的老朋友,会不会……是他?那个画画的家伙?”
然而,没有得到响应。
往身边看去,夏姬只是凝视着窗外,带着一丝微笑。那仿佛哭泣般的微笑,过去曾经看到过好几次。
早知道就不问了,我心想。从我们单独见面以来,今夜是我第一次感觉夏姬如此接近我,但偏偏一提到他,她的心马上飘然远扬。能让她出现这种表情的,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人——就是那个男人。
“小慎啊……”
原以为要继续刚刚的话题,夏姬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事。
“你要坚强喔!”
“……啊?干吗突然说这个。”
“慢慢来,不用太勉强,但要加油喔!若有什么我可以做的,我都会帮忙。就连外婆,一定也不希望你老是这么又哭又后悔的。“
“什么‘老是’,我根本就没哭啊!”
“虽然跟刚刚蜡烛的故事不相干,”无视于我的抗议,夏姬继续说,“不过,唯独人的寿命,我们只能当是一种命定而妥协。因为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努力去过上天所赋予的一生罢了,虽然死者已矣,生者何堪,却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继续活下去。”
我的确从她仿佛回到过去当老师的口吻中,获得一些安慰。不过,在此同时,心中某个角落里,事实上也有一股情绪正蠢蠢欲动——你懂什么!
虽然我觉得她说得都对,但唯独今天,我就是有一点儿拗,觉得她讲这些所谓的大道理也没用!反正再怎么说,她都是父母亲细心呵护的掌上明珠,跟我这种人不一样。外婆一手带大我这个被父母舍弃的孩子,最后我却连一句对不起都来不及说,外婆就已经撒手西归。这份悔恨,她根本不可能理解……
“死者已矣,生者何堪。”
她讲这句话的时候,到底抱着怎样的心情?
想到她那一瞬间的内心深处,心中便产生无限落寞。真希望眼前可以再回到月光之中,紧紧拥她入怀。
因为那一夜,她为我做了这十年来,她一直祈求有人能够为她做的事。
闭上眼睛,靠着某人的肩膀,只是静静地任由某人温柔地摸着自己的头——真正需要这些的,其实是夏姬。
1
那天,似乎下了场午后雷阵雨。八月底,蝉鸣也不耐那仿佛会天长地久热下去的暑气而歇了声。
在因雨而凉爽的街道上,吹起充满湿气的风,令人不禁想起南方岛国。在我打工咖啡厅前的人行道上,到处积着浅浅的水洼,过往行人时而因路两旁树上滴落的水滴而猛然缩起脖子。店内的桌布、印有店家标志的纸巾,不知不觉间,都因饱含水汽而变得软趴趴的。
突然,一个声音让我回过了头。
“请问这个柠檬塔……”
在紧邻着大开的玻璃门外,那名客人手指着对折的菜单,她就坐在我刚刚擦过的露台坐椅上。同是临时工的山田用手指兜一个圆圈对她说:“还蛮小的,大概就这么大。”
“那就这个吧,还要……大吉岭红茶。”
那女人的声音低低的,妩媚与清爽奇迹般的融合在一起,那感觉如同表层与衬里同时被丝绒和麻纱完美地缝合在一起似的。
我转过头去,望着她出神,连桌子都忘了整理。端正的额头,只把右侧长发夹到耳后的动作,都跟记忆中的一样,但因为她低着头,其实看不清楚她的脸庞。不久,在听过山田重复订单并轻轻点头之后,她合起菜单,交还给山田,终于抬起了脸。
记忆片段穿透我的身体,那强烈而鲜明的痛苦,连自己都无法理解。
急急忙忙将餐具收到后头,我抓了沾湿的抹布又走到外面,从角落开始,重新擦拭排在深绿色遮阳伞下的桌子,然后调整根本没歪的椅子。就我从旁观察,她和五年前一样,几乎没什么改变。虽然少说也有二十九岁了,但除了气质更加高雅端庄,几乎完全没变。不管是脸的轮廓,或是身体线条,都毫无松弛之处,姿势优美得仿佛从头顶吊着一根看不见的线。桌下交叠的长腿笔直地延伸到脚尖。说到小腿形状,完全对我的胃口,令我快要按捺不住。
唯有那么一瞬间,我们的眼神交会,她却面不改色地把目光移到手表上,然后往人行道的方向看去。
——也难怪啦!我自我安慰。她认识的我,不仅个头儿小,头发还是黑色的。然而,实际上,相较于十六岁,我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连我难得参加去年年底的同学会,昔日的同学们也无法一眼就认出我来。即便如此,我还是在心中存着一丝希望,期待眼神交会时,她会以怀念的语调呼唤我的名字。
位于东京练马区一隅的某所高中。
那时,我读高一,而她——齐藤夏姬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那时,她才刚从大学毕业两年左右,非常年轻,人长得漂亮又开得起玩笑,最重要的是她不像其他老师哕里哕嗦的,所以大家都非常亲近她。再说,她上的语文课也挺有趣的。
可是毕业后,她从不参加我们的同学会。据说,通知的明信片应该寄到了,但就是没收到出席与否的回音。
要是我现在走到她身边,喊她一声“老师”,她会是怎样的表情?我一边扶正写着菜单的看板,一边想着。毕竟,她当时不告而别便辞职离开学校,现在要是有学生主动攀谈,说不定反而会让她感到困扰,但左思右想,又觉得这样的机会实在干载难逢。就在我磨磨蹭蹭、犹豫不决之际,耳边响起一句:“请问!”我不禁跳了起来才响应,她带点儿讶异的表情看着我问:
“这里能不能抽烟啊?”
“很抱歉,由于这里面对人行道,所以禁烟。”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却语无伦次,连自己都觉得窝囊。但同时也暗忖:原来她抽烟啊!我问她要不要到店内的吸烟区,她摇了摇头说:
“不用了,反正我也不是非抽不可。”
“谢谢!”说着,她露出一丝微笑,随即又看了一下时间。环绕在纤细手腕上的粗犷手表,反射着黄昏的夕阳,发出内敛的光芒。
除了那只手表之外,她几乎没戴任何首饰。米色衬衫和同色系裙子都是很素雅的设计。就连脸上的妆,都淡到不确定到底有没有化。
即便如此,她还是有种独特气质,让路上往来的行人忍不住多看她一眼。她的亮眼并非鹤立鸡群般,只是很自然地吸引别人的目光。尽管是斑驳的古木椅,只要她如小鸟停驻般自然落座时,便仿佛置身在欧洲街角、历史悠久的咖啡座,连带把咖啡厅的格调都提升不少。
她现在到底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我心想。还在当老师吗?还是在哪家公司上班?或者已经结婚,育有一两个小孩,今天只是稍微出来松口气,跟同性友人碰面之类的?
由于我长时间的注视,她察觉到我的视线而抬起眼来,不解地歪着头。
我虽然吓了一跳,却在心里想着:就趁现在,去啊!说些“你还记得我吗?”或是“你一点都没变嘛!”不管什么都好,要是错过了眼前,恐怕再也遇不到这么难得的机会了……
就在这瞬间,她的眼神移到了我身后。
她等的人来了。
装着记忆的容器,或许像个发条已褪色的小音乐盒吧!乍见之下,不足为奇,所以平时连自己都忘记心里有个这样的东西。但是偶然的所见所闻却成为一把钥匙,只要刚好对上了钥匙孔,盒盖便会慢慢开启,并上紧发条,充满色彩、音乐的回忆,瞬间就会源源不绝地从盒子里流泻而出。
我的心中堆着好几个这样的盒子。有的盒子收藏着我想不断取出凝视的回忆,有的只收集希望尽快遗忘的记忆。当然,将其中的回忆一一分类的是我自己。
只不过,尽管以为自已已经小心翼翼地整理好了,不知为何,里面的记忆却总是擅自交替,犹如一入夜就会兀自动起来的玩具兵似的,出其不意地突袭我。比如说,难得我想要重温与外公外婆的回忆而打开盒盖,却突然浮现出妈妈的容貌和声音。
“你要乖喔!妈妈会再来看你。”
这句话,数不清妈妈跟我说了几遍。她说几次,我就相信几次。
当时,爸妈每晚都为了离婚与否而争论不休。闹到最后,终于决定离婚,接着又为五岁的儿子归谁而大动干戈。他们甚至不顾我就在隔壁房间听得一清二楚,谁都不肯让步。然而,他们不是抢着要扶养我而坚持己见,反倒想尽办法把我丢给对方,互相推卸责任。
许久之后,我才晓得,原来妈妈当时已经有了新的男人,而爸爸也有了新的女人。虽然不清楚是谁先出轨,总之最后还是扯平,所以不管对他们哪一个人而言,我都不过是个麻烦的累赘——就这点来看,他们也算是对臭味相投的夫妻吧!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