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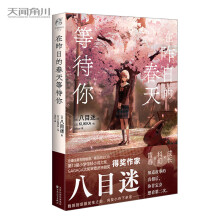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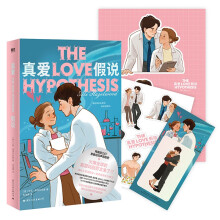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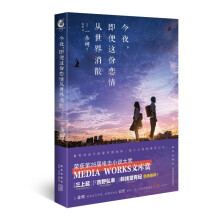



《在遥远的礁岛链上》(I Havsbandet)是瑞典现代文学巨匠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的“雷霆之作”,以斯德哥尔摩多岛海为背景,讲述了一位渔业督察员的故事。主人公智慧、犀利也自负,蔑视所谓“低等人”。在岛上“粗鄙而低级”的渔民和农夫中,他力图改革,有过胜利,但更多的是四处碰壁。他的心智和体魄都并不强健,在岛民中被孤立的他,很难弄清自己究竟是迫害者还是被害者。他在精神上的优越、性格上的颓废和敏感,也让他容易成为岛民和自然不可控力的袭击目标。小说还穿插了他和一位女子的感情纠葛,从订婚到分手。最后,主人公在圣诞夜到海上寻觅死亡。本书带有很强的尼采式的超人和悲剧英雄色彩,展示了浓郁的北欧风土人情。
第一章
五月的一个夜晚,一条鲱鱼船在外海的鹅石湾近风而立。因为三座金字塔而在海岛一带远近闻名的罗科纳正开始变蓝,而那清澈的天幕上,太阳开始沉降时,云已形成;海水已在岬外飞溅,横帆上恼人的拉扯表明陆风很快将被来自上端、海上和船后的新形成的气流打散。
舵柄那儿坐着东礁岛的海关主管,一个生着一把黑而长的络腮胡子的大汉,他看上去时不时地在与两个坐在前头的属下交换眼神,其中一个照管着带钩的杆子,好让大大的横帆保持迎风状态。
有时,舵手朝蜷缩于桅杆边的小个子绅士投去探寻的一瞥,这位绅士看似又惊又冷,不时地将围巾更用力地朝自己的腹部和下身拉扯。
海关主管一定觉得小个子惹人发笑,因为主管频繁转身到背风处,摆出一副嘴里有夹裹着烟草的唾液、要啐上一口的样子,好啐掉一个逼近而来的笑。
小个子绅士穿着一件海狸色春大衣,其下露出一条宽大的苔绿色裤子,裤子正落在一双鳄鱼皮靴的上缘,靴子上端的褐色皮绒面上带着黑纽扣。内衣几乎看不见,不过在脖子周围,他绕了一条奶油色绸巾。他的手由一副三纽扣的三文鱼色小山羊皮手套好好地保护着,右手腕戴着一根粗粗的金手镯,而金手镯雕成了一条咬住自己尾巴的蛇。手套下看得出手指处的隆起,像是有戒指。脸孔,就能看到的来说,瘦削又苍白,一小撮稀疏的黑胡子边缘上翘,加大了脸孔的苍白,显出些异国风。帽子朝后戴着,让黑色的、齐刷刷剪开的刘海看起来像无边圆帽的一部分。
最能抓住且不倦地抓住舵手注意力的是手镯、胡髭和刘海。
从达拉岛开始的长途航程里,他这个大幽默家试图和要航行到东礁岛去执行所接受的使命的渔业监管员开始一场愉快的交谈,可那位年轻博士对那些套近乎的风趣显现出伤人的无感,这让海关男人确信,“监管员”相当傲慢。
不管怎么说,当他们迎风穿过杭斯腾岛时,风力变强了,有生命危险的航行生动起来。手拿绸质海图坐着,在自己不时扔出的问题后做了记录的渔业监管员,此刻将海图塞入口袋,转身对舵手说话,那声调与其说是男人的,不如说是女人的:
“请稍微小心点驾船!”
“监管员怕了?”舵手回答,嘲笑着。
“是,我在意自己的命,这一点我会坚持。”监管员答道。
“不在意别人的?”舵手又顶上一句。
“至少不像对我自己的命那么在意,”监管员反驳,“航海是桩危险活计,特别在使用横帆时。”
“哟!那么先生是经常使用横帆航海的了,以前?”
“平生从未体验过!不过我当然看得出风给哪儿带来压力,算得出船重能给出多大的反作用力,完全明白什么时候船帆会后转。”
“那么,自己坐在舵边得了!”海关男人半呵斥着。
“不!那儿是海关主管的地盘!给国家办事途中,我不坐马车夫的位置。”
“当然,根本就不会航海嘛。”
“如果说我不会,要掌握航海技术自然非常容易,每个男学生都会,每个海关下级职员都会——不会航海丝毫不让我感觉羞耻!就小心地航行吧,我可不想变得湿漉漉的,也不愿弄坏我的手套。”
这是指示。本来怎么都算得上东礁岛最厉害的“那只公鸡”的海关男人,感觉到自己有些被罢免了的滋味。船舵动了动,帆又鼓了,船速飞快,稳定地朝着礁岛航行,那上头的白色海关小屋在落日光芒照射下耀眼地闪着光。
内群岛渐渐消退,往外海抵达了这一片巨大的、如今无边展开着自己、朝东而黑沉沉地威慑着一切的水面时,人会觉得脱离了所有仁慈的保护。没有爬上小岛或礁岩好躲在避风之处的希望,没有在暴风来临时收帆的可能,往外海去,人不得不到毁灭的正当中去,越过黑色海峡,往外,直抵那些看来比撒在海中的浮标大不了多少的小小岛礁。
正如前面所说的,渔业监管员强烈关心自己的性命,他够聪明,能估算出自己微不足道的抵抗力应对不可战胜的自然那无法计量的威力会是什么结果,因此觉得沮丧。36岁的他有着过于清晰的眼光,不会高估舵边男人的见识和勇气。看起来他对那张棕色面孔和那副大络腮胡子毫无信心;他也不相信一条肌肉发达的胳膊能在那股给摆动的帆带来数千碗磅压力的风跟前占得什么优势。他看穿了这样的胆子不过是基于有缺失的判断。真傻,他想,明明有甲板船和蒸汽船的,却把自己的命置于一条小敞船上冒险。这是多么难以置信的愚蠢,于一根云杉桅杆上升起一张如此大的帆,强风吹进时,桅杆曲起浑如一张弯弓。背风桅索松了,前桅索也一样,整个风压全倒在看来甚至已经烂了的迎风桅索上。把自己交给几根麻绳或多或少的内聚力这一不确定的因素,他可不愿意,因此,在紧接而来的强风中,他转向坐在升降索边的海关低级职员,以简短而有穿透力的声音命令:“把帆放下!”
海关低级职员看着船尾,等待舵手的指令,然而渔业监管员的命令在眨眼间得到重复,随着这样的强调,帆落了。
这会儿船尾的主管喊叫起来。
“是他妈谁在我的船上指挥?”
“我!”监管员回答。
接着,他转而对海关低级职员下达新命令:
“把桨伸出去!”
几支桨伸了出去,船晃了几下,因为海关主管在愤怒中离开船舵并且宣告:
“行啊,那就愿他自己能掌舵吧!”
监管员马上占据了船尾的地盘,海关主管未及停止咒骂,舵柄已到了监管员的胳膊底下。
小山羊皮手套立刻在大拇指接缝处裂开,不过,就在海关主管带着络腮胡里的笑坐着,一支桨准备好随时推出、给船开道时,船匀速向前了。渔业监管员丝毫不注意那带着怀疑的水手,只入神地盯着迎风侧,他能很快分辨出一个几米高的长谷般的涌浪,分辨出带短瀑布而被风吹起的浪,其后,他朝船尾匆匆扫视就测出了风压差,注意到尾流里水的流向,他已完全清楚,要避免漂离东礁岛得走哪条道了。
主管试了很久,想迎上那黑色的、燃烧的眼神,希望那眼神注意到自己的笑容,可他很快就疲惫了,因为那双眼睛看起来不想从他这里接收什么,似乎要保持干净,远离任何可能搅扰或弄脏它们的东西。乞求了一阵,主管泄了气,心不在焉地观察起船上的部署。
此刻太阳已落至地平线,浪花崩裂,底部紫黑,边缘深绿,浪头升起的最高处亮着草绿色,泡沫喷吐,在阳光里染成红香槟色。载着男人们的船这会儿低低地沉入暮色里,在一个瞬间居于浪峰之巅,四张脸亮了,又立刻熄灭。
并非所有的浪花都会崩裂,有些只慢慢滚动向前,轻摇着船儿,提起它,又往前推着它。似乎那小个子舵手从远处便能判断出一个碎浪何时到来,他轻推舵柄,或保持航线,或有所偏移,或潜行在那可怕的、威胁着飞奔向前、要在船上击打出自己的拱门的绿墙之间。
事实上,帆被取下后,危险确实增加了。因为驱动力减弱了,人得在没有风帆提力的情况下航行,因此,对于这难以置信的良好操作,海关主管的那份吃惊开始转为崇拜。
他看着那张苍白面孔上变化的表情和那双黑眼睛的转动,感觉那里头隐藏着某种更综合的盘算。然后,为了使自己看上去不那么多余,他伸出自己的桨,觉得机会来了, 想在它溜走前表达诚挚而自发的善意:
“他以前在海上待过!”
部分是因为正忙得不可开交,部分是因为不愿和海关主管有任何交集,监管员不想为一个受惊的瞬间的软弱而被这个战斗者外表的超强愚弄,于是没做任何回应。
他的右手手套沿着整个大拇指完全裂开,手镯也掉了下来。光辉从浪尖褪去,暮色降临时,他用左手掏出单片眼镜搁在右眼上,对着航海罗盘上的好多条纹迅速移动脑袋,好像在察看陆地,而没有陆地可见。于是,他抛出一个溅着水花的问题:
“东礁岛没有灯塔吗?”
“没有,上帝知道。”主管回答。
“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碰上暗礁?”
“完全是水。”
“但是能看到兰德斯奥特和桑德哈姆的灯塔吗?”
“桑德哈姆的看不清,不过兰德斯奥特的那个清楚些。” 主管说。
“坐在原地别动,我们会走对。”监管员结束对话,他似乎借助三个男人的头以及远处几个不明固定点确定了位置。
云已聚,五月暮色被半黑占据。就像在某种轻薄而不透明的物质里摇摆,没有光线。只有在更黑暗的影子对着空气半暗的影子时,海浪才会升起。它们向着船底举头撞击,让船儿在浪脊上给抬起,弹到另一边,在那儿滚动着给推开而变得扁平。然而此刻,把朋友和敌人分开变得更难了,测算更难以确定了。两支桨在避风侧伸出去,一支桨在迎风侧,这多少带来一些力量,在对的瞬间保证船儿漂浮。
除了北面和南面的两处灯塔,很快就会什么也看不见的监管员必须用耳朵代替眼睛,然而在他习惯于海浪的咆哮、哀叹、嘶鸣,习惯于区分一个碎浪或风卷的波浪之前,水已进入船内,他不得不将两腿搁在坐板上来保护自己考究的靴子。
不过,很快他已研究了海浪的和声学,甚至能从浪涌有规则的节拍中听出危险的迫近,当海风压得更强烈、威胁着要把浪头卷得更高时,他感觉到右耳的鼓膜,像是他演奏着自己那敏感的知觉的航海和气象乐器,连着脑电池的电线完全裸露,只是让那小而可笑的帽子和一刀切的黑刘海遮住了。
在海水侵入的那一刻吐出粗暴言辞的男人们,感觉到船如何在向前猛冲后平静了下来,听从每一个号令:迎风或背风,明白他们在哪一边,该怎么做。
监管员借助那两座灯塔进行定位,把他的单片眼镜当成了望远镜,但保持船只航线的难度在于,礁岛上木房的窗户里没有任何光亮,因为房子建在石坡背风处。如今这危险的航行已进行了一小时或许更久,前方地平线上露出一片黑色高地。那个不愿让可疑的建议干扰,更相信自己的直觉的舵手保持着沉默,他觉得那该是礁岩或大石块,他安慰自己,抵达一个固定的地方,不管那是什么,总比漂在空气和海水间要好。然而,那堵黑墙以比船只更快的速度逼近,以至于怀疑在监管员大脑中苏醒,他觉得航线有些不对。为确认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同时也给出信号,万一那是一艘船,一艘没点灯的船,他掏出自己的风暴火柴盒,点上一整盒,在半空高举了片刻,再扔掉,这样它们在船的周围照亮了几米远。亮光只穿透了黑暗一秒,不过,那个图像像一盏魔术灯在他眼前停留了好几秒。他看见漂流的冰块撞击岩石,波浪碎于石块,像巨大的石灰岩上的洞穴;他看见一群长尾鸭还有海鸥带着无数尖叫飞起,然后,沉于黑暗。碎浪景象在监管员面前呈现出一具棺材的视觉印象,里头将躺着被宣告死亡的分割了的尸体,他感受到这一想象中寒冷和窒息的双重剧痛。然而,麻痹他的肌肉的苦痛反而唤起了灵魂潜藏着的所有力量,让他在顷刻间准确算出危险的大小,算出逃生的唯一办法,于是他喊出一声指令:“停!”
背朝波浪而坐、没察觉到这一切的男人们歇在桨上,船给吸进约三四米高的碎浪。浪在船只上方的高处裂开,像一座瓶绿色穹顶,带着全部的水往下坠于另一边。船的另一侧就像吐过一样,一半是水,而船中人让可怕的气压弄得半窒息。有时能听见三声哭号,像做了噩梦的睡眠中人,而那第四个,舵柄那儿的男人,则沉默着。他只是用手指了指礁岛,看得见在不过几链外的背风处有灯光闪烁,于是他沉到船尾柱下,躺下了。
船停止了起伏,因为已进入顺水,所有桨手都坐着,似乎醉着,点了点如今已不需要的桨,船缓缓地由顺风推进了码头。
“船上有些什么,好伙计们?”道了声让一阵风吹跑了的“晚上好”之后,一个老渔民询问。
“是渔业监管员!”海关主管一边将船拉到一间船屋的后头,一边嘀咕。
“是吗,一个想来窥探渔网的!好吧,祝他如愿以偿!”
渔民乌曼说,他像是这岛上穷困而稀疏的住民的头儿。
海关主管等着监管员上岸的表示,可他看不到艉柱那儿躺着的小东西有任何蠕动,便担心地爬进船,双臂抓住那具衰竭的身体,将其抬上了岸。
“他完了?”乌曼问,带着一点但愿如此的意思。
“差不多。”海关主管说着,拖住那潮湿的重负往房子里去。
魁梧的海关主管跨进兄弟的厨房的情形里有某种巨人和小拇指的味道,弟媳站在炉边。他在沙发上放下那具小身体,一丝对弱小之人的同情浮现于低额头下的大胡须上。
“看,这是我们的渔业监管员,玛瑞。”他和弟媳打招呼,随后在她腰上搂上一把。“现在来帮帮我们,拿点干的给他擦擦,送点湿的进他嘴里,他好进自己的房间。”
躺在坚硬的木沙发上的监管员看上去是一具悲惨而可笑的形体。白色衬衫高领在他脖子周围扭成了一块破布,右手手指全部从裂开的手套那儿露出,软化的袖口耷拉着,上头沾着溶解的淀粉。小鳄鱼靴失去了原有的光泽和形状,主管和弟媳费了很大的劲才将它们从脚上脱下来。
主人们终于脱掉了“失事船只”身上的大多数衣服,给他盖上一条毯子后,拿来了煮牛奶和烈酒。而后,一人摇着受苦者的一只胳膊,主管用自己的胳膊抵起小个子的身子,在他闭着的眼睛下、张开的嘴巴里慢慢地注入牛奶。不过,当弟媳要给他灌下烈酒时,那气味似乎对监管员起到了速效毒药的作用。他抬起一只手推开玻璃杯,而后睁开眼,完全清醒了,似乎刚结束一段补充精神的睡眠,他问起自己的房间。
房间自然还没收拾好,不过约一小时后会好的,只要他愿意在这儿静躺着等待。
于是监管员躺在那里,消磨无法忍受的一小时,让眼睛在房子乏味的陈设和住民间移动。这是政府给东礁岛小海关的主管免费使用的屋子。几乎什么都没有,安置得和头顶的天花板一样。白色而未贴壁纸的墙面抽象得正如国家的构想,四个白色四方形围成一个房间,为一个白色四方形覆盖。与个人无关,生硬得好像旅店,不是用来居住,而只是寄宿用的。为了接班人或政府贴上点墙纸,这位主管和他的前任都没这份心。而在这死一般的白色正中,立 着暗黑、劣质、半摩登的、工厂生产出的家具。一张带松树结的圆饭桌上有核桃木染色剂,满是白色的、挂碟子的弹簧圈。几把同样材质和纹路的椅子,高背、歪斜,在三条腿上轮番晃荡。一张坐卧两用的长沙发,好像一件用最少的料和最低的价做出的男子成衣。一切都不合适,没有什么东西能满足邀人休息或感觉舒适的目的,也因此不好看,尽管他们贴了纸质装饰物,还是十分难看。
海关主管将他硕大的屁股坐进一张藤条椅,当庞大的背抵住倚靠时,椅子立刻发出一阵恼人的吱吱声,还有弟媳愠怒的训斥——小心别人的东西,主管却用一个放肆的拍打来回嘴,接着是一道眼神,确定无疑,这两人有一腿。
整个屋子给监管员带来的压迫感因为这一不和谐的发现而加剧。作为自然研究者,他并没有那些允许和不允许的常规概念。然而,对于刻意制定的自然法则,他有强大而鲜明的直觉,看到自然的指示遭到违背,内心会很不舒服。对他来说,似乎在他自己的实验室里有这么一种酸,自创世起通常只和一个盐基结合,可现在竟然违抗自然法则,和两个结合上了。
在他的思绪里运转着从普遍杂交到一夫一妻制的进化,他感觉自己走回远古时期,和过着珊瑚般生活的野人部落在一起,是选择和变异能承载个体的存在和血统之前的群居状态。
当他看到一个有着过于硕大的头和一双鱼眼的两岁女孩踩着猫步在屋里走来走去,怕被人瞧见似的,他立刻意识到,那可疑的血统撒下了纷争的种子,似乎是毁灭性的,会惹出事端。而他能轻易地算出,那个时刻一定会来,那时,这个活着的见证人会让所有的人得到惩罚:一个危险的见证人非自愿的罪过的惩罚。
他还在这些思绪中时,门给打开了,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进来了。
那是海关主管的弟弟,还停留在下属的杂工位置上。
体格上他生得比主管还魁梧,不过他金发白肤,带着开放、友好而充满信任的表情。
招呼上一声愉快的“晚上好”之后,他挨着自己的哥哥在桌边坐下,抱起孩子放在自己的腿上,吻她。
“我们有客人!”主管知会着,指了指监管员躺着的沙发,“要住在楼上的渔业监管员。”
“哦,是他吗?”韦斯特曼说着起身去和监管员打招呼。
他把孩子抱在臂弯里走近沙发,因为他是这里的主人,未婚的哥哥只是和他吃住在一起,他觉得自己必须对客人表示欢迎。
“我们这儿简陋,”他说了些祝愿的话之后补充道,“不过我老婆不是完全不懂烹调,三年前嫁给我之前,她在一间更好的屋子里当过差。可我们有了小家伙以后,她有别的事需要费神。没错,有人帮,就会有孩子——是有这说法,我倒是没像这话里说的那样需要帮助。”
监管员吃惊于长句子突然的转弯,他问自己,这男人是否知道了什么,还是说只不过觉得哪里出了点问题。监管员自己可是十分钟内就看出了一切——对问题好奇的人怎么可能几年还弄不明白呢?
监管员受困于对整件事的厌恶,转向墙面以便合上眼,用脑子里更愉悦的大自然的图景打发剩下的半小时。
可他没法让自己耳聋,反而违背意愿地听见了一通对话,刚才还很生动,艰难向前似乎字眼出口前拿折尺量过,出现沉默时,便由那丈夫填补,那人似乎对沉默深恶痛绝,怕听到不想听的,而在自己的言语之河迷醉自己之前,他又无法平静。
一小时终于结束却还没有关于房间的说法,监管员起身问:“弄好没有?”
“好了,”女主人说,“某种程度上是好了,不过——”
监管员以一种命令的语气要求立刻把房间收拾好,并用得体而威严的言语提醒他们,他可不是自己要来住进这里头的,也不是谁的客人,而是带着政府指定的任务前来,只是在要求自己的权利——他可以得到这些,因为发自民事部门的照会已通过国税总局送到达拉岛皇家海关了。
于是事情立刻给理顺了,韦斯特曼握着一支蜡烛,跟着这位严肃的绅士上楼到山形墙卧室,那里的摆布没有一样能解释竟然要拖沓一个小时。
一个挺大的房间,和楼下一样,墙是白色的,大窗户在长墙正当中打开,像一口黑洞,黑暗从洞外流入房间,没受任何窗帘的阻挡。
有一张床已在那儿铺好,简单得似乎不过是地板上的一个隆起,好阻止穿堂风;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盥洗柜。监管员带着绝望的眼神朝自己周边环顾,惯于饱眼福的他,如今只见稀疏的生活必需品给移植到了这空房间,在这里,牛脂蜡烛对抗着黑暗,大窗户似乎要消耗燃烧的牛脂蜡烛产生的每一束光线。
他觉得自己是那么迷茫,似乎朝着雅致、地位和奢侈向上奋斗了半生之后,他跌入贫困,进入一个低阶层里,似乎他热爱优美与智慧的感性给投进了牢房、剥夺了营养而进入一所刑罚机构。裸露的墙宛如中世纪修道院的静修室,那里有禁欲主义的图景,环境里的空无催促饥饿的幻想噬咬自己,招致更亮或更暗的幻象,只为从空无中挣脱。墙面石灰里的苍白、无形也无色的空无强迫出一个要想象出某个图景的驱动力,那是野人洞或枝叶窝棚永不会唤起的,是具有永远转换的颜色和移动的轮廓的森林无须在意的,一个想象出图景来的驱动力向前推:平原不会有这样的驱动力,有着天空色彩丰富的变幻的石楠荒原不会,永不疲倦的大海也不会。
他立刻感到一个发酵了的欲望,要在瞬间拿起带棕榈和鹦鹉的阳光明媚的风景涂满墙面,将一条波斯毯展开在天花板上,在账本一样有线条的木地板上铺上兽皮,把转角沙发置于角落,前头摆上小桌,在满是书刊的圆桌上方挂一盏吊顶灯,对着短墙架起钢琴,以一排书架装饰长墙,在沙发角竖一座小小的女体雕像,无论是谁!——就像桌上的蜡烛对抗黑暗,他的想象反抗着房间的陈设,然而,想象失去掌控,一切都消失了,周围瘆人的一切把他吓上床,接着,他灭了烛火,拉过毯子盖住了头。
风摇撼着整个山墙,水罐碰着水杯咔嗒咔嗒响,风儿从窗户到房门再穿过房间,时不时抚摸着他已被海风吹干的一缕头发,他觉得像有人用手摩擦他的头,而在交响乐团的定音鼓般的狂风呼号间,礁岛南边的岬上,碎浪冲击着悬崖。当他终于开始习惯风和浪单调的声音,就要入睡前,听见楼下一个男人的声音,那是在为一个孩子做晚祷告。